廿一年磨一剑——访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天华
2014-01-26阮静
●本刊记者 阮静
廿一年磨一剑
——访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天华
●本刊记者 阮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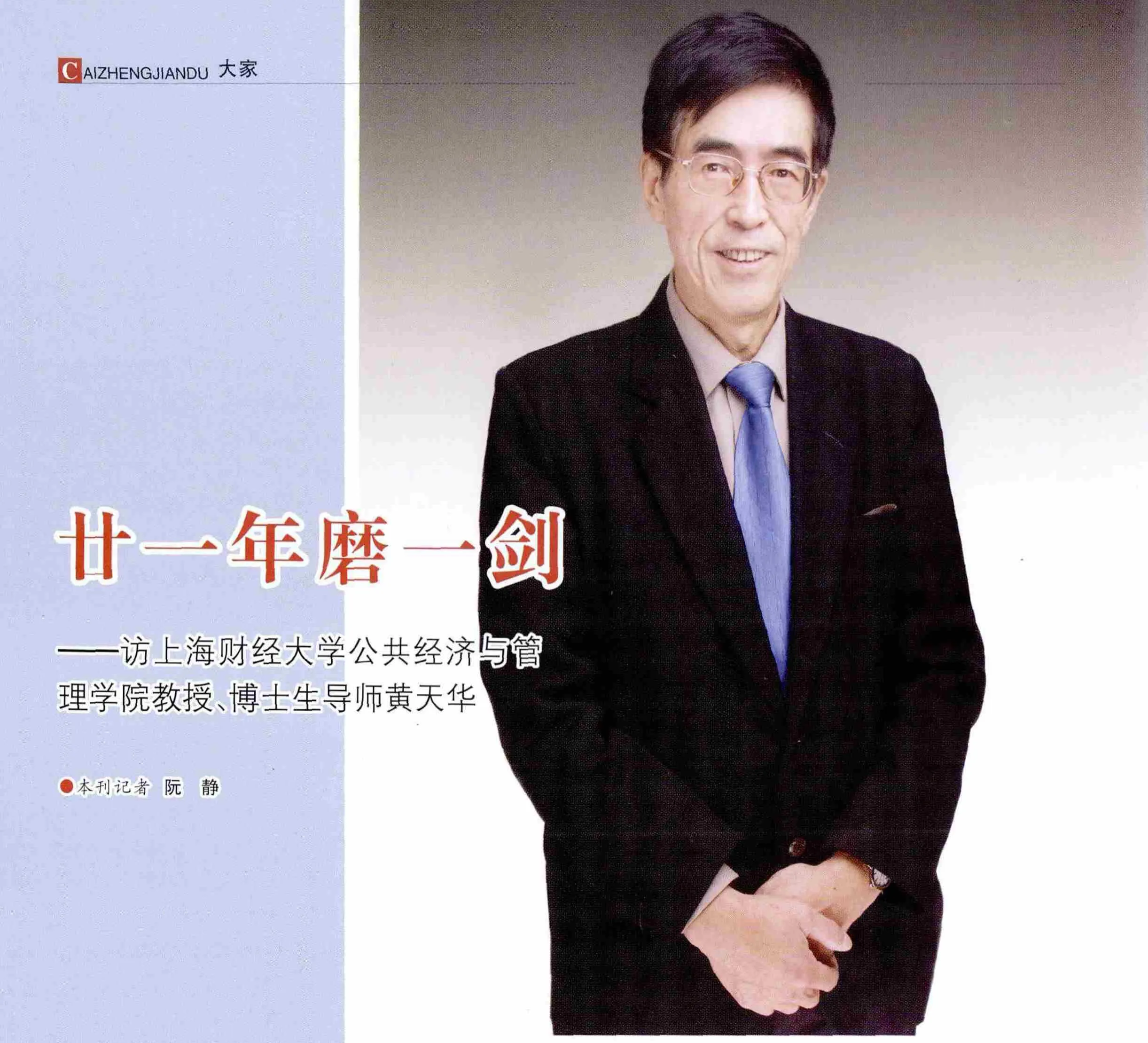
黄天华,江苏泰兴人。1983年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毕业。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财政史纲》、《WTO与中国关税》、《中国税收制度史》、《原始财政研究》等。1987年,获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高等教育局“教书育人”先进教育工作者奖。1989年,获财政部、中国财政学会“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奖”成果奖。2008年,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在上海财经大学凤凰楼里,有这样一位学者,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天都在伏案写作,用他自己时间的算法,即从旧历大年初一到这一年的大年三十,都在办公室——于他而言是书房——著述写作,唯一的调剂就是到楼下边散步边思考问题。学校离家很近,他却总忘记归途,甚至走路时会常常撞到脑袋——似乎唯有这样的时刻才让他从沉浸的学问里暂时抽离出来回到现实中。
他是黄天华老师,一位中国财政制度史的教育者、研究者,更多的是探索者。
在当下我国,财政史学显然不是一个热门的学科,甚至一度出现过该领域的研究人才匮乏的危机,但对黄老师而言,却是毕生所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考制度刚刚恢复,黄老师通过了考试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再回校园学习,并留校成为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老师。他对历史学的执着和热爱,使他看到了财政与历史的契合点:财政史——财政制度史,成为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
而今,黄老师潜心于书斋治学已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最热闹、最繁华,并充斥名利诱惑的三十年,他却一头扎进古老中华民族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在中国财政制度史领域里默默地耕耘。
研究“原始财政”第一人
直到今天,黄天华老师仍然清晰地记得本科读书时第一节财政学课上,老师提出了“财政从哪儿来”的问题。他被深深地吸引住:财政怎么产生?为什么要财政?或许就是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此改变了他的志向。限于刚恢复的上海财经大学各方面条件,他为了钻研此问题,除了上课就是往返于上海市图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浩瀚的书海中,努力地汲取相关的知识,对科学的不懈追求及在专业领域的艰辛跋涉,使他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在财政史研究领域,财政起源是一个难度较大,同时又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当代,学界自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流派。黄老师于三十年前发表了《论原始财政》,首提“原始财政”的理论,并就财政起源问题做了深入且有分量的研究。
黄老师认为,财政起源与国家起源是一个同步的渐进过程。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形态在其形成过程中,财政的运动过程始终与其协调一致,紧密相连。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财政与国家的运动过程具有同一性”或两者是同步的。显然,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发展的高级形态是财政分配得以从一般经济分配中独立(或分离)出来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一独立(或分离)的过程,无疑就是财政起源的过程。因此,只要存在形成中的国家就必然存在形成中的财政,国家形态的发展与财政范畴的演变确实具有同一性,其形态只不过表现为雏形的国家和原始财政而已。故而,也称之为原始财政。在黄老师看来,财政之根源是经济关系,财政之本质是公共权力之集中收支,财政之特征是基于公共权力的强制性,这是其研究原始财政的出发点;他以动态粗线条的形式勾画出财政的运动过程:一般经济分配中的强制性因素→一般经济分配中的强制性分配→一般经济分配与强制性分配(即财政分配)分离,国家财政形成;并勾画出与此相适应的是公共权力的演变过程:一般公共权威(前氏族社会)→氏族民主政治(母系氏族社会)→家长制(父系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或王权政治(农村公社时期)→国家政治(阶级社会),最终得出这样的观点和结论:“财政形态的运动过程与公共权力的运动过程是同步的,当财政分配融合于一般经济分配之中时,就如同十月怀胎,而公共权力的高级形态——国家,正是它的‘助产婆’,这就是财政起源与公共权力的辩证关系;也是原始财政范畴独立和出现的过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老师赞赏他“勤奋而执著,耐得住寂寞”,并鼓励坚持“这种难能可贵的学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全国财政史研究中心主任赵云旗老师评价道:“这些新观点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为持续深入地讨论“财政起源”问题,黄老师就这一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综合性考察和研究,并接连刊发了《再论原始财政》、《三论原始财政》和《四论原始财政》。这些理论比较系统地佐证了财政起源即原始财政的基本观点。同时,黄老师也从实证角度切入,发表了《论中国农业税的起源》、《论中国关税的起源》、《论中国商税的起源》、《论中国盐税的起源》以及《论宗教税课的起源及发展》等论文,从各个侧面论述和佐证了原始财政的基本观点;继而又发表《论夏商周三代税制结构及其发展》、《论秦代税制结构及其发展》、《我国早期赋税制度综述》等论文,最终基本构建起“原始财政”的框架体系,成为学界少有的就财政起源问题勤耕细作的研究者,堪称研究“原始财政”第一人。
回头来看,正是当年对财政起源问题的浓厚兴趣以及其后多年对该问题的“穷追不舍”,让黄老师获得了财政部、中国财政学会“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奖”等学术奖项的肯定,于原始财政问题研究上终有所成。
“我写每一本书都有‘制度’二字”
写就我国第一本断代财政史,即《汉代财政史》的马大英先生、亦为黄天华老师求学读研期间的财政史导师,他曾于1980年在其著作中写道:“财政上所反映的阶级关系,敏锐而透彻,纤毫毕现,它是整个历史的一面明彻的镜子。财政史当然首先要述明一代史实,然而却不能停留在典章制度的陈述上,那将是一堆死气沉沉的故纸;而是要通过财政史实,探索一代政治的治乱安危,民族发展的盛衰隆替,寻根究底,穷本溯源,说明白几个为什么!”
尽管这段话仍带有当年的时代特征,但依然可窥出财政史及其研究的意义所在。而通过财政史实“说明白几个为什么”,正是一代代财政史学研究者的治学出发点和落脚点。黄老师专注于财政制度史的研究,他认为“制度”才是更能“说明白几个为什么”的关键!尽管财政制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在黄老师眼中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财政制度都有其功过得失,系统地总结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财政制度,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今天的财政体制创新和税制改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采访中,黄老师直言财政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财政的涉及面太广泛,凡是与“钱”有关的事情最后都会归结到财政制度上,如“军费”、“行政”、“官俸”、“文化教育”、“公共工程与公共事业”、“社会保障”等国家开支且不说,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工资”、“理发洗澡”、“亲属聚会”、“外出旅游”、“打电话发信息”、“小商小贩”等,包括眼下反腐败、反裸官、“打老虎拍苍蝇”都和财政制度密切相关,“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因此要‘说明白几个为什么’就务必从制度入手契入财政史研究。”
实际上,黄老师的每一部著作都与制度有关,从《中国财政制度史纲》、《中国关税制度》到《中国税收制度史》以及正在审阅即将出版的《中国财政制度史》都立足制度研究、探研财政得失。其中2007年出版的《中国税收制度史》在学界广受好评,这部近200万字的专著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第十四届“中振基金优秀专著奖”、上海财经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多项有分量的学术奖项,著名财政学家许毅教授为此书题词“以史为鉴,发展创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老师为此书作序,对这一研究成果评价颇高,而且对黄老师勤奋执着的治学精神赞赏有加。
多年来研究财政制度史也让黄老师形成了从制度角度分析问题的思维习惯。采访中,他不仅详述了“上计”这一历史上的预决算制度对当世的借鉴,也就笔者所关心的财政监督问题从制度本身、内容完善、整体配套等多层次提出改进建议。“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黄老师引用了邓小平这句话来进一步说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写每一本书都有‘制度’二字,就财政问题而言,制度研究是探研得失、鉴往知来的根本”。
廿一年磨一剑
《中国财政制度史》是黄天华老师多年来梦想完成的著作,他从1992年动笔以来,几十年沉于史海,日日夜夜,辛勤笔耕,立志为五千年来财政制度作一系统总结。
黄老师说,上海财经大学的第一节财政学课,影响了他的志向;而他的导师马大英老师影响了他的一生。马老师曾经跟他讲过很多有关财政史研究的感人经历,让黄老师特别难忘的是这样一个场景。一次,马老师讲道:“中国财政史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的前面,远远超过了我们!”这让黄老师颇为震惊:研究中国财政史,外国人走在中国人前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马老师进一步对他说:“如果你愿意毕生从事这个事业,以后你会详细知道的。”此后在黄老师研究写作《中国财政制度史》的过程中,从宋代开始,这一问题就慢慢显露出来,如宋代财政经济史研究,日本与法国占先;至于清代、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财政经济,更是以美国为中心。黄老师本人在研究清后期、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财政时的一些资料,正是由他所在学院外籍院长从美国大学复印而来。“这是我们民族带血的创伤,是难以忘怀的”,在中国财政史研究上中国自身反而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事实自与马大英老师的那次谈话起就刻在了黄老师的心上,让他立志一定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为祖国争一点光——“这是我的心愿”,黄老师强调道。
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有个著名的观点:契入历史,财政经济正是一把钥匙。黄老师正是紧紧撰着这把钥匙几十年如一日治学财政史。眼下,《中国财政制度史》即将付梓出版,这部五百余万字的四卷本著作除去资料文献搜集和准备工作,自动笔至今日,已花费他本人整二十一年时光。在黄老师看来,以这样一部著作系统梳理我国五千年财政制度是历史赋予他这一代人的责任,“我能够有幸执笔写作五千年的财政制度,就必须竭尽全部心血和精力,给社会留下一粒铺路的小石子,因为我爱我的祖国。这不是随口而言的,二十一年的时间,让我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多么厚重。”在采访中,黄老师曾饱含深情地说道,在他这部新著的扉页上,一定会赫然写着“谨把本书献给我的祖国!”

马克思曾有言:“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我们姑且不论于学者而言何谓“光辉的顶点”,仅此“廿一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已然是一抹光辉启迪着后来人。
“我是否能为后人留下一粒铺路的小石子”
原始财政研究是黄天华老师治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而为五千年财政制度作一系统总结则是他治学的夙愿。“我原本打算用十五年时间完成这部《中国财政制度史》,虽然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当我一旦执笔时,自己还是被震慑到了,财政问题太复杂了,我面对着一个又一个非常具体而自己又不熟悉的领域”,谈及这部新著的写作历程,黄老师说道。紧接着他向笔者细数起五千年财政制度史研究展开时遇到的困难——
“当我研究军费开支时,我就必须深入军事学领域,否则根本无法下笔;研究行政开支,就必须深入国家机关的组成与运转领域;研究官俸开支,就必须深入了解国家官员设置,行政级别及薪金政策;研究教育开支,就必须深入了解各类教育机构设置,教师的配备及薪金政策;研究公共工程开支,就必须深入了解各种农田水利、建筑、航运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社会保障开支,就必须深入了解自然灾害规律、社会救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研究宗教开支,就必须深入了解宗教常识、布局、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大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起源与传播;宗教从来就和财政捆绑在一起,还要了解汉传佛教的政教分离,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这都给财政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必须大量补充搜集这些方面的文献资料。”
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在当世的认知和研究都实为不易,何况当这所有的问题铺陈在五千年文明中,其研究难度可想而知;更进一步来看,财税涉及历朝历代的政府收支,本身即为一门精细的学问,当这门精细的学问置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则更加务求清晰严谨准确,而对财政史学研究者来说欲达到此要求则难上加难。尽管五千年中国财政史的研究一直在我国学界进行着且不乏通史类研究成果的推出,但这些成果由于受时代、技术、文献、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往往将某一税种或某一项政策法令笼统地搁置在一个模糊的历史框架内,以致于中国财税制度研究中常出现“关公战秦琼”的现象,例如仅盛行于东晋南朝各代的“估税”,在很多财政史专著中却被笼统地划入前后三百余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大历史时期,不免失之严谨,既难以准确反映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的税制特点,也不易厘清具体税制的来龙去脉——“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等并列写作于史学界行得通,于我们财政史学界就待商榷了,因为财税涉及具体时期具体朝代的收支问题,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交代、收上来的每一分钱也要交代,几百年的财税问题若并在一起写作在我看来是不妥当的”,黄老师直言,“某一财税制度的起源、发展、直至今天是怎样一种情形要全部界定清楚,这件事完成了我们后人才方便做进一步研究,否则就是一本糊涂账。”而他的这部新著致力于解决的正是杜绝中国财政制度史研究中的“关公战秦琼”的现象,让“糊涂账”不再糊涂、为后人留下一部精细清明的《中国财政制度史》。
“这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件小事,但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黄老师说道,而为完成生命中的这件大事,他甘愿投入二十一年时间于书斋枯坐、潜心治学,因为他坚信一旦决心提笔从中华文明源头起顺流而下梳理厘清历代财政制度,就必须投入以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正如他认为自己有幸站在高等学府的讲台上教书育人,就必须竭力发出人生最大的生命和精力的价值,哪怕只闪烁一丝微光——这已是当世所稀缺的一种治学信仰,尤其在他本身受到病痛折磨却依然坚持写作、半世清贫却从不问名利的情况下,这种精神更加可贵。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说:“爸爸一生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地球上能够留下一个痕迹,那将是我最大的满足。”
新著《中国财政制度史》即将付梓,二十一年、四卷本、五百余万字注定这是一部虽含辛茹苦但值得期待的重量之作。而过程之艰,在此一刻于黄老师而言也已不足为外人道,反之他更多地感念一路上给予他支持的同事、同行,“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自己无法在这条路上执着地走下去。”
而说起对新著的期待,黄老师表示“我是否能为社会或后人留下一粒铺路的小石子?仅此而已”。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姜斋文集》里的一段话:“阳禽回翼,地远天孤;一线斜阳,疑非疑是。”这位一生颠沛流离的晚明后人,虽处家国破碎的境地,却如一只鸿雁,望着前方的一丝光亮,在地远天孤间虽疲惫但执着地飞去,终为后人留下宝贵且灿烂的思想财富。黄天华老师也一如那只鸿雁,向着自己的学术理想,不畏治学之艰,廿一年磨一剑。
(本栏目责任编辑:阮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