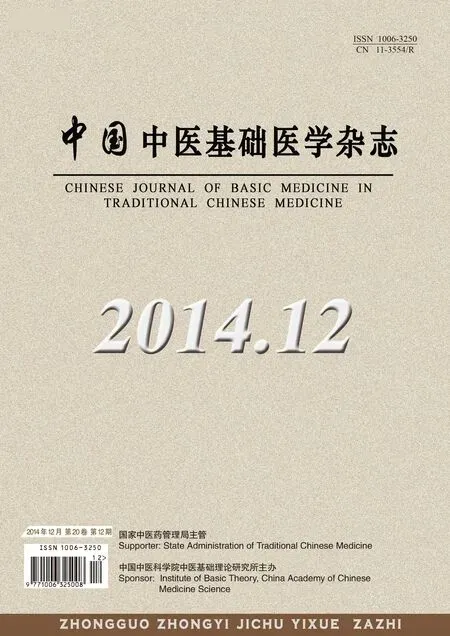清代医家戴天章温病辨治特色探析❋
2014-01-25孙大中岳冬辉
毕 岩,孙大中,岳冬辉△
(1.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2.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 510006)
中医学对温病的研究,不仅体现在对病因与发病特点的认识上,而且体现在辨证与治疗规律的把握上。清代医家戴天章对于温病辨治问题的独到见解与临床经验,一直深受重视。因此,探析其临床辨治特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戴天章,字麟郊,晚号北山,江苏江宁人。少习举子业,尤精于医学,擅治温病,学术思想宗于吴又可。生平著述颇丰,但多遗失或未刊行,其现存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为《广瘟疫论》。该书临床实用性强,对后世瘟疫的防治以及温病学说的发展、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1 鉴别寒温5种辨法
戴天章对吴又可的《温疫论》推崇备至,对瘟疫的病因倡导吴又可的“杂气论。”戴天章认为瘟疫与伤寒鉴别之要“尤慎于见证之始”,提出着重从气、色、神、舌、脉5个方面对瘟疫与伤寒加以辨别。
1.1 辨气
辨别患者呼吸、分泌及排泄物所散发出的气味。戴天章通过闻诊对患者的呼吸、分泌及排泄物所散发出的气味进行辨别,以鉴别温病与伤寒。他认为,风寒邪气伤人而为病,一般不会有臭气触人,如有也必是有热入阳明而成为热腐之气,但不作尸臭气。瘟疫乃大地间之杂气,属败气、秽浊之气伤人,侵及人体,由秽热蒸腐气血津液而成,故气味多尸臭味,其不同于一般之臊、腥、焦、腐之气味。他认为:“风寒,气从外收敛入内。病无臭气触人,间有作臭气者,必待数日转阳明腑证之时。[1]”尸臭气触人不可名状,“轻则盈于床帐,重则蒸然一室”[1]。 只要医生注意鼻子嗅觉灵敏,就可分辨得出。其临床表现,酸臭者多属湿热郁蒸;口气臭秽喷人者,多为阳明腑热;有血腥之气,多见于热入血分迫血妄行。
1.2 辨色
戴天章指出:“风寒,主收敛。敛则急,面色多绷急而光洁。瘟疫,主蒸散。散则缓,面色多松缓而垢晦。[1]”外感风寒之邪,使皮肤收敛,故面色多绷急;湿热熏蒸、气机郁阻面色多显黄滞;阳明实热面色多红赤并以午后为甚;而温疫乃秽热之气,其主蒸散,故面色垢晦而松缓,如烟熏、油腻,多为疫邪熏蒸津液上溢于头面所致。
1.3 辨舌
风寒在表,舌多无苔或白苔亦薄而滑,邪传入里,则苔由白而黄、由黄而燥、由燥而黑。瘟疫初起,舌苔多白厚不滑,或粗如积粉,及至转黄黑亦不燥,由秽浊之气入胃,胃津腐瘀所致。正如吴坤安言:苔形粉白而厚四边绛者,此温疫证也。戴天章指出:“若传经入胃,则兼二三色。[1]”因此,观察苔色变化时,注意苔之燥润至为关键。因临床 “又有白苔即燥与至黑不燥者”[1]。如至黑不燥者多兼湿浊,若黑而粗涩、舌体裂纹或兼珠点等特点,不可误为阴寒里结之症。
1.4 辨神
由于瘟疫乃天地间秽热之疠气所致,且心为火脏,故疫邪内袭极易神明受扰而见神志异常之症。如烦躁惊悸,昏昧不知所苦,梦寐不安,闭目即有所见,继则神昏谵妄等。如:“瘟疫初起,令人神情异常,而不知所苦。大概躁者居多,或如痴如醉,扰乱惊悸,及问其何所苦,则不自知,即间有神清而能自主者,亦多梦寐不安,闭目即有所见,有所见,即谵妄之根。缘瘟疫为天地邪气,中人人病,中物物伤,故其气专昏人神情也。”[1]戴天章提出温疫初起即会出现心主不明之神志异常的证候表现,为后来叶天士提出的温邪“逆传心包”理论奠定了基础。
1.5 辨脉
主要辨析风寒与瘟疫初起脉象之异。戴天章认为:“瘟疫之脉,传变后与风寒颇同,初起时与风寒迥别。[1]”伤寒初起脉多浮,或兼紧,兼缓,兼洪而皆浮。传里后则不见浮脉,其至数必清楚而不模糊。而瘟疫病变乃伏邪为患“从中道而变,自里出表,一二日脉多沉,迨自里出表,脉始不沉,乃不浮不沉而数,或兼弦兼大,而皆不浮,其至数则模糊而不清楚”[1]。因疫邪由终原分传表里,秽热之气蒸散,脉不能鼓指,故至数模糊不清。故戴天章指出与伤寒不同,瘟疫初期若见沉迟之脉,则要注意从气、色、舌苔、神情等方面加以辨析。戴天章强调四诊合参、不凭脉独断的思想是极其符合中医临床实际的。
辨别气、色、舌、神、脉5个方面是戴天章从其长期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瘟疫与伤寒初起的鉴别要点,不仅有利于对伤寒、温病的辨别,更有助于温病的临床辨治。其内容虽未尽善,尚有局限性,但确实发展和丰富了温病的诊断内容。
2 辨治温病兼夹证
戴天章对于温病兼夹之证的辨治尤为重视,总结出五兼十夹证,所谓五兼即兼寒、兼风、兼暑、兼疟、兼痢;所谓十夹即夹痰水、夹食、夹郁、夹血、夹脾虚、夹肾虚、夹亡血、夹疝、夹心胃痛、夹哮喘,并对此五兼十夹证提出了相应的治疗原则与方药。经其对瘟疫兼夹证的归纳,其内容更加系统完整,纲举目张,便于理解与运用。
2.1 瘟疫兼证的治则与方药
瘟疫兼寒者,当辨其疫与寒孰轻孰重。若疫重寒轻者烦躁症多,无汗恶寒症少,则当以败毒散加知母、石膏,或达原饮加羌、防、柴、葛,或六神通解散。若寒重疫轻者恶寒无汗必甚,烦躁必轻,则只用败毒散,或大青龙汤,或九味羌活汤。若治寒遗疫,必有斑、黄、狂、衄之变;治疫遗寒,复有厥逆、呕利、胸腹痞满之忧。瘟疫兼风者,反令病势易解。因寒主凝泣,则疫邪内郁,郁一分,病势增一分;风主游扬,则疫邪外疏,疏一分,病势解散一分。即于时疫诸方中的荆防,咳加前胡、杏仁、苏子而已。瘟疫兼暑者,汗出更多,两邪逼出表汗则表必虚,故发表之味不可重复也。治法于时疫诸方中,微减发表之味,如用羌即不用独,用柴即不用前。因邪从表出,郁热必轻,故又不可过用清凉寒润,最宜加用分利燥脾之品,如木通、滑石、猪苓、赤苓、泽泻、香薷、苍术之类。瘟疫兼疟者,寒热有常期,疟症全具,但热多寒少,且多燥渴扰乱,热势迅速,神情昏愦,秽气触人,多发于秋季,治宜达原饮加柴胡为主。后期邪退正复,可酌用小柴胡汤、柴胡四物汤、参胡三白汤等方加减。瘟疫兼痢者当分表里,若疫痢初起,表证阶段,当以人参败毒散加陈仓米(即仓廪汤)败毒散解表,加陈仓米以和中养脾胃。俟表证解后,里热症具,方可议清议下。若疫痢介于表里之间,微见少阳、阳明证者,则可借用柴葛五苓散。
2.2 瘟疫夹证的治则与方药
夹证与兼证有别。兼证是疫邪兼他邪,夹证是疫邪夹内病,情况比较复杂,需视具体情况而定[2]。瘟疫夹实,有夹痰水、夹食、夹郁、夹蓄血之不同。在治疫邪时必须当先考虑祛夹邪,夹邪祛则疫毒始得透达,否则影响疗效。夹痰者,于治疫药中加栝楼、贝母甚加牛黄。夹水者,于治疫药中加辛燥、利气、利水之品。燥湿则半夏、苍术,利气则莱菔、草果、木香,利水则木通、苓、泽,甚至有须用大戟、芫花者。夹食者,需视宿食停积部位不同而处以不同治法。食入肠胃之阳明诸证,治法备于三承气汤下之;若食积胸膈之上,则于治疫药中加枳、桔、青皮、莱菔、曲之类,甚则用吐法以宣之,使胸膈开而阳气宣达,然后热症自见,当解表,当清里,自无误治矣。夹郁者,于治疫药中加苏梗、木香、大腹皮、香附等类,以宣其气,舒其郁,则表易解,里易和。夹蓄血者,治法必兼消瘀,加红花、桃仁、归尾、赤芍、元胡之类,量加一二味。瘟疫夹虚,有夹脾虚、夹肾虚、夹亡血之不同,当治疫邪为主,养正补虚为辅。因疫邪最易伤正,故不可养正而遗邪。夹脾热者难治,因时疫必得汗下而后解,脾虚则表不能作汗,里不能攻下,或得汗而气随汗脱,得下而气从下脱。其治疗发汗勿强其汗,发表必兼养正,可选人参败毒散;攻下勿妄其下,攻里尚需兼顾气阴,可选黄龙汤。若夹肾虚者,其证更加复杂。由于时疫之邪必待汗、下、清而后解。肾阳虚者,一经汗、下、清则阳气脱绝之症随见,肾阴虚者,一经汗下则阴精枯竭之症力显。可于通表药中加人参、白芍,阳虚兼杜仲,阴虚兼知母;入里当下必以陶氏黄龙汤为主,当清必以人参白虎汤为主。夹亡血者解表清里,用药必步步照顾荣血。如九味羌活汤之用生地,人参败毒散之用人参,达原饮加用人参等。瘟疫夹宿疾,有夹疝、夹心胃痛、夹哮喘之不同。此时应当但治疫邪,疫邪去则旧病自已,或再治旧病不迟,因疫邪为急,急则治标,多数宿疾乃疫邪所诱发也。如夹疝者,但治疫而疝自消,若依常法治疝,用吴萸、桂、附、茴香诸燥品,轻者变为囊痈,重者呃逆哕厥沉昏而莫救矣。如夹心胃痛者,可于达原饮中加木香、苍术以开通郁疫,使其透发于表,而痛自已;若误用桂、附、姜、萸,以致危殆。如夹哮喘,亦但治疫其哮喘自除,或于治疫药中加贝母、栝楼、淡豉、桑皮、疫邪哮喘并解。
3 创立治疫五法
戴天章提出了治疗瘟疫的汗、下、清、和、补五法,并着重阐述其在治疗中的意义,进而使温病的治疗趋于完善。
3.1 汗法
戴天章运用汗法主要有以下观点[2]:一是主张“温病汗不厌迟”,强调汗法应用之时机;二是在乎“通其郁闭,和其阴阳”,强调温病汗法应用的目的。因其所观察到主要是里热郁蒸之温病,故在里热出表而邪郁肌腠之际,可采用辛寒、辛凉之剂通其郁闭以清热透邪外达;若仅是里热而无怫郁肌表之见症,则只需清其里热而无需解表,故有“汗不厌迟”之谓也。如属温邪在表之新感温病之候,应及时采用辛凉透表之法,使温邪从汗而解。若亦拘此“汗不厌迟”之说,反致病邪传里生变。
3.2 下法
戴天章运用下法的论点[2],一是强调“下其郁热”,二是主张“下不厌早”。他认为温病里热郁蒸,当苦寒下夺,以釜底抽薪使郁热有外泄之机,故“伤寒下不厌迟,时疫下不厌早”。伤寒在下其燥结,时疫在下其郁热。伤寒里证当下,必待表邪全罢,时疫不论表邪罢与不罢,但兼里证即下,伤寒上焦有邪不可下,必待结在中下二焦方可下,时疫上焦有邪亦可下。此伤寒下法与温疫下法之不同。温疫下法有六:结邪在胸上,贝母下之,贝母本非下药,用至两许即解结邪在胸及心下,小陷胸下之;结邪在胸胁连心下,大柴胡汤下之;结邪在脐上,小承气汤下之;结邪在当脐及脐下,调胃承气汤下之;痞满燥实三焦俱结,大承气汤下之。此外,又有素体虚弱,或老衰久病,或汗下之后,虽具下症而不任峻攻者,则麻仁丸、蜜煎导法、猪胆导法为妙。分症的细密,可体会到他治温病的临床造诣之深。“温病下不厌早”说为很多医家所赏识。临床证实,一些急性热病及早运用下法,或与其他方治法配合使用,确可达到下其郁热、泄其毒邪等作用,可缩短病程,提高疗效。但临证亦不可拘泥此法,并非凡是温病皆可滥用攻下,这主要是针对热郁于里的温病而言,若属温热在表之证,决不能早用攻下。
3.3 清法
戴天章重视清法在温热病治疗中运用,他指出:“时疫为热证,未有不当清者也。其在表宜汗,使热从汗泄,汗法亦清法也。在里宜下,使热从下泄,下法亦清法也。”[11]1144,1145他还提出温病“当清者十之六七”[1],认为温疫多为热证,未有不当清者。若邪热在表,已汗而热不退,或邪热在里已下而热不解,或本有热而无结,则惟以寒凉直折,以清其热而已,并认为汗、下、清三法可合亦可分。时疫为热证,在汗、下后热邪流连不去,或本来有热气结,此时则惟以寒凉直折以清其热。凡清热之要,仍需视热邪之深浅、病位,酌加汗、下及适当药物,三者可合亦可分,理法方药应用灵活。热之浅者在营卫,以石膏、黄芩为主,柴胡、葛根为辅;热之深者在胸膈,花粉、知母、薏苡仁、栀子、豆豉为主;热在肠胃者,当用下法,不同清法或下而兼清亦可;热入心包者,黄连、犀角、羚羊角为主,直入心脏则难救矣,用牛黄尤可十中救一,须用至钱许,少则无济。戴天章所用清法主要是取辛寒、苦寒之品,对于热郁气分或化火者甚为恰当。
3.4 和法
戴天章所称和法是指调和之法,而非和解少阳,他将相互对立的几种治法同用即称为“和”法[2]。即寒热并用谓之和,补泻合剂谓之和,表里双解谓之和,平其亢厉谓之和。寒热并用者,因时疫之热,夹有他邪之寒,适逢时疫之邪气实,人之正气虚之际,故用补泻法以和之,如其方中黄芩与半夏并用,黄连与生姜并用,知母与草果并用,石膏与苍术并用者皆是;表里双解者,因疫邪既有表证又有里证,故以此法而和之,如其方中麻、羌、柴、葛与黄、硝、芩、栀、枳、朴配伍合用者皆是;平其亢厉者,时疫之大势虽去而余邪未解时,选用下法少其剂量缓其峻,或选用清法变汤剂为丸散剂缓其时日,故亦成为“和法”。由此可见,戴天章所论之和法,实寓汗、下、清、补诸法综合运用之意,亦是疾病在常与变过程中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具有“乱中整合,调营卫,和阴阳”之理。
3.5 补法
戴天章补法包括补阴以济阳,补阳养正以祛邪。温邪致病固然伤阴者多,亦有因寒凉太过而致伤阳者。他认为:“时疫本不当补,而有屡经汗下清解不退者,必待补而愈。此为病药所伤,当消息其所伤,在阴在阳,以施补阴补阳之法。[1]”并在《广瘟疫论》中提出:“凡已经汗下清和,而烦热加甚者,当补阴以济阳……当其汗下清和,热退而昏倦痞利不止者,当补阳,所谓养正以却邪者是。[1]”《广瘟疫论》中还列举了15种当补阴证和7种当补阳证,补阴宜六味地黄汤、四物汤、生脉饮、养荣汤等诸方为主,补阳宜六君子汤、建中汤、附子汤、理中汤等诸方为主。邪热耗伤肺胃阴津,或罹及下焦灼损肝肾之阴者,治宜滋阴补液;若因邪盛正衰,或患者素体亏虚而致亡阳厥脱者,则虚回阳固脱。可见,戴天章“补阴补阳,又当酌其轻重,不可偏废”[1]之说甚合临床实际。
综上所述,戴天章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对温病辨治问题做了深入思考,在温病学理论上有新的建树,其学术思想上承吴又可之学,并影响杨栗山、余师愚和吴鞠通等温病医家,丰富充实了温病学内容,对后世温病学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虽然戴天章对温病辨治所形成的独到认识及其所论之“瘟疫”与吴鞠通“瘟疫”的概念和范围上不尽相同,但其所阐述的诊治方法和辨证内容对于瘟疫的治疗尤其是对于温病治疗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和意义。
[1] 李顺保.广瘟疫论·温病学全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117-1118.
[2] 岳冬辉.温病论治探微[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92,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