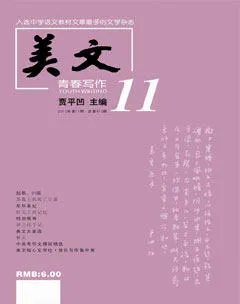故乡的茶味
2013-12-29丁威
说到茶,我还年轻,没有见识过许多茶味,难免捉襟见肘,舌尖滑过一片茶,说不清道不明是哪种,只知那一种泥做的水样的东西,留在唇齿间,将人往空明的高处升。四月时候,清明到谷雨,正是新茶时节,蛰居一冬的,探出脑袋,又赶上这样好听的节气名字(节气的名字都藏韵,如芒种、入梅、白露、雨水)。嫩芽,指头一掐,是一痕油油的茶绿,嗅,躲不掉的清香,嚼,苦涩又回甘。用唇采茶,不伤其嫩,可看做一张嘴的欲说还休,含着力,试探,用唇的柔软包住茶的嫩,舌尖扣住,扯呢,也是缓,回力的劲道,摘取云朵似的,如一朵雾似的小蜂采蜜,一片毛尖就被采下。而后的工序我不甚明了,道不出一三五,就留给那些熟稔茶之道者,我所说的是端上桌面的那一道味,云蒸雾绕时候,那一片茶里的心绪。
前年,我还藏在北京的湿寒里,衣物不够,又没暖气(后来买了几瓶二锅头,冷的时候,就喝上几口),和同学藏在一间不足5平米的房间里,由于房子的格局问题,终日不见阳光,关了灯,闷上被子,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又没有找到,每日就是上网投简历,期盼着有一家公司的垂青,而后便是在漫天的风沙里,赶上几班公交,倒转几线地铁,迎接别人一次次的目光打量,闻讯,将那些烂熟于心的自我介绍添油加醋地倒腾给别人,像年轻时候的海明威在巴黎一样,想要用手敲敲木头,期待好运气的降临。
找了近一个月的工作,手头的钱眼见着少,日子却只是无望。印象中北京的天气一直不好,风沙吹得外面一阵阵嚣叫,杨树早已落尽它最后的叶子,触目皆不见绿色,只剩灰,天空自不必说,就是人脸,也是倦怠的灰蒙蒙一片,那些街边的站台、闪烁的车流灯光、灯火摇曳的娱乐、入夜后依旧拥挤的地铁……构筑着北京的旷远、间隔、距离。
那一个圣诞前的夜晚,和同学穿行在繁华的三里屯,彩灯挂满了视线,用城市的妖娆撩拨外乡人的心弦,几乎是疼痛的。走一路,只一路的沉闷,说不开心,眉头几乎成一副锈蚀的锁,任谁也无从打开。你期待什么呢,期待北京这个城市收留你,它是祖国的首都,是心脏,血液从这里出发,它意味着新生、时尚、活力、跃动,等等等等,想象它的广阔天地,那些年轻的骏马啊,扬起你的蹄瓣,抖擞你的鬃发,将你青春的嘶鸣响彻,前方一望无际,我年轻的骏马要驰骋千里,几乎是嚎叫,几乎要热血回流,几乎将重整河山待后生。拒绝抒情的年代,想起浪漫自由主义的八零年代,说到北——京——,你也要在零度的冰冻里抒情,说一说梦想的北京,说一说理想主义花朵般的北京。
可是啊!你相信北京有驰骋的沃野千里,你也要相信,北京有生硬的拳头、有冰冷的拒绝、有干涩的冷漠、有物欲的盲肠……那个夜晚,和同学几乎绕尽了大半个三里屯,走到最后,只剩一口一口地喘气和叹息,后来,你简直要分不清哪些是喘气哪些是叹息了,我苦笑着对他们道: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啊!心里想的尽是:回家,还有那一床温暖收留我,一碗热粥,种下我的眼泪。
父亲打来电话了,还有母亲,手机放在耳边,我觉得隔着好远啊。母亲依旧絮絮叨叨,他瘦弱不堪的儿子啊,北京的湿寒是否侵蚀他,哪一阵冷风吹他,哪一块砖石硌疼他,有没有一碗饭喂饱他的肠胃,那些烈酒是不是还在熊熊烧着她儿子的疼痛,那些失眠的夜晚是不是还在折磨着他衰弱的神经;衣服暖不暖、被单厚不厚,冷风过时、冬雪降时,他的儿子躲在哪里?母亲在电话那头长吁短叹,好像她的儿子就要被北京打败,狼狈、脆弱,好像全世界的暖都抵不上让她看见我,看见了心里就踏实了。她说啊:你不在跟前,我瞧不到你,我哪能放心得下,北京那么冷,你年轻又不管不顾,只知道消耗,我哪能安心,每夜我睡不着,就只是想你,你是我儿子啊。父亲接过电话,一阵沉默,责怪我到北京也不跟他们打声招呼,我还嘴硬,说自己大了不想拴在他跟前,又一阵沉默:问我钱够不够,北京天气寒,和家乡不同,别仗着年轻,就拿筋骨去扛,我说:我知道。手机里是长久的呼吸,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的沉默,隔着山似的,沉重,我理解这是爱,我如此固执,硬要撇下嘴,将他的爱生硬地收下,不言语,算作勉强接受。而后,便是短暂地重新梳理一遍嘱咐,忙音过后,我点上烟,回到住处,烟灰结了老长一段,缓慢跌落了。
后来,我在一首诗里写道:他也在异乡,在床榻之上/ 空空洞洞地老去,挂念着你/ 把一点点的温暖收藏/ 故乡的云再飘起来的时候/ 他把爱给你,像小时候田埂上的那些悠长的午后/ 他的烟一直都没熄灭/ 我很小,他也一直年轻。
那些被时光打败的父母亲啊,心藏这样的一个儿子,因为瘦弱、多病、固执,又多加多少心血?!
那间住处的楼下有一个饭店,是老乡开的,我们都喜欢辣,又因为钱少,就只点那两道小菜:小炒肉和醋熘白菜,辣椒只一根,就叫你脸面通红,就要大口灌水。起先老板只有白开水,我们一口一口嚼辣椒,一口一口灌白开水,将在北京的一点感触掏出来,怀念一下过去的岁月,对比下,好像,那些日子一个挨着一个的,都是好日子。
有一天,老板提上来一壶茶水,叶子很宽大,一看便知不是什么好茶,泡久了,汤色是暗的,让人想到说不出话来的那种喑哑的暗,不过,说起来,有茶总好过寡淡的白开水。我们照旧点了如上的两道菜,菜没上来前,我给他和我各倒了一杯茶,刚端起来,因为热气蒸腾,茶味就上来了,多久没喝茶了,感觉的神经立马就察觉到了不同,鼻子闻了下,太亲切了,又闻了下,眼泪几乎要出来,喝了一口,眼睛就脆弱得忍不住了。我跟他说:你尝尝这茶。他看着我湿润的眼眶,尝了一口,没舍得咽,脸上的表情我全都了解。我说:你猜我喝这茶想到了什么?我们几乎同时道出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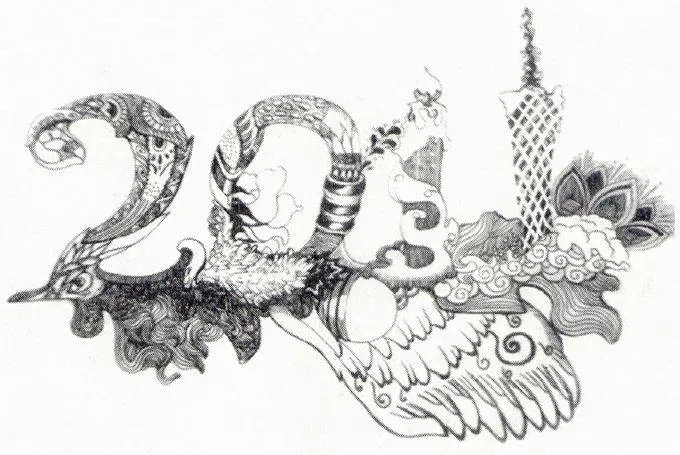
它让我想到了家,更进一点,是爷爷家那些便宜的茶。用瓷缸子泡,放很多茶叶,倒满一大缸子水,盖上壶盖,闷,才不管这是不是一种不好的泡茶方式呢,而后,端起来,喝下一大口,不去品它,咕噜一声咽下去,因为太浓,嘴里就全是苦味,等吧,那些粗劣的甘味稍后就会泛上来,待甘味退去,再灌上一大口,如此几番,一缸子茶就喝尽了。我不说喝茶,那是豪饮,管渴,饿了,甚至管饱。
我们在菜还没上桌前,就喝完了一壶,就又续上一壶,菜也上了桌,一样的一口一口嚼辣椒,一口一口灌茶水,话却少了,似乎那许多话,都融在了家乡的茶里,喝吧,喝吧,家乡话都在茶里,你喝到饱,家乡就像茶水一样流在身体里了,那些家乡的滋味,你要在北京——这个找不到家乡的地方——喝醉在家乡的滋味里吧。
那天,我们吃得特别有味,似乎家乡的茶特别下饭。饭后,我们还坐了一会儿,一人又慢慢地喝了一杯,一点一点地品,是要品出乡音、品出乡味、品出乡愁的那一种,起座的时候,摸摸滚圆的肚子,相互笑笑,就像回家了一样。结账的时候,跟老板说:这茶真好喝,让人想家。老板笑笑,特别亲。
那之后,我们每次去,都要满满地灌一肚子茶水回来,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家乡的茶,成了不系之舟的港湾一般,收留我,给予慰藉,将身心沉在那一丝丝的家乡茶味里,说不出的亲切,道不明的要热泪盈眶。
后来,临近过年,同学要回家,我要孤零零地待在这座并无好感的城市,想到这儿,我也就辞去了工作,和同学一道买了回家的车票,我于北京,灰暗暗地离去,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被打败的兵,算作仓皇地逃离了。
临走前的那顿饭,我们依旧是在老乡的饭店里吃的,吃不够的那两样,桌子上沉默得很,各人在想各人的心思,想着灰蒙蒙的这段生活,是青春里不起眼的一个注脚,再提起,个中滋味,谁能说得清,关于梦想,关于热血,关于生活,我们也许只有沉默的份,就像这最后一顿饭,嚼着嚼着,你都不知道该怎么下咽了,后来就喝茶,想用家乡的滋味冲淡一点什么,可是它又是什么呢?我们说青春啊,这个光明的动词,你哪里能说得出口?
熊培云说: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我后来回想,那在北京的第一口茶,结结实实地烙在记忆里了,想起之前写的一句:对于爱茶之人,茶乡即是故乡。我又回到了故乡,喝到了真正的故乡的茶,有好有坏,滋味不同,却唯独那一种,是叫我沉默地攥紧了茶杯,叫我热泪盈眶。
叫我想跟你说起:漂泊、亲情、故乡、故乡、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