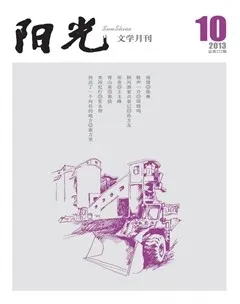到达了一个向往的地方
2013-12-29秦万里
人和人不一样,这是一句废话。说废话不好,我却第二次说了这句废话。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废话有时候就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因为人人都知道,所以大家就认为是废话。被认为是废话的真理,往往会被人们忽略。我重复地说一句废话,是我觉得这句话有用。《阳光》的朋友让我写文章,是给写小说的人看,也是给看小说的人看的,这句话在这样的文章里有用。我在写《不一样的人走进了不一样的笼子》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给启发了,写完这篇文章就更觉得这句话有用了。
有经验的小说家永远孜孜不倦地努力,就是为了塑造不一样的人物。在他们的笔下,不一样的人常常会经历不一样的命运。他们不仅刻画不一样的性格和不一样的形象,描绘了不一样的命运,还体察那些不一样的心灵。这样,他们的小说就更容易成为读者们爱看的小说。
我们且以王小鹰的《点绛唇》为例。
在这篇小说中,王小鹰刻画一位名叫叶采萍的女人。叶采萍是上海人。上海是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是许多外地人向往的地方。叶采萍已经是上海人了,但是她并不满足,她向往上海的淮海路,因为在“那个年代,哪个女人能在淮海路上拥有一间方方正正亮亮堂堂,煤卫齐全的婚房,简直就是公主王妃一等的角色了”。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年代老百姓的住房比现在还紧张。绝不仅仅是住房,还有观念问题。淮海路是上海市的高级区域,“入住者大都是殷实富足的人家,还有不少文人墨客聚集其间”。能够成为这里的居民,自然就是一种荣耀。早在中学时代,叶采萍就向往这种荣耀,她追求同班一位名叫虞志国的男生,虞志国帅,更重要的,虞志国是淮海路的居民。班里的其他女孩子也想追求虞志国,但是叶采萍和她们不一样,叶采萍比她们有心计,也比她们下功夫,后来叶采萍成功地嫁给了虞志国,真的如愿以偿,成了淮海路的女人。“那几年,叶采萍在虞家的日子过得风调雨顺,虽是忙碌,忙也忙得乐陶陶美滋滋。中学的女友常有小聚会,都惊叹她愈发白皙,愈发福相,愈来愈年轻了。交谈之间,叶采萍三句不离虞志国和女儿,从丈夫女儿的吃住行一一道来,描绘得有滋有味,就像端出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小菜,馋得女友们啧啧称羡”。叶采萍满足了,享受着自己心中的荣耀。后来虞志国出国留学的签证又批下来了,这种荣耀就达到了顶峰:“那一晚的聚会,是叶采萍人生中的高光点。她是那样的兴奋。她从同学们的眼神中体会到自己是多么光彩,多么令人羡慕。章梅芳的目光几乎都不敢在她身上停留,匆匆一瞥,也是垂下了眼帘,掩饰住心思。”章梅芳曾经也是虞志国的追求者,但是,阴差阳错的,却让各方面都不如她的叶采萍占了先机。
事实上,叶采萍的荣耀并不真的那么辉煌。“虞家的那幢房子,传到虞志国父亲身上,也只二层楼两间向南的正房了。却有单独的大卫生间,楼梯间也蛮宽势,做饭统在底楼的灶间里,上下十多级楼梯,还算便利”。叶采萍和虞志国结婚了,“虞志国父母便让出小间给儿子做新房。将大间里的餐桌挪到楼梯间,老夫妻俩与女儿隔橱同居一室。直至两年后,虞志国妹妹出嫁搬走,公公婆婆方才住得落定……”人和人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的条件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淮海路上有卫生间的两间房子吗?但是“叶采萍是从打浦桥一带旧式里弄的一间三层阁里嫁进淮海坊的,好比一步登天了”。所以她特别满足,特别感激虞家人给她的一切,“她心甘情愿将虞家里里外外的家务事全包了。清早起来买菜做早饭,下班回家烧饭洗衣裳,厂休日更是一刻不停地扫地抹灰擦玻璃窗,连上下楼梯的扶手都抹得照得出人影”。在虞家,叶采萍并没有享受到多么丰厚的物质生活,虞志国在国外靠打工维持学费,几乎就不给她寄钱,就连一点点爱的表达也十分吝啬,“出去头一年,虞志国十天半月总会给家里一封信,用的都是叶采萍为他准备的信封,收信人自然都是叶采萍。叶采萍先关进自己房间看信,看完了,再去念给公公婆婆听。其实虞志国信里面无非报报平安,问候问候,几乎没有夫妻间的私房话。可叶采萍念信时,总喜欢念念停停,目光在信上来回搜索,以显示有些话是写给她一个人的,不方便公开的”。就是这样的信,叶采萍也要拿到老同学们当中去炫耀,“谁集邮啊?志国寄来的美国邮票你们要不要”。她还要提醒大家:“掀邮票管掀邮票,不准偷看里面的信啊!”好像信里写了多少甜言蜜语夫妻恩爱。
叶采萍放大了她的荣耀,藏起了她的窘迫。叶采萍下岗了,然而“淮海坊人家的生活大都保持一定的水准,进出弄堂,遇街坊邻居寒暄之际,眼角余光只消从你拎着的马夹袋蜻蜓掠水般一扫,便晓得你们家的经济状况了。叶采萍毕竟是淮海坊里的外来人口,底气不足,面子上的这口气,她是万万不可输掉的,便是省也只能省在内里。可是,公婆是省不得的,女儿也是省不得的,能省的只有自己了……”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去找她的老同学章梅芳。人和人不一样,当年也曾追求虞志国的章梅芳早就抛开了情感的纠结,自强自立,成了上海有名的“童装女王”了。章梅芳把叶采萍介绍给一位名叫徐贵棠的老板。其实叶采萍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在徐贵棠那里如鱼得水,很快就成为公司很得力的中层干部。“叶采萍现在薪水比在手帕厂多了将近一倍,手头有了钱,日子就过得鲜活起来。下班回家,到长春食品公司兜一转,两三只塑料口袋装得满腾腾的,走进淮海坊,碰到街坊邻居,喉咙嘭嘭响起来:‘王家姆妈,我买了只牛肘子,煮罗宋汤,尔雅顶喜欢吃了。还有一段银鳕鱼,清蒸蒸,年纪大的人牙口不好,松软一点,刺又少。’”叶采萍说的是上海话,这篇以大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字里行间都溢出了上海方言的特色,这样的语言特色烘托了小说中具有上海特色的上海的人。
王小鹰用具有上海特色的语言刻画一个上海女人,这个上海女人就是一个上海女人,她和重庆女人不一样,和北京女人也不一样,和其他城市的女人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她刻画了一个特别虚荣的上海女人。在王小鹰制造的独特语境之下,似乎是,只有这个生长在上海平民家庭的女人才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她的虚荣心驱动下的种种行为。王小鹰给了叶采萍一份苍白的荣耀,她让她自己在这苍白的荣耀上添加色彩。这一笔一笔勾画出来的虚荣,渐渐鲜活起来了,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个千辛万苦的女人在观念的误区中,进行她“不一样”表演。
叶采萍热爱淮海路,叶采萍的身心已经不能自拔地陷落在淮海路上这个叫做淮海坊住宅区。她的丈夫一走就是七年,她用她的辛劳和智慧坚守着她的荣耀。其间虞志国的妹妹离婚了,带着儿子回来,挤占了她的房间,婆婆让她睡到壁橱里,她竟然还感到庆幸:“叶采萍却先松了口气,婆婆并没有叫自己搬出淮海坊的意思!随即又想,婆婆碰到难处,首先跟自己商量,真是把自己当贴心人了,心口热了起来。再盘算一下,是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不见得自己去跟公婆同居一室啰!一来阿琴也蛮可怜,做嫂子的总要显得大度一点;二来,她阿琴总不会在娘家住一辈子吧?这三嘛,志国明年就要回家,公婆万万不会让宝贝儿子挤在壁橱里睡觉的呀!”王小鹰把小说写到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了叶采萍的另外一面。叶采萍不光是一个虚荣的女人,还是一位贤妻良母,一位好儿媳。但是,当虞志国终于回到上海的时候,竟然不愿意与久别的妻子共度良宵:“爸,妈,我才被公司聘用,这次主要为工作回国,顺带探亲。有个同事同我一道回来的,公司只订了一间房,所以,所以……”已经十分明显了,虞志国是个无情无意的丈夫,那么叶采萍是如何应对的?“叶采萍像是被人揿到阴嗖嗖的深井里,几乎透不过气来。脚骨断了筋似的,软软的,亏得尔雅懂事地扶住了她。她脑袋却煞煞清:众人都等着自己的反应呢!迅速瞥一眼虞志国,虞志国的眼珠慌慌张张躲进眼窝深处。她竟看到他的额角渗出一片细汗,心一软,便用力撑出笑脸,强硬着声音道:‘那也好。爸,妈,我们先送志国去宾馆吧!’”
王小鹰刻画了一个不一样的女人,这个上海女人与其他城市的女人不一样,与上海的其他女人也不一样。她虚荣,她是贤妻良母好儿媳,她心软,她善解人意,她还能够忍辱负重。但是她的丈夫却在美国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离婚,对于叶采萍来讲,最难过的事体不是失去虞志国这个丈夫——她早已习惯了没有虞志国的生活。让她难以割舍的却是搬出淮海坊,搬出虞家,搬出她蜷缩了多少个夜晚的楼道壁橱。从此,她便不是‘淮海坊的女人’了——这是她青春少女时代梦寐以求的桂冠,她曾经得到了它,却又浑浑噩噩地将它弄丢了!”
这是一个女人的悲哀,她的悲哀不在于她失败的婚姻,而在于她的观念,在于她那脆弱的荣耀。
离婚之后,叶采萍的悲哀还在延续,因为她又把身心和希望寄托在老板徐贵棠身上了,在虞志国探亲结束回了美国之后,叶采萍成了徐贵棠的情人,从此她又像依恋着淮海路,依恋着淮海坊狭窄的壁橱一样,依恋着徐贵棠,依恋着徐贵棠的那一套老旧公房,当徐贵棠的热情渐渐淡去,“叶采萍不敢承认他对自己已经厌倦了,她总是帮着他跟自己解释,他太忙,要操心的事体太多。现在下海开公司的人多如牛毛,生意愈来愈难做了。她总是日复一日地期待他的到来,每日下班便匆匆忙忙赶回老屋,收拾好房间收拾好自己,等待着门铃突然之间唱响。每每等得星低月远,漏断人静,方才心力交瘁地上床,孤衾冷褥,蜷缩到天亮”。这就是叶采萍,她永远都在替别人着想。这就是王小鹰,她又一次剥开了人物的性格层面,叶采萍虚荣,叶采萍勤劳能干,叶采萍心软,叶采萍爱替别人着想,叶采萍还依赖。叶采萍的心灵永远需要一根柱子来支撑。结果却是一根柱子也靠不住,徐贵棠的老婆发现这一私情,把她赶了出来。
叶采萍也就从公司辞了职,辞职之后,她“心里空落落,身上轻飘飘,一辈子都没这般闲逸过。她是闲不住的人,在新房子里困了两天,浑身不舒服,便又去寻章梅芳,求章梅芳给她点儿生活做做,薪水少点儿也没关系。章梅芳刚开了几爿店面,正缺人手,叶采萍做事又勤快又把细,自然是觅宝似的收下了她。叶采萍唯一的要求,不想去闸北、宝山的新店铺做,就想留在她淮海路上的老店里,哪怕多做点儿时间也心甘情愿。章梅芳晓得她有淮海路情结,乐得成全她”。
仍然是淮海路!这剪不断的淮海路情结真是的令人无奈。王小鹰刻画了一位不一样的女人。叶采萍的不一样就在于她永远剪不断的淮海路情结,在于她为了淮海路所付出的千辛万苦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其实她并不是为了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而是为了别人注视自己的目光,她陶醉于“淮海路女人”这顶“桂冠”,却不知道应该让自己卑微的心灵变得强大一些。她到达了那个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却是永远将自己锁在了一个误区。我们为她叹息,她却幸福在她的误区。
不一样即独特性。高明的小说家用独特性吸引我们的目光,让我们在不经意间走近了一颗不一样的心灵,也让我们在不经意间看到了思想的火花。
秦万里:湖北黄冈人。《小说选刊》 原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短篇小说《泥人程老憋》《王小晓飞往东京》以及文学评论等若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