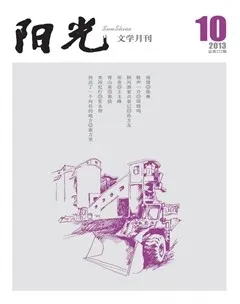青山泉
2013-12-29郭蓓
我们的小城坐落在一片平坦的大地上,向北一百多公里就有比肩接踵的群山,山里沉睡着黑色的矿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里建起了一个属于我们小城的千人大矿,规模不小,所有的人都是从我们这儿地方招工去的。
煤矿的四周都是山,农作物不能种植,连村庄都很稀少,最近的是十几里外的小镇,小镇的名字如诗似画,却也是就地看景取的——青山泉。我们的煤矿也依这被唤作青山泉煤矿。
我的父亲母亲便是这煤矿的第一批工人,年轻的他们像早晨第一缕清新的霞光,朝气蓬勃地缔造了这片矿区。历经几十年,“你是掘进几队?”依然是矿里人见面时的问候语。父亲最初的岗位在掘进队,母亲则在矿灯房。每天,她把擦拭干净、充足了电的矿灯递给从小窗口前一一走过的矿工,也递到我父亲的手中。这盏矿灯使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相恋,有了我们这个小家,有了我和妹妹。矿山地处荒僻,教育落后,爸爸把幼小的我们留给外婆,在家乡小城上学。童年的天空便裂成两端,一端是外婆外公给予的疼爱,一端是与父母天各一方的苦涩。与父母的分离在小孩子的心头形成一丝懵懂的忧伤,而每个学期期末考试一结束,我们盼望已久的团圆时刻就到来了。
从我们小城到矿里,隔一天发一趟车。外婆把我们送到车上,托付给司机老柴。老柴脸黑嗓门大,在我家喝过酒,我喊他“柴大”。 汽车逢站就停,那时的路况全程要跑三个多小时。车越走越冷清,车上的人一一下完了,只剩下不多的乘客一路跟到终点——矿里。最后一段路,大客车也归心似箭,跑得很快,车厢里的一切物什都剧烈地抖动,发出很大的合奏音响。天色渐暮,车厢里到处漏风……最后连大客车也在矿里休息了。
一个下午的颠簸对于喜欢闻汽油味的小孩子来说是一段让人兴奋的旅程。远远地望见一座高高的煤山,就知道煤矿到了。这座完全由煤堆起来的小山,是煤矿的“迎客松”,是煤矿的特殊标志。煤矿不用仓库,采出的煤被十几个拖斗车连成的小火车从深深的地下拖出,大卡车把它们运走之前就堆放在“煤山”这里。这座煤山是矿里的每一家都可以随意取用的资源。平时烧饭,冬天供暖。寒假,爸爸总是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拉回满满一平车的煤,把火炉烧得旺旺的,屋里热乎得都不用穿棉袄。记忆中,在煤矿度过的冬天总是温暖得像春天。
我们煤矿的规模很大,光是职工便有一千四百号,还有家属、小孩儿,拉拉杂杂的总有两千人吧。这里像个小镇,一个五脏俱全、功能完备的小社会,什么食堂、医院、裁缝店,应有尽有。既是一个地方去的,彼此都能牵连些亲戚熟人,常常沾亲带故,所以大半也都相熟了。医院院长是“沙大爷”,开裁缝店的女人年纪比我妈小,有趣的是论起辈份来妈妈却喊她姑奶,自然就是我们的“老太”。有次我不服,眼睁睁看着是个“阿姨”却要称她“老太”。我给妈出题:“你能喊给我听听吗?”“姑奶!”妈妈毕恭毕敬地喊。我赖不掉了,只能规规矩矩地叫:“老太。”惹来女人们疯一样的笑。
从我记事起,妈妈就不在矿灯房工作了,出身于粮食系统的她的工作也总是与各种各样的吃食打交道。我最早的记忆里妈妈在冰棒房工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真是一份惬意的工作。盛夏来临,那时的人家必备着几把大蒲扇,电风扇尚属时髦,更不知空调为何物。所以一走进冰棒房,那种沁人心脾的清凉真如跌入童话世界一般。阿姨们望见小孩子,总是欢喜地抱到齐腰高的冰柜上逗弄着,冰棒雪糕尽你吃。冰柜的盖是平着掀开的,一股白色的寒气过后,冰柜里呈现出一排排序列整齐的“窝窝”,这是做冰棒的模具。在一个铁皮水桶里用奶粉和白糖调制出原料,再舀着注满那些“窝窝”,最后一步是放冰棒棍,把一个个扁小的木棒倾斜着插入雪糕水里——千万别插偏了,那样的话,雪糕没吃完,冰棒棍就支撑不住了,剩下的雪糕就要掉到地上了。放好冰棒棍,盖上冰柜,过两小时再打开,从“窝窝”里取出的就是晶莹坚固的冰棍儿啦。冰棍的头顶上有时带着红豆沙、绿豆沙,舔一下雪糕,满口香浓的牛奶味……窗口,有人来领冰棒了,递进两张薄薄的职工消暑券,再递进一只暖瓶,暖瓶口刚好塞进长方形的冰棍,闪着白镀光的内胆便把自家的冰棒装走了。
我们的煤矿人多,食堂也大。我的暑假便从大食堂开始了。因为妈妈是食堂职工,所以就让我们也入了伙。食堂的职工每月交十块钱就管吃饱,小孩子肚子小,伙食费减半,交五块钱就可以在食堂吃一个月,很是划算。除了在食堂吃,不开饭的时候我也总在大食堂里玩儿,四处游荡。那时在我的眼里,食堂实在是个好玩儿的地方,角角落落都充满着新奇。首先是无论什么用具一到大食堂,必得放大许多,这些用具也总有出人意料的用处,长大以后读到《格列佛游记》里的大人国,我仿佛乘上时光穿梭机又回到了童年的大食堂。若先去看卖粥,粥是盛在小水缸里的,这是货真价实的水缸,里面完全可以蹲个小孩。舀粥的也是与水缸配套的铝舀子,只是还得加上长长的木柄,不然它若沉入粥海可就无从打捞了。若去看炒菜就更让人瞠目结舌了,炒锅大得没沿不说,用来炒菜的竟是一把大铁锹,需得一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奋力翻动才行。菜炒好后,分别铲到澡盆大小的菜盆里,用小推车送到卖菜的窗口去。有一年夏天,夕照还热辣辣的,食堂跑采购的大卡车回来了。在各色果蔬菜品中,让矿里人兴奋的是一只半米长的大西瓜。虽然它长着绿油油的西瓜纹,但个头比冬瓜还大。一时围观者众,兴致盎然地议论着。“五十二斤还零三两!”采购员满脸自豪地说,“这家伙个人没法买,谁家买去了,谅他一星期也吃不了!只有咱大矿能买!”除了在矿里,以后我再没见过那么大个儿的西瓜。
那时,到处弥漫着大集体的祥和气氛,人们脸上总挂着松弛无忧的笑容。大食堂是个让人快乐的地方,食堂里的人,越是熟悉越是亲昵,见了面就越是要互相戏耍涮弄方见得要好。开着玩笑,不知不觉,一车面粉卸完了,斗着嘴较着劲,没觉得怎么使劲,面揉好了放在那儿醒着了。他们也有统一的工作服,大白褂,大白围裙,男师傅女师傅们全都松松垮垮地穿着,或者根本不穿,随意地解下来放在手边,只是看着钟走到十一点,才胡乱把蓝套袖套在两条胳膊上,把白帽子扣在头上,以很“卫生”的形象站到窗口卖菜了。从缸里舀稀饭,从澡盆里用大勺打豆芽。
绕过大厅往里走,一扇铁门终日半开着,进去便是食堂的后院。说是后院,天热的时候炸油饼也在这里。一个人管案板,揉面,摔打,切条,切片儿。要是做油条,就拿两根白面条儿撂一起,单根筷子从中间轻巧地压一下,为的是给油条分出两条腿儿,中间压过的地方又能相连。要是做油饼,一个小块面团,拿擀面杖滚圆了,直接丢到油锅里飘着。油锅始终是沸着的,所以有一个人专门管它。用一尺长的筷子不停拨弄着,这筷子专为炸锅使用,若用它夹菜,恐怕只能送到桌对面的人嘴里。刚丢到油锅里的面先还是白生生的,小油泡们吱吱地围着它,转眼泛黄,金黄,长筷子帮它打个滚,颜色均匀了,就捞到旁边的铁篮子里沥油。沥一会儿,也不那么烫了,就可以交上票端走了。
忙过早点,就该打点炒菜用的菜蔬了。炸油饼的摊儿收了以后,露出一块平平整整的水泥地,它比平地略高,下面实际上正是食堂的储藏室。水泥地好清扫,有时拉一根软水管冲刷一遍也不费事,这一块地方正好可以用来料理原材料。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大卡车拉来了一车冬瓜,有几十个吧,摆在这水泥平台上。两个小师傅开始削冬瓜皮。他们各坐一只冬瓜,再弯腰去削另一只。削完了再重找一只坐着,再削这只“板凳”。两个人说说笑笑,虽不十分累人,也削了一个下午。要是今天吃土豆,瞧吧,平台上小山样的土豆挨个去皮也是一桩浩大的工程呢。杀鸡也是在这里。抓过一只鸡来,不管它如何咯咯咕咕地叫,两翅反剪在后,鸡冠也扭到翅上,腾出一只手来拿菜刀在鸡颈上一拉,鸡叫不出声了,还是蹬腿。控一小会儿鸡血,手一松甩到水泥台上去,那儿,被放过血的公鸡扑扇着各色羽毛,起先还很剧烈、不甘,很快就平静了,过不多会儿小师傅就来给它褪毛。这场面小孩子看来太残忍,下回一看要杀鸡,赶快跑开了。
食堂里的师傅们都是边干活边谈话,笑嘻嘻的。他们那样放松,随意,快乐,既是尽着本职,又有一种率性而为的劲头。面点房的人整天跟面粉打交道,他们的大围裙和蓝帽子总被无处不在的面粉染得白蒙蒙的,连眉毛上也下了雪。和面,蒸馒头,有的小年轻打闹起来,抓起一把面粉朝对方脸上一扬,叫他吃雪,大师傅也就边笑边骂。大师傅四五十岁的年纪,看起来稳当多了。把面和好,搭上一块湿布醒着,可以歇一歇了。大师傅正好解解烟瘾。一棵烟点上,舒舒服服地吐出一口,烟雾缭绕着白眉毛白胡子,大师傅又想讲古了。这也是小孩们留连在面点房的重要原因。“今天讲个什么呢?嗬哟,说起来,皇陵前的石兽石人可都不可小瞧,动辄都有着五百年、上千年的道业呢……”大师傅偏爱这些神神叨叨的民间传奇。他总爱讲“道业”,谁谁谁“道业”不深,但如果谁谁谁吃了谁谁谁,对方的“道业”就累加到他身上了……“道业”究竟是个什么,小孩子其实并不知道,但看到大师傅眼睛兴奋地瞪大,烟圈吐得更多了,就朦朦胧胧地点头,也琢磨出必是神奇的叫人长生不老又类似于“功夫”的东西吧!
在过去,许多大集体的单位食堂还等于礼堂。食堂的就餐大厅平时摆满了随意取用的桌子椅子。可到了年节,大桌面顺墙竖起,头顶拉上纵横交错的彩花,这儿就成了文艺汇演的礼堂了。舞台是现成的。舞台的灯一照,台上净是化了妆换了演出服装的矿工们,这天天吃饭的地儿一下子光彩、热烈起来。春节的联欢尤其火爆,人挤人,人摞人,食堂的师傅们赶紧占据卖菜卖饭的窗口,脸上的笑被台上的灯光映得红彤彤的。我们姐妹因是孪生,更醒目一些,从小活泼,爱唱爱跳的。小学二年级寒假起,在煤矿的“春晚”舞台上表演歌舞或朗诵就成了保留节目之一。那一夜,是可以任性晚睡的。大年初一一早,我们正坐在热被窝里,棉裤还没穿,管文艺演出的叔叔就来了,送给小演员每人一个日记本,一杆钢笔,作为奖励。那个兴奋劲儿就别提啦,可能有点儿像外国小孩得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吧,因为是演出的酬劳,还多了一份光荣和自豪。
我们到处疯跑,仿佛因为太阳的热力,细腿伶仃的八九岁孩子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和探索的好奇。
医务室前的草丛里有一种灌木上可以摘到蓖麻子,小指头大小的绿球上长满了刺。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武器。摘一小把装在兜里,乘谁不备丢一个在他(她)头发上,蓖麻子的刺像小手一样抓牢在头发上。因为分量轻,被袭击的人往往浑然不觉,但看到小伙伴绷不住的样子,急忙检查起自己的头发或者辫子来。
玩腻了蓖麻子,小孩子们还喜欢程奶的小屋。程奶是调度室的接线员,她工作的屋子很小,面前插满了电话线。电话铃响她就戴上大耳焐一样的黑色耳机。“你好!调度室。要哪里?……好,转掘进三。等着。”然后程奶拔下这个,插上那个,好不神气。她喜欢小孩去玩儿,不忙的时候,知道电话逗得小孩心痒痒,就把我们抱上膝盖,说:“咱给你爸爸打电话?不要?那打到小吃部去,找妈妈!”有一回,程奶忙了。有邻居小孩敲窗户,羡慕地看着调度室满桌子的电话线。妹妹抢着去开窗,外面猛推了一把,弹回来的窗框磕掉了她的一颗门牙。哭哭啼啼地被送回家,程奶说:“我一会儿没看好,就调皮成这样。”
除了黝黑而神秘的“井下”,煤矿的角角落落我们都跑遍了。煤矿的前面是煤山,后面是铁道,远处是层峦叠嶂的群山。煤矿的建筑群很有特点,以至于后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认出大大小小的煤矿。煤尘重,所以煤矿的楼多多少少都有点儿黑黢黢的。最易辨认的是带斜坡的楼,或是两个楼之间悬空连接着一个通道,据我观察,这种楼只有煤矿才有。不论是斜坡还是通道,都是为了铺设运煤的传送带。有一年夏天,我们一帮小孩逞强,竟然沿着一道斜坡一直爬到了楼顶。那楼有四五层,在楼顶的平台上,我还发现了几个水泥铸字,仔细辨认,写的是:“苏联造,一九五三年。”虽然我年纪还小却很震惊于自己的发现。这些运输矿藏的建筑竟然是苏联人造的?这些不起眼黑糊糊的楼竟然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一种历史的感怀和复杂况味穿过我小小的胸膛。
爸爸的办公室在机关楼的一层,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安全科”。安全科里有三四个人,按小城的礼仪,比自己爸爸年轻的叫“叔叔”,比爸爸年长的得喊“大爷”。不管是叔叔还是大爷,每次见到我们姐妹,必做的功课就是猜我们的大小。“我来猜猜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把我俩并成一排,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再看看这个。猜对的人马上很自豪,“我一看就知道,小二子脸圆,大子脸尖,鼻子这儿还有一个痣,当然也不明显……”猜错的则抓抓脑袋,服气地说:“太像了,长得太像了!这恐怕父母也有弄混的时候。是不是,老郭?”
爸爸并不总在安全科待着。他要每天下一次井,及时巡察和排解安全隐患和问题。机关楼后面有一个水池,水池很普通,有趣的是水池边上用水泥砌出了一块搓衣板。有一天午睡醒来,我们在这个水池边玩儿水,把手掌堵在水龙头上互相滋得水淋淋的。正闹腾着,远处走过来两个矿工,他们显然刚刚从井下上来,带矿灯的帽子还戴在头上,脸上像花猫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地抹着煤灰。这样的矿工在煤矿大院里太常见了。这俩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朝我们打闹的地方指点、嬉笑着。妹妹说:“有什么好看的?”她言语犀利,没想到两个矿工笑得更厉害了,露出的牙齿刺眼地白。他们一直走到水池跟前了,妹妹的眼神忽然慌张了一下,我才看出其中一个脸上脏兮兮的矿工竟然是爸爸!我俩不知是害羞还是着恼,竟然不约而同地拔腿就跑,悄悄回头看时,那俩人拧开水龙头洗起脸来。这件童年的趣事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只有那一次,我看见爸爸脸上抹着煤灰的样子。——就那一次,还没认出他来。
煤矿后面的铁轨只走运煤的火车,偶尔会有一个火车头拖着十几节空车厢呜呜地势来,装满煤又呜呜地吐着白雾跑远了。我们曾经踩着枕木上的野花野草沿着铁轨走出好远。火车来得少,轨道边荒草丛生。想想还不如矿里好玩儿,就又走回去了。有一次不知怎么看到一个黑糊糊的棚子,几十个矿工正席地而坐,边闲谈边在等待着什么。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里面有个笼罐一样的东西升上来。总觉得那个地方有点儿神秘,回家一说,妈妈正色说:“那是井口。太危险了,下次不许去了,听到没有?!”我俩懵懂地点点头。长大以后,我总把煤矿当作自己童年的家,也遗憾矿工之家出身的我却从未到过井下——那几百米下的地层深处。虽然我现在的生活已经远离煤矿,可是每每路过煤炭部的大楼,或是读到煤矿文联主办的《阳光》杂志,童年的那缕阳光仿佛又照进我的心田。每有矿难消息,我也总感揪扯着心肺。回想着我的父亲母亲在我们地方的煤矿上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二十年,想象着父亲站在罐笼里沿着窄窄的井筒一米一米地下降到几百米深的地下,只有头顶的矿灯是他照亮自己的阳光……我总有深深的感动。爸爸常自豪于自己在煤矿干了二十年“却一个手指都没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理解了爸爸的话对他的人生、对我们整个家庭的幸福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青山泉煤矿的家在一个四四方方的家属院里。这正方形的每条边都是一排房子,每个家也就是一间屋,家具朴素简单,却那么温馨可人。煤球炉在门外,进门是脸盆架子,旁边摆张小饭桌,里面是床,床前有一个柜子一张书桌。院子里一共住了一二十家,矿长的家在最里头,跟我家一样,一家四口,也是一间屋。他的大女儿患有脑膜炎后遗症,模样呆滞,自然他偏疼的是活泼可爱的小丫头。靠近院门的是放映队的办公室,只摆着机器,要看什么电影,一轱辘一轱辘的胶片要到放映前才拿来。显然机器贵重,这间屋便帘幕低垂,上锁的时候多。
房子都顺了边,中间的空地除了随便地种点儿花草,便自然地成了大家消暑娱乐的地方。夏天的傍晚,屋子里充满暑气,人们乐得待在院子里。那个年代,男人们大多穿件白色的背心,泡杯浓茶,再摇把蒲扇——我们院里多的是这样乘凉的人。有趣的是,三五成群的都是下象棋的,不玩扑克。似乎看不起扑克似的。象棋是把大智慧运用到小棋盘中,是微缩的战场,是意味无穷的角斗,才值得棋迷者两眼放光引颈观看,也才值得每天都端着茶水攥着扇子自动前来。左一堆下象棋的,右一堆下象棋的,不知怎么,我和妹妹看着看着也学起样来。家里有一副塑料象棋,比不得院子里月饼样的木棋子气派,可是小孩子玩起来正好。二年级暑假,棋子上的字认得差不多了,我和妹妹把塑料棋盘铺在凉席上,就一人一边排阵布兵起来。“红子先走”这个规矩我懂,看了无数回了。也学大人们先拱侧边卒,再飞象跳马出车……不太会的就瞎走,若是吵将起来,就一齐嚷嚷着请爸妈过来“评理”。最容易发生纠纷的是别不别马腿。“马走日,象飞田,炮打隔子连”,口诀也是听会了的,可是最麻烦的是马腿,顺边的“别”,不顺边的“不别”,因为究竟是顺边还是不顺边就容易耍赖、争吵。爸妈过来先评了理,再教一点儿规则和战略战术,渐渐的,我俩才真会下象棋了。上初中时,一个男生带象棋到班里玩儿,我观战时“点拨”了两句,他惊讶得下巴快掉下来了,他还以为女生只会玩圆溜溜的跳棋什么的呢。
识字多了,在家待着的时候,就特别爱看书。我们爱看的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杂志,爸爸偏爱科学,他督促我们看的还有科普故事《科学世界》以及益智类的智力小故事之类的图书。我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本白话《聊斋》,字当然认不全,但磕磕巴巴、囫囵吞枣地把一个一个的小故事都读完了。回想起来,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大部头吧。
夏日里最愉快的记忆还有放电影的时光。绚丽的晚霞刚刚从西天消退,我们便准备去看电影啦。我家有两把托熟人从四川捎来的藤椅,结实、轻便,像是特意为看露天电影而准备的。这天的晚饭是吃不安生的,匆忙塞进几口,我和妹妹便一人搬一把藤椅抢占位置去了。就见门口路上散散落落的有不少小孩也在搬着各式各样的椅凳,都是奔煤山外的电影场去的,一时,马路上还有点儿甚嚣尘上的味道。我们把椅子安顿下来,兴奋地等待天黑。不一会儿,爸妈也来了。妈妈胳膊上搭着两条小浴巾,预备夜深了给两个小鬼盖肚皮,手上还少不了零嘴吃食。爸爸就轻省多了,烟卷不断。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放映员架好机器,远处一辆自行车骑来,大家纷纷转告“送片子的来了”。两把藤椅爸爸妈妈一人坐一个,再分别抱一个小孩。放的什么电影倒大多模糊了,也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大篷车》什么的吧,但是放电影的节日般的欢腾和露天电影场在爸妈怀里睡觉的快乐,真叫人期待和难忘。
一个清新的早晨,妈妈特意带我们去了一趟青山泉镇上。太阳刚刚从山岭上升起,把我们的影子拖得长长的。我们俩一左一右拉着妈妈的手,地上,我俩的影子都是一模一样的。草叶间闪动着星星点点的露珠,凉凉的风里有了一点儿秋的意味——暑假也快要结束了。
搭了一段食堂采购的大卡车,妈妈领我们在一排简陋的房子前下了车。那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我至今记得站在铁轨前平坦的水泥地上,沐浴在金黄的晨光里等待火车的激动心情。手心里紧紧攥着那张扁扁硬硬的火车票。望着缓缓停下的火车,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又有一点点的自豪,因为爸爸说过,火车是靠煤才跑起来的,没有我们从地底挖出的煤它跑不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乘火车,它可比煤矿里的小火车大多了,虽然它没有我们爱闻的汽油味,但是比汽车宽敞整洁。这列绿皮火车的座椅很可爱,居然像会议室的长椅一样由一根一根的木条组成。人们两两相对,靠窗还有一只袖珍的小桌。火车开动了,我俩都趴到窗口看外面匀速闪过的田野景色。虽然只坐了十五分钟的火车,但这天早晨,世界却变得如此不平凡。
也许是坐火车这个美妙的开端吧,这一天的一切似乎都那么美好而难忘。青山泉镇上有个溜冰场,我们胆儿小,但在妈妈的鼓励和保护下,也玩得特别痛快。又到百货大楼,从玻璃柜台里选了好几本童话书。妈妈还给我们买了新袜子和白球鞋,这是为新学期准备的。
告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八月三十日,大客车照例停在食堂的后院前。爸爸递了支烟给黑脸“柴大”,看见他的大茶缸还是空的,连忙端回去给他泡茶添水。前一天晚上,妈妈就已经把我俩的暑假作业、童话书和衣服鞋子整理好,放进各人的书包里了。这时先拿到大客车上占着“柴大”身后的两个座位。天刚蒙蒙亮,车厢里开了盏昏黄的小灯。夜色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们却要和父母亲分别了,回到只有小学校、外婆和外公的世界里去。汽油味还像来的时候那样充满了陈旧的车厢,可是不想闻,因为心里难过,胃里也像是要晕车似的翻腾着。
终于,大客车在“柴大”的发动下,剧烈地抖动着。
爸爸说:“好好学习!”
妈妈嘱咐:“听外婆的话!”
隔着窗子,我看见妈妈还在挥手,爸爸却又燃起了烟。汽车载着我们驶过方方正正的家属院,驶过机关楼边带水泥搓衣板的水池,一转眼,煤矿大门口的煤山越来越小。青山泉,我们度过了美丽夏日的地方,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日夜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们总在梦中哭着思念的家,远了。
不平坦的山路上,大客车颠簸了一下。
我和妹妹的手不由自主地攥在了一起。
郭 蓓:1977年出生于江苏睢宁,200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做过大学教师、文学编辑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