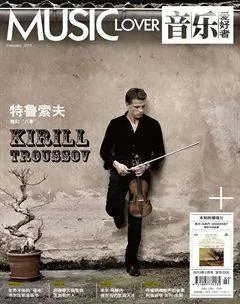迎刃而解的“悬念”
2013-12-29周凡夫

“睽违宝岛二十二载,乐自香江来。”这是香港中乐团重访台湾的宣传单张及场刊封面上的标语。也就是说,香港中乐团此行是双方期待超过二十年的事,观众在强烈的期待下,对乐团必然有极高的要求,乐团的表现要满足这种高度期待不是易事。再加上首场于台北中山堂的演出是首次举办的香港周闭幕节目,而中山堂是近年来在台湾风头强劲的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驻地,台北亦是台湾国乐发展的重镇,在这种种情况下,香港中乐团上下的压力自然不小。
香港中乐团1988年首次访问台湾,在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共演了六场,场场爆满,掀起了讨论大型民族乐团的热话;1990年重访,参与第九届国际艺术节,在台北演出了三场,同样大受欢迎。今次访台三场演出门票全售罄,二十二年后的台湾观众,特别是国乐观众的视野与要求,都已和二十多年前很不一样了。香港中乐团这次巡演会在台湾带来何种反响,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大得胜》先声夺人 《精·气·神》考验观众
就在这种种悬念下,八十多位乐师仪容端庄地分别从中山堂中正厅的两边列队同步出场,乐声未起已展现出训练有素的威仪阵容,指挥阎惠昌出场引发热烈的掌声,可见当晚观众中应有不少是他的“铁杆粉丝”。开场曲《大得胜》先声夺人,热闹欢庆的吹打乐,能做到强而不吵已不容易,八支唢呐加上大量打击乐,大型民族乐团的宏大气势将场内气氛加温,尽展乐团的强大吹打乐实力。最后八位唢呐乐师,采用“循环换气”的方式,按序逐一起立持续不停地吹奏几近一分钟的绝活,将全曲带上高潮而结束,哄堂而起的热烈掌声,悬念感觉已解除一半。
接着是与传统民间风格的《大得胜》截然不同的现代风格作品《精·气·神》。这是香港作曲家陈明志十多年前的作品,2001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音乐议会“国际现代音乐交流会”获选为十首推荐作品之一。乐曲的创作概念来自东亚的哲学“气”,强调音乐中的音形特变、音乐变化、阴阳虚实的动静对比、瞬间的爆发力和大幅度的强弱对比效果,变化极大,这可是一首对乐团和听众都是很大考验的作品。阎惠昌首先向观众介绍了该曲的特色,让大家将欣赏的心理作出调整后才欣赏。阎惠昌与香港中乐团自1998年2月首演该曲后,不仅不时选奏该曲,且已于1999年录制成唱片出版,当晚奏来,驾轻就熟,其中似无若有的音响亦能让人屏息。自乐曲开始,以两个鼓状物牵紧一条弦线振动,发出奇特的音响,曲中复杂且丰富、跨越幅度极大的变化和不时出人意料的独特音响效果便一直牵引着观众,最后在一声单一的弱音和弦音响后,静止的时空仿佛凝结着……好一会儿后才爆发出的满堂热烈掌声,无疑是这首长近十分钟的香港现代风格作品已“成功登陆”宝岛的标志,关于这首在台湾首演的“新作品”会有何种反应的悬念亦一扫而空。
《滇西土风》无悬念 高洁共鸣《幽兰操》
相对而言,作曲家郭文景先后跨越十五年为香港中乐团创作的《滇西土风三首》,三段充满音响色彩变化,音乐形象、节奏、音色鲜明的乐曲(最后一首《祭祀—火把—烈酒》更带点《春之祭》的影子),将观众情绪大大刺激起来完结上半场,那则是在意料之中、事前毫无悬念之事。
下当场开场是另一首台湾首演作品,由香港中乐团委约赵季平所写的《幽兰操》。这可是一首讲求意境、采用如散文诗般的音乐语言、借着相传为孔子所作的《幽兰操》来描绘出伟人孔子人格魅力的音乐作品。乐曲长约十六分钟,一开始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柴亮演奏小提琴,与同样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赵家珍演奏的古琴,以对话般的呼应奏出高洁清简的主题。古琴在各种传统演奏技法以外,还采用了滑音、击打琴身等特殊技巧。这段由小提琴与古琴主导的音乐,深邃幽清,讲究的是线条和单一的色彩,长度超过整首乐曲的一半,这可是对听众耐性的挑战。当晚中山堂内人人屏息而听,及至古琴拍打琴身,节奏渐渐变得较为快速,小提琴亦配合着激动起来,强力的压弓效果,加上拉弦组的伴奏,将这段刻画孔子的形象及隐含着大志难展、怀才不遇、流离郁结的内心世界的音乐,引向一个较为激情的结束。
在竖琴简短的滑音连接下,进入由西安音乐学院声乐教授张宁佳主导演唱《幽兰操》歌曲的第二部分。全部歌词共十六句,每句四字的文言文,张宁佳采用融入了中国戏曲唱腔的发声,艺术歌曲的雕琢再配合带有一定戏剧性的肢体动作,很细腻深情地将这段饱含着孔子人生观和自况感怀的诗词,既非悲泣、亦非控诉,而是颇为直接地直抒胸怀。情绪一步一步铺排,在前八句后,经过乐队和小提琴的过门,带入越发愤懑激情的后八句,小提琴、古琴和乐队扮演的正是这种情绪上的变化和气氛的营造。神来之笔是最后重唱《幽兰操》最初的四句歌词,让全曲回到较为平和高洁的意境中结束。
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场内几乎人人专注投入,屏息聆听的宁静气氛已见出台北听众大都能感受得到这种高洁的音乐意境,且能有所共鸣,水平确是不低,事前的悬念看来是多虑了。
《黄河畅想》对唱版 台北“首演”悬念消
音乐会压轴之作是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的程大兆所写的《黄河畅想》,阎惠昌与香港中乐团采用互动方式,于乐曲末段让乐团提供拨浪鼓予全场观众,舞台上下均在指挥的指示下互动演出。这次一如该曲在欧美及中国大陆演出时那样,台北的观众情绪亦被高高掀起。
《黄河畅想》在大家的兴奋情绪中奏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曲中情绪转换之处,既非采用原版的由女高音领唱,亦非巡演时以唢呐取代的“改编版”,而是由乐团中两位乐手毛清华和任钊良暂时放下手中的中胡和管子、站起来高歌的“对唱”版。两位乐师都非专业歌唱家,他们的歌声能否压住场,那可是此构想的悬念所在。结果,在两位乐手的努力下,此“对唱”版本的台北“首演”悬念亦有了让人满意的答案。
这之后引发的便是对返场曲的期待。
阎惠昌遂与乐团互动演奏了香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主题曲,场内的热度再度提升。最后再来一曲绘声绘影的《赛马》,音乐会终在沸点下结束。而场外大堂早已排了一条等待指挥家及独奏家签名的长队,毋须细数早已远远超过“八十位”的限额了!
综观香港中乐团此行访台,面对的各种悬念,最后都得以释怀。仔细分析悬念因素得以迎刃而解的原因,节目设计安排要考虑目标听众的水平和欣赏心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仍是乐团艺术上的实力和艺术水平的表现。香港中乐团声名在外,能赢得“香港文化大使”之名,赢尽中国大陆和欧美无数城市的爱乐者掌声,凭的都是艺术上的实力,靠的都是指挥阎惠昌及棒下的每一位乐师对艺术一丝不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