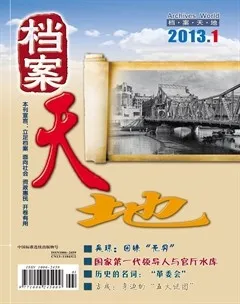革委会
2013-12-29张春锋刘慧鑫
“革委会”一词想必广大读者并不陌生,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省及其以下各级政权和各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基本组织形式。它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存在了长达十二年之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新生事物大加赞颂,曾在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革委会的成立背景
革命委员会,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全面夺权运动的产物。
早在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该通知说要“夺取”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966年8月8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更是明确提出:“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1966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1967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夺权阶段的序幕。
在舆论大环境的风向下,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宣告夺权。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上海市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夺取了中共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建立了新的政权组织。1月8日,毛泽东对上海夺权运动的评价是:“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1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说:“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林彪、张春桥等人推波助澜。张春桥更是肯定地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1月23日,林彪确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方针——“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一场“全面夺权”的斗争不可阻挡地展开了,上海的夺权运动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
第一个革委会的诞生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说:“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时,就已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1967年1月,在张春桥的主要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关于夺权后建立的这个政权组织的命名问题,善于投机钻营的张春桥想起了毛泽东肯定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话:“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于是,张春桥决定按毛泽东的思路办,把上海市造反派所建立的新政权叫“上海人民公社”,并以“上海人民公社”的名义连续向中央打报告,除了报告大好形势外,主要报告“上海人民公社”的优点。
有上海市做了夺权的表率,全国各地也开始纷纷效仿全面夺权运动。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各地组织的新政权名称命名并不统一。针对新建立的政权名称不统一的状况,2月12日,毛泽东为此事专门召见张春桥、姚文元,批评了他们建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他说:“那是要改变国家体制的,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都叫“人民公社”行吗?中央也叫“人民公社”行吗?我们国家的体制改变后,外交上是否也要改变?要外国再承认一回?要重新建交?”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问题,问住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在谈话中同时也作出了自我批评说:“我也考虑不周到呢。我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来考虑,这样就发生了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国家主席是否要改变为“公社主任”或“社长”?这就发生了外国是否承认的问题。如果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要选举人民委员会。”经过此次谈话,毛泽东决定:上海的新政权,不能叫“上海人民公社”,要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暂叫革命委员会为好。2月14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将“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革命委员会”。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革委会的“三结合”组织形式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组织形式。
上海夺权后,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提出“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新的政权机构。社论不仅号召要向走资派夺权,而且实际上又提出了新机构中要有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解放军到地方支“左”,成为“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又一个重要前提。1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指出,在夺权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里首次提了新建立的政权要以“三结合”做为基本组织形式。
同日,黑龙江省成立了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这是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政府机构中,第一个以“革命委员会”命名的机构。2月2日,《人民日报》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黑龙江省的经验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是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其中,无产阶级造反派及其所代表的广大革命群众,是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革命领导干部是革命委员会中的骨干和核心。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这种“三结合”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的部门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各级政府机构,是由革命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农村人民公社以下由民兵代表代替解放军代表。在工厂企业中,是由革命干部代表、民兵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在各大中专学校,是由革命学生代表、革命教职员工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
各级革委会领导班子,执行原各级政权机构的一切职能,只是内部设置的名称有所改变。革命委员会在机构设置方面,非常强调组织机构的所谓“革命化”和“精兵简政”。原来的司、处、科、股被取消,改称为“领导小组”。在省、市、自治区等各级政权机构的革委会中,一般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或政治部)、生产指挥组(或生产指挥部)、人民保卫组(或政法工作组、保卫部)。而在各组(部)下面又分设若干小组,分管各方面的具体事宜。各组(部)也是由革命领导干部、军代表和一般工作人员三方组成。革命委员会在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的同时,其管理职能也在不断扩展,并最终取代了地方党委、政府的一切职能,成为唯一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革命委员会”成员一般不通过选举产生,是经过所谓“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才推选出来的”。这种推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造反派组织的状况和审查机关的主观意志。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4000多名委员中,包括其中大约半数左右的群众代表,都没有经过民主选举。而当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在当时各级党组织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唯一国家权力机关,已经成为一个党政一体、无所不包、至高无上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种体制把以往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一元化发展到极端,成为一种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混沌体。同时,毛泽东掌握的原则是,建立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必须由中央批准,主要领导人必须是由中央派出的或被中央认可的。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指示》就中共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10月19日来电请示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要求各地都应这样做。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各地征求意见。文件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来实施党的组织领导。
“革命委员会”开始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全面夺权浪潮的推动下日益向前发展。省级以下各级组织,从市、县、公社到学校、工厂,甚至车间、街道居委会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同时“革命委员会好”成为全国必须遵守的法律。
全国山河一片红
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4省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并建立起革命委员会。1967年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太原市的党政大权。22日,青岛市23个单位组成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告成立,并正式接管了青岛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贵州省党政大权。31日,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夺了黑龙江省党政大权。这些构成了1967年春全国夺权的第一次浪潮。对上述各地的夺权“斗争”,《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关键在于大联合》、《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予以肯定。后来的24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大多是在当地军管会、军区(军分区)或主要是由部队支左人员组成的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也都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给予高度赞誉,如《芙蓉国里尽朝晖》、《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红日高照长白山》、《不到长城非好汉》、《东北大地红烂漫》、《长江万里起宏图》、《辽阔中原唱凯歌》、《春风已到玉门关》等等。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维吾尔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这样,当时全国(除台湾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对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全部建立革命委员会表示热烈祝贺。社论满怀豪情地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从1967年1月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作为各级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可谓“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好”从此成为“文革”中反映“造反”成就的一句口号。
河北省革委会的建立
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趋势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也着手建立。
截止1967年底,华北五省除河北外的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只有河北由于武斗问题,原有省级政权机关瘫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工作被无限期拖延。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环境下,上到中央,下到河北都开始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着急。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河北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1967年是河北省省会驻地动荡的一年,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由于武斗不断升级,其作为省会的地位注定无法维持,为了尽快结束河北的无政府状态,石家庄革委会的成立吸引了正在谋划筹建河北省革委会工作的中央和华北局领导的注意。
1967年10月14日,石家庄地直各部门造反派实行大联合,有十个局、处建立了“三结合”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10月21日,石家庄地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石家庄地区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统归其所有,成为石家庄地区最高临时权力机构,同时也是河北省地、专级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委员会。12月20日,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市革委会委员、驻石部队指战员、各群众组织代表共1500余人在石家庄市八一俱乐部举行了成立大会。
1968年1月16日,180余名代表在北京召开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会议指出“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建议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提交了《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往石家庄市。河北省革委会由121名委员组成,设办事组、秘书组、保卫组、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等五个机构,李雪峰任主任,刘子厚任第一副主任。原省委负责人林铁被打倒。
2月3日,河北省在石家庄市东方红体育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以示祝贺。
革委会的落幕
党的“九大”以后,开始了恢复各级党组织的工作。197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提出要陆续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党委,并要求新党委成立以后,不另设重叠的办事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基本上就是党委会的办事机构。后来各级党委成立后,新党委和原来的“革命委员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党委的第一书记基本上都兼任“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中共中央开始重新考虑部队的“三支二军”问题,这直接涉及“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问题。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二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决定:“三支二军人员撤回部队;凡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管、军宣队、支左领导机构撤销,少数军队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三支两军”人员撤回后,各级地方党委成员适当作了调整,一些比较熟悉全面工作和富有经验的地方领导干部重返各级领导岗位,并更多地挑选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此后,大部分参加到“革命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陆续返回部队,特别是企事业等基层单位的军队代表。但也还有一些军队代表留在地方,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和省市一级的“革命委员会”担任主要负责人。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这以后,“革命委员会”内部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干部、军队、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政权形式,已经不作为普遍原则存在了,而被新的意义上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形式所取代了。
作为“三结合”中居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人民解放军已从革命委员会中撤离;作为“文化大革命”重要合法依据的群众组织——所谓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农民代表大会”等,已经为逐渐恢复的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共青团、工会和妇联等所取代;随着老干部的复出,“革命干部”代表中老干部占了绝对优势。“文化大革命”前的领导体制基本上得到了恢复。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这实际上第一次对“革命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通过立法的程序加以确认。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新建立的政权形式“革命委员会”,在其建立8年以后,才通过立法机关把“革命委员会”作为一种政权形式确定下来。
197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本年10月份至12月份分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由“革命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选举新的“革命委员会”。之后,从1977年10月至1978年2月,各省相继召开了省人大,选举产生了各省新的“革命委员会”。这改变了以前完全依靠“革命群众行动”产生“革命委员会”的非程序性、非民主性的错误做法。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是我国的地方政权机构;要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改选各级“革命委员会”。今年内全国的省辖市、自治州、县和公社,都要分别召开人代会,选好新的“革命委员会”。地区一级是省的派出机构,不设“革命委员会”。工厂、生产大队、学校、商店以及机关和其他企、事业单位,除了实行政企合一的厂矿企业外,都不是一级政权,不再设立“革命委员会”,而应分别实行党委领导下厂长、大队长、校长、经理等的分工负责制。会议通过的宪法也做了相应规定。这实际上把国家的政权形式同各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区别开来,为以后最终取消“革命委员会”做了一定的准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革命委员会仍作为地方人大和政府合二为一的权力机关存在了一段时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它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决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9月11至1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在一九七九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的决议》。至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制度,恢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制度。存在了十二年之久的革命委员会结束了自己的历史,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终告结束。1979年8月至1980年6月,革命委员会终于在相继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人大会议上被正式废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随之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