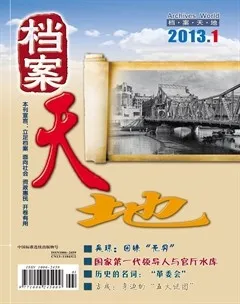回味“无穷”
2013-12-29吴琼
编者按:
著名黄梅戏演员,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人。吴琼以唱功见长,声音委婉、动听,如珠落玉盘余音绕耳,能高能低、能细能厚。1980年毕业于安徽省艺术学校,后进入黄梅戏剧院,曾被评为黄梅戏全国“十佳”演员之一。主演过《女驸马》、《天仙配》、《凤铃》、《孟姜女》、《无事生非》等黄梅戏舞台剧。
严厉的母亲
我的老家是一个叫做繁昌的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隶属安徽省芜湖市。繁昌的县名很好,繁荣昌盛之意。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勤恳劳作,邻里相敬如宾,民风朴实无华,父母一辈子生活在那里,深爱着那片土地。
我爱我的母亲,一个“爱”字还不足以表达我对母亲的情感,我觉得“喜欢”这个词好,因为“喜欢”更生动,给人不一样的感觉。我喜欢我的妈妈,特别是在我长大以后。
母亲在我小的时候,总是要打我的,而且是每天都要打一顿。刚开始,怕得要命,只要看见妈脸色变了,便吓得魂飞魄散,撒丫的跑出去,直到天黑被妈妈拎着耳朵揪回家,必定还是要补上打的。
慢慢的,打多了,打硬了,胆也壮了。如果知道自己闯祸了,逃不了一顿打,看见妈妈回来,便自觉地把门给拴上,任妈妈怎么打,也不吭声,还咬着牙,像电影里的刘胡兰。妈妈骂我是犟驴,有时她都气哭了,我还是不认错。常常有小伙伴们趴在小木窗上偷看,幸灾乐祸,第二天要是被我抓住,跑不了要暴啐他一顿。现在想起来,谁家要是摊上这样的倔孩子,非恼死不可。
母亲被我的无事生非,疯野打架搞得无可奈何,手中的道具也由鞋底、鸡毛掸、棒槌换成扁担。那个时候,打架的理由很简单,谁要是喊了我爸爸的名字,是跑不了要打一架的。还有,谁要是欺负了我妹,那也是不顾一切要拼命的。
小的时候,我个子长的很快,一个院子里同班的男孩都比我矮。后来他们都猛长,我却停止不前了。因为个子长的高,所以很逞强,有理无理和人拼一架。
有一次又闯祸了。可想而知,这一顿打又是逃不脱的,妈把我打的很重,昏昏沉沉,带着眼泪我睡着了。半夜,被一阵哭泣声惊醒,原来是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妈看我醒了,摸着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问:是不是很疼?妈妈对着我又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院子,就你爸爸被下放到农村,我一个人带着你和文子(我妹妹的小名),每天上班,做服务员,站柜台,拉杂货,多辛苦,回到家,你还尽给我惹事,你能不能不和人家打架呢?你能不能给我安分一天呢?我还是不吭声。妈哭了,说:人家爸爸不是局长就是科长,妈妈也是坐办公室舒舒服服的。谁像我们家,就你爸爸一个男人还下放在农村。我们家没有男孩,我把你当儿子养,指望你好好读书,将来争争气,哪知道没有一天你不和人家斗,不和人家闹的。我不打你,我能跟人家去吵吗?我只能打你呀!妈妈一边摸着我的屁股,一边痛哭起来,我紧紧地咬住被子,没有让她看见我的眼泪。
先前总挨母亲揍,我恨母亲。心想,如果将来有机会,让我逃了出去,我是再也不会回来的。可是这一刻,我对这个信念开始有点动摇。
我没有像妈妈指望的那样,好好读书。我在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搞的热火朝天,不夸张地说,我妈的肺给气炸了。那时候,她们晚上是要政治学习的,妈去学习的时候总要把家里的门给反锁起来,不让我去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妈没想到,等她一走,我就把小木窗掰开,让等在外面的小伙伴儿把我拽出窗户,跑出去疯玩。我们自排自演各种电影里好玩的情节和有意思的台词,也把家里仅剩的毛巾偷出去披在身上扮演杨子荣。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小伙伴们又赶紧把我从小木窗里塞进去。就这样酷爱着哼哼呀呀,蹦蹦跳跳,和我妈迂回周旋。快乐的事总不会天天跟着你的,我妈还是发现了我的秘密,逃不了痛打一顿。
我疼的躺在床上起不来,听见爸和妈说:你打就打屁股吗,别的地方别使劲打呀,她还小。妈妈说:她小?那老二怎么知道听话呀?打,还顾得上打屁股还是打脑袋?你看看你女儿那个倔样子?啊,敢背着我跑出去又唱又跳,这不成妖精了?妈妈说的老二是妹妹吴静,妈妈最喜欢的女儿。
十岁那年,我代表县第一小学宣传队参加全县汇演。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让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我红了,迅速成为繁昌县家喻户晓的人。以至于遇着我爸妈的人都说:嘿哟,你们俩连“东方红”都不一定唱得全,你女儿的歌可是唱得真不错哦。我妈听了不仅没有一丝窃喜,反而恨死了,骂我妖魔鬼怪。
我们家,妈是主心骨。因为是妈把我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的,而爸爸却一直在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了十年,家里自然是妈妈说了算。妈妈不让我搞文艺,认为那是没有出息的人干的,说白了,就是戏子。而我偏要和母亲对着干。在她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也确实很不听话,从小到大。终于,我背着妈妈考上了安徽省艺术学校。那年,我十三岁,离开了县城,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的棍棒。原以为,我会像小鸟一样冲出了牢笼,可以自由地飞翔,快乐地飞舞。没料到,我想家,想妈妈,想得我躲在被窝里常哭湿了枕巾。也许是没开窍吧!第一学期放假,拿回家的成绩单,没有一门是过六十分的,妈妈差点又给我两个耳光。看在我半年没有回家,举起来的手又放下了。看着一样都不及格的成绩单,我第一次感到了羞愧。
1976年的夏天,妈妈带了好些花生、咸鸭蛋什么的搭顺便车来学校看我,正赶上我们上“把子”课,我拿着刀枪,一路唱着蹦着往练功房去,妈妈跟在我后面很久,就是不敢叫我。最后看我快要进练功房了,才怯怯地问了声:你是小琼吗?我没想到妈妈就站在面前,那个高兴劲儿,别提啦,一下子扑在妈妈怀里。妈许久没说话,当我抬起头,却发现妈妈眼睛红了。妈轻声地说:你怎么瘦了?我都不敢认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我说没有。那时我正在为改变胖小猪的形象而努力。
说实话,在学校时,最盼望的事,莫过于家里来人了,家里带来那些好吃的,足令我们兴奋好几个礼拜。毕竟,我们只有十三岁呀。十三岁到十八岁,我由一个野孩子,变成了大姑娘,我泼辣狂野的性格,在学校里磨平了很多,我变得少言寡语,又倔又拧。班主任的话我也有一搭无一搭的似听非听,没有课的时候,除了一个好朋友,我也不大和其他同学一起玩,集体活动更是极少参加。老师不理解,一贯对集体那么狂热的女孩为何变得这么冷漠?怀疑我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或受了什么刺激?便把我妈从老家叫了来。我妈听老师说,我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不听话的孩子,非常生气。又是“不听话”。
好在,我更多的喜怒哀乐,只一个人品尝,不想让妈妈知道,不想让她操心,不想让她打我。对于孩子,打,还是有作用的,特别是像我这样倔强淘气的孩子,不打,恐怕难以成材。我还是庆幸在妈妈的棍棒之下,成为了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一个爱父母的女儿。不过,我将来不想打孩子,我想换一种方式。
慈祥的父亲
爸爸,从小在我和妹妹心里就是一个大救星。从记事开始,爸爸被下放到农村,妈妈独自带着妹妹和我在县城生活。爸爸不忙的时候,一个月回来一两次。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开小差,想象着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家里的门是开的,烟囱冒着烟,那就是说我亲爱的爸爸回来了,他已经把晚饭给做好了,有时他会在门外劈柴,每次我都用近似短跑运动员的速度奔进家,抱着爸爸的脖子窜上去,用下巴噌他的胡子。一般,我会找爸爸要一两毛钱,然后撒丫地跑出去在同伴中炫耀,去买吃的,我们会一直玩到天黑而不用担心被妈妈揍。
在我们家,爸爸是慈父,绝对的;妈妈是严母,毫无疑问。
爸爸回家一般只能呆上一天或两天,而这个时候对于我和妹妹来说,像生活在天堂似的。因为,我们不用在妈妈下班之前要把饭做好,水缸里挑满水,还有毛巾,抹布要洗干净。这些爸爸都帮我们做了。我发现,爸爸在家的时候,妈妈心情会好很多,我们也因此很少挨打。
印象中,大约是我四岁的时候,爸爸被下放到农村的。所以妹妹出生时爸爸不在家。那天已经很晚了,妈妈要值夜班,家里没有人,只能把我带在身边,我才四岁,像一只小狗一样紧紧地跟在妈妈后边。妈妈在招待所工作,晚上要给客人准备热水。突然,妈妈挺着大肚子上不了楼,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因为水瓶里都装满了热水,妈妈强忍着把暖水瓶小心地放好,让我去叫人来。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我看见其他阿姨把妈妈扶到家,请来了阿婆,没有一会儿,就听见妹妹的哭声了。当时,妈妈不让我进屋里,我就趴在门缝里偷偷地看,一个好小的木盆里,妹妹睡在里面,很小很小的。后来,听妈妈说,生妹妹的时候,托人带信儿给爸爸,爸爸听说又是女孩,还有点儿不太高兴,也没有回家,说是乡下走不开。长大了,我们问爸爸是不是这么回事,爸爸不承认。
因为爸爸毕竟很少回家,五六岁的我便开始做家务。七岁已经学会烧饭,不是现在的电饭锅,是那种大锅灶。如果妈妈嘱咐我在锅里面蒸一碗鸡蛋,就算家里的荤菜了。妈妈是我们县里有名的干净人,有事无事要把衣服拿到大河里去洗。如果是换季的衣服,哪怕是干净的,妈妈也要重新从箱子里扒拉出来,到河里去洗一遍。通常是天没亮(大概是清晨三四点钟吧),爸爸挑着装满衣服的桶,陪着妈妈到东门河去洗衣服。我是没有这个胆量的,那个时候,也不知为什么?总有人对于谈论什么“水猴子”类似的话题乐此不彼,说得大多数妇女儿童没几个敢在天黑时走在河边,我妈妈是属于少数胆大的。
爸爸最头疼妈妈的讲究,妈说只有天还没有亮,别人不用水的时候,水才是干净的,没有污染。在她眼里,好像那些衣物比我们人还要珍贵,伺候起那些衣物,比对我和妹妹、爸爸都仔细、耐心。我想,妈妈是穷怕了,也可以说妈妈太勤劳啦。爸爸头疼妈妈的讲究,我也怕。我最怕冬天妈妈让我到大河里洗被子或鞋子,因为人小,被面儿大很难抖落的开,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容易把人给带到河里去。再有,就是洗鞋子,小时候穿得球鞋不知为什么那么脏,洗多少遍也不见清水,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全力,等晒干了以后,鞋子的边缘还是有一圈黄印迹,少不了挨妈妈说我惜力。要是爸爸在家,这些事爸爸就全给干了,真痛快呀,我可以大大地玩一下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头,只要有人在门外喊一声,就会不顾一切地冲出去。如果,妈妈在家,不让出去,心里就像猫抓似的。妈妈常说我,魂不在家里。其实,出去和小伙伴玩,也就是蹦蹦方格,跳跳皮筋,还兴一种把蒜苗的梢子打成结,你抛过来我砸过去的,和现在的小女生玩得花样实在是不能比。
爸爸从小没有打过我一巴掌,更没有打过妹妹。只有一次,爸爸举着木棍,要揍我,让我逃掉了。后来,我知道,其实爸爸并不是真的要追我,但是我确实把爸爸气着了,就那么一回。事情其实很小,但是却很让我爸生气。受妈妈的影响,潜移默化的,我对爸爸家的人不是那么热情。也因为大家不在一个县城,来往很少。一天,爸爸的侄子,也就是我的堂哥,到家里来,正好是吃饭的时间,爸爸让我再加点米,重新煮点饭,我不高兴地说:不煮。我特别拧,就是不给做,堂哥站在门口很尴尬,说算了,我出去吃吧,爸爸火上来啦,抄起柴火棍就要打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爸爸会揍我,所以一点儿准备都没有,还站在那里梗着脖子。当爸爸真要扑过来的时候,我才看见爸爸的脸色变了,着实吓着了,这才想起拔起腿跑。爸爸狠追了一通,看我躲到隔壁黄阿姨家,也就住了手。黄阿姨出来拦住我爸说:哎,老吴,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你怎么也打起你家大女儿了呢?我哭了,觉得委屈,还伤了爸爸的心,这件事在我记忆里一直很深。后来,我们对我二伯一家人,改变了态度。现在,爸爸也就剩下这唯一的哥哥了,所以2003年,爸爸说要请二伯和二妈来北京玩,我和妹妹都很热情的表示欢迎,并安排的很周到,爸爸十分满意。
初识黄梅戏
七十年代考艺术学校,也像考状元一般,一个县只中一名,我是幸运的那个“状元”。
十三岁那年,我开始学唱黄梅戏。这以前我也喜欢唱,可我只喜欢唱歌,大都是电影里的歌。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里面所有的歌我都会唱,我就是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战斗”到安徽省艺术学校,“战斗”到黄梅戏队伍里来的。十三岁,多么小的年纪啊!现在想起来,什么都不懂,是艺术学校的老师一点点的教,为我们费尽心思,才让我们迈进了这道门槛。
1975年夏天,我背着行囊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离开了长江边上的繁昌县,走进安徽省艺术学校。清楚的记得,当我站在迎接新同学的敞棚大卡车上时,那种快乐自由的感觉像风一般飞扬。我对妈妈说:我要唱戏了。我妈说:那有什么好,不过是为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呗。
我是第一个进学校报到的学生,可见我是多么迫切地想离开家。和现在的孩子相比,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独自去遥远的地方,恐怕是大人小孩都难以接受的。
我很泼辣,像山里的小辣椒,但我更热情,我不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却经常把自己扮成大姐的角色,把所有的激情和热辣都放在了这个集体,快乐的为每一位新到校的同学擦床铺,打开水,买饭,每一位送女儿来学校的妈妈都喜欢我,夸奖我重视集体、关爱同学,并一致选我做班长,这更激起了我的荣誉感,似乎也觉得自己有责任肩负这样的重担,把集体当作自己的家,一心一意的为这个“家”疯忙。
那时候,学校都要安排新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概就和现在的军训差不多吧。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叫小汤镇,十八个女生住在一间大屋子里,都是地铺,用稻草铺成的。白天我们到田里摘棉花,清晨和傍晚在晒稻场练功或学唱,突出的劳动成果并不能掩盖我在业务上的笨拙,因此,专业课上我常常是被老师骂的对象,也是一些同学私下取笑的素材。那时的老师都很严厉,对一些没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总怀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所以偶尔我还会挨老师的鞭子,特别是练习跑圆场,因为我是扁平足,既跑不快也跑不漂亮,挨鞭子就很正常了。所谓挨鞭子,不过是老师狠狠地举起,又轻轻地放下罢了,一点不疼,样子吓人,最要命的是丢脸。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业务落后而沮丧,我发誓要干出名堂来给他们看看,我一定要在业务上拔尖。我把自己的练功计划排得满满的,什么圆场、基本功、毯子功,什么唱腔、念白、小品,我都要争取第一。
对于学艺的孩子,老师若说这孩子开窍了,那就有戏啦。1976年的春天,我,突然开窍了。我那又亮又脆的嗓音开始引起同学们羡慕的目光。每次,我的唱念考试都是第一名,这让我非常得意,甚至有些不可一世的轻狂。
我做事的极端和任性是出名的,有时这很可怕。当我把兴趣和热情转到业务上的时候,除了练功练唱,我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我常常把练功后的脏衣服汗袜子扔在盆里好多天不洗,直到闷出馊味儿,害得几次卫生检查全班都评不上先进,同学们气坏了,为此和我大吵了一架。还有,练什么都不惜力,不仅自己如此,对合作的人也不放过,如排戏的搭档,只要有空就一起练习。
临近毕业,每一位同学都在为毕业去向而奔忙。当时,我那么希望分配到省黄梅戏剧团,是因为我的初恋男友在合肥工作,所以为了他,我要努力争取留在合肥,当然,我也自信地认为,我出色的专业成绩会为我赢得进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机会。所幸的是,我终于被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同时,分配到剧团的有十个同学,五男五女。五个女生就是后来被人们热称的“五朵金花”,男同学当时虽然没有显山露水,但现在,他们都是黄梅戏界的顶梁柱。当然也有彻底改行做别的去了。
我以总分第一的毕业成绩离开了安徽省艺术学校,走进安徽省黄梅戏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