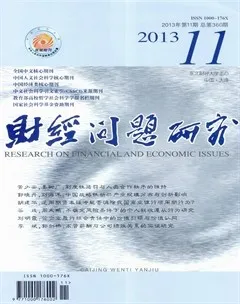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错位研究
2013-12-29孔繁彬
摘 要:自帕特里克提出“跟随需求”和“供给导向”两种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模式后,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主题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争论。现代金融于各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凸现了对这一主题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机构部门视角,兼顾理论框架和现实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未推动非金融企业部门经济增长,阻碍了住户部门经济增长,但是优化了机构部门构成,推进了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发生错位,金融改革陷入两难境地。
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机构部门;错位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1-0055-06
一、引 言
针对这一主题,国外文献大致可以被归纳为宏观国家、中观产业及微观企业三种层面的研究。
宏观国家层面上,King和Levine[1]认为以银行或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发展水平皆对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积累率及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稳定的促进作用。Tadesse[2] 则认为随着一国金融部门发达程度的提高,相对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对经济促进作用会越来越显著。Hung[3]构建的内生增长模型表明当政府支出相对较大时,多重均衡便会实现,金融发展会增加通货膨胀,降低初始通货膨胀率较高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初始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时,金融发展才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促进经济增长。
中观产业层面上,Rajan和Zingales[4]认为金融发展会通过降低产业向外部融资的成本直接促进产业增长,并通过技术创新间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和产业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产业的规模构成及产业集中度。Wurgler[5]以及Fisman和Love[6]从不同视角论证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微观企业层面上,Kunt和Maksimovic[7]认为法律体系越是完善的国家,其能够提供长期债务的债券市场和提供股权资本的股票市场越发达,这样公司外部融资的可得性越高、融资成本越低,公司增长也就越快。Castaeda[8]的
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是非线性关系,尤其是当机构较弱时股票市场的形成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基于不同覆盖范围和不同视角做了大量的研究。基于国家整体的研究文献中,冉茂盛等[9]认为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袁云峰和曹旭华[10]认为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王志强和孙刚[11]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基于地区局部的研究文献中,钱方明等[12]以单个省市为具体对象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而孙杨和杨俊[13]则进行了多地区或中东西部的比较研究。基于不同视角的文献中,韩正清等[14]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视角探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
冉和光等[15]从产业视角对主题进行研究,孙佳钧等[16]基于资本账户视角对中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在资本账户不开放的条件下,国内金融深化对本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国内金融深化对本国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供给导向说”在二者关系的争论中处于上风。国外的大部分研究覆盖了许多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包括中国,因而国外研究成果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金融与经济发展。国内研究的进展滞后于国外,大部分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上,对产业、企业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即使是中观层面上的分类,机构部门分类并没有产业部门分类那样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创的这一科学性极强的分类思想被证明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的基石,与三次产业分类相比,将整体经济按此法分类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有利于更细致、更具针对性地分析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关系及其形成原因,有利于更好地揭示总体现象,发现普遍规律。因此,本文以此作为切口对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研究。
二、基于机构部门视角的经济与金融构成分析
(一)机构部门构成分析
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共同构成了参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部门,其中企业部门又可细分为金融机构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
中国经济总量的九成以上是由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增加值所组成,二者呈此消彼长关系,企业部门与住户部门总量贡献率的时间分布分别近似U型和倒U型,其中新千年作为各自贡献率趋势变化的转向时点,两部门生产增量贡献率变化速度均大于总量贡献率变化速度,而政府部门作为管理、协调和监督的部门其经济增加值比较稳定。由于金融机构部门与非金融企业部门规模差异较大,为客观评价二者贡献,采用反映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经过二次收入分配对社会贡献份额的相对贡献率来比较两部门社会经济贡献率。中国企业部门社会经济贡献率阶段性特征明显,金融机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相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对社会的贡献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区域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金融机构部门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意味着它在享受机会的同时,也将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一般来讲,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越大,说明该国国民经济增长所蕴涵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先进性越强(弱),因而机构部门构成水平也就越高(低)。
(二)金融资产构成分析
中国金融体系呈现银行主导和政府主导的双重特征模式,具体表现在巨大的银行类金融资产份额约占金融总资产的70%以上和政府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在全部金融机构中所占的绝对比重。据统计,截至2013年3月,在各类银行资产构成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比为43.90%,由各级政府持大部分股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占比分别为18.00%和9.30%,这意味着不包括其他类金融机构中的政策性银行时,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银行总资产占据了全部金融机构的七成以上。
社会资金循环系统中,企业部门是资金的主要融入者,住户部门是资金的融出主体。从企业部门融入资金看,中国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以外源融资为主,内外源融资严重失衡,企业的留存收益过低,无法支持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只能通过具有政策倾斜性质的高负债来融通资金。尽管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
呈上升趋势,但是这种带有上升趋势的高资产负债率将成为银行和上市公司的巨大隐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内源融资
虽然中国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约束略有放松,但是对其贷款比重仍然非常低,它们只能依靠留存收益和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进一步发展。另外,2006—2008年企业新增资金来源中直接融资比重较2001—2003年有了较大提高,说明中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为企业开拓了融资渠道,增加了企业通过市场直接融通资金的便捷度,同时也缓解了中国银行的信贷压力,分散了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
从住户部门融出资金看,储蓄存款依旧是中国住户部门的主要融资方式,除2007年,新增储蓄存款均占住户部门资金总融出的八成以上,这说明中国居民在选择资金融出方式上的传统观念并没有改变,仍然将安全性和保障性摆在首位,这一点也促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垄断特征。保险支出在2002年实现了跳跃性增长,随后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但绝对额与融资比重仍然较小。
城乡居民存款结构较为稳定,城镇和乡镇居民存款占比分别维持在80%与20%左右,这种稳定性体现了中国居民存款分布的不均衡性,而不均衡性又反映了城乡可支配收入和参与潜在金融活动能力的差距。
定期存款占比的下降意味着活期存款比重的提高,说明住户部门具有高流动性、强交易性的资金需求的倾向性,随之而来的是消费和生产经营意愿的增加,而近年来住户部门资金融入的增加也证明了这点。
中国住户部门资金融出方式以储蓄存款为主,当这一比重过大时,就导致了银行绝对垄断和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外源融资方式,这样三者任何一方利益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余二者,严重时会冲击到整个金融体系,而为了稳定风险,政府就会介入,政府的介入又进一步强化了银行垄断,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的融资结构仍然不会改变,如此往复,金融系统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三、中国机构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指标
本文采用代表着企业实体经济总量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增加值(NFQY)和
住户部门增加值(ZH),并购建经济发展水平的现代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XDH)指标,其由企业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增加值与住户部门增加值的比值构成,该比值越大,经济发展水平的现代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越高。
1992—2008年的各个机构部门的增加值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得到不变价增加值数据,用GDP平减指数(1992年为基期)除现价增加值以剔除价格因素,而各部门现价增加值根据结构赋权平摊处理后得到。
2.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采用传统的金融发展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
金融结构比率(FSR)和金额中价效率(SLR),但在处理方法上略有改进。FIR指标是存量指标与流量指标的比值,为了满足时间可比性,将上期和本期的金融资产加总再除以2倍的本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由存款余额、贷款余额、流通中的现金、股票市值、债券(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保险费收入和国外资产(由金融资产近似替代)构成,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其中,2005年和2006年企业债余额根据发行额、汇兑额与余额关系计算而来,2002年和2003年企业债余额根据EXCEL的规划求解功能近似估计而来;1991—2003年和2004—2008年储备资产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2006—2007年)和《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储备资产数据需经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换算处理,汇率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 基于VAR模型的机构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检验与分析
1.变量平稳性检验
将绝对量指标NFQY和ZH做对数处理后,再对各个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LNFQY、LZH、XDH、FIR、FSR和SLR都是非平稳变量,经过一阶差分之后,所有变量在5%置信水平下平稳,即原序列都为一阶单整,且单位根检验的各个方程都通过了变量系数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检验等相关统计检验(如表1所示),故符合协整检验和VAR模型的准入条件。
2.非金融企业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向量自回归分析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明,LNFQY、FIR、FSR和SLR之间有且只有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协整向量为(1,-4.20,12.54,-14.51)′,即LNFQY和 FIR、SLR存在正向长期关系,而与FSR之间有负向长期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明,FIR、FSR和SLR都不是引起LNFQY变化的原因,LNFQY是引起FIR和SLR变化的原因(5%显著性水平),而它的变化对FSR有较弱影响(10%显著性水平)。综合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结果,可以判断FIR、FSR和SLR的变化不会导致LNFQY的变化,LNFQY的变化会对FIR、FSR产生正向影响,对FSR具有弱负向影响。
3.住户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向量自回归分析
根据SIC与AIC准则选取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稳定,结合表4以及LZH分别与FIR、FSR、SLR的双间脉冲响应和方差贡献图(图略,需要者可与作者联系)可知,FIR、SLR不是引起LZH变化的原因,FSR是引起LZH变化的原因。LZH变化是引起FIR和SLR变化的原因,它对FSR有较弱影响(10%显著水平)。FSR对LZH有较大的负向冲击作用,方差贡献度自2期过后一直维持在50%的水平。LZH变化对FIR和SLR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当给LZH方程误差项一个正向冲击时,会造成FIR的正向变化和SLR的负向变化,对两者的影响力度从3期过后均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虽然LZH对FSR有微弱影响,但整体看来FSR是LZH变化的原因之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4.经济现代化程度与金融发展的向量自回归分析
根据SIC与AIC准则选取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稳定,结合表5以及XDH分别与FIR、FSR、SCR的脉冲响应图和XDH序列的Cholesky方差分解结果(图略)可知,XDH不是引起FIR、FSR和SLR变化的原因,而FIR、FSR和SLR都是XDH变化的原因。其中,FSR以1%的显著水平拒绝了原假设,FIR和SLR分别在5%水平上成为XDH的Granger原因。在3个金融变量中,FIR对XDH的冲击最大,自2期过后,方差贡献稳定在12%以上的水平,且效用逐期增大,但增幅不大。与FIR对XDH作用方向相同,当给FIR方程误差项一个正向冲击时,经过各期传递,最终会使XDH做出同向响应,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短期看,SLR会对XDH产生正向作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4期后),会对XDH产生负向作用,整体看来,正负效应相互抵消,作用效果也不显著。综合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知,XDH对FIR、FSR和SLR没有影响,FIR和FSR对XDH有正向影响,SLR对XDH有短期正向影响和长期负向影响。
(三)实证结果及其经济解释
1.实体企业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关系
实体企业经济增长导致了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表现为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效率的提高,而金融发展并不是实体经济增长的原因。近些年以来,中国不断地扩大金融规模,积极地大力发展以股票市场为主导的资本市场,但是为什么却没有收到预想的成效呢?或者说,为什么被西方国家普遍认同的“金融功能理论”在中国却失效了?从实证结果看,首先,实体经济增长会导致金融效率的提升,这与中国金融效率下降的事实矛盾,但却凸显了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效率问题。其次,实体经济增长并不会促成金融结构的调整,相反存在微弱的抑制作用,但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是明显的,这说明中国金融结构的改变是政府强制牵引的结果。近年来,虽然中国一直在对金融结构进行着调整,但是对资本市场的扶植主要是以股票市场为主,股票市场的发展是为了以更小的成本获得融资,以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和健康成长。但是,这些获得融资的企业未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有效率”的企业,有些企业进行“圈钱式”的融资可能别有所图。相反,那些最有效率的、只能依靠内源融资的企业常常因为无法获得充沛资金而丧失应有的竞争力。
商业银行将资金贷给拥有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这不仅使得一些国有企业失去了创新的活力,变得懒散、臃肿,反过来又导致金融中介机构丧失了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寻求利润的正常本性和动力,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资金并没有配置到最具活力、最有效率的实体企业。另外,即使商业银行“愿意借”,这些企业也无法负担高贷款利率的成本,中国确实存在融资渠道单一的缺陷,也说明中国银行业是一个暴利行业,因而改变这种格局就显得非常重要。
2.住户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需求跟随”关系
中国金融发展对住户部门增加值没有促进作用,住户部门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规模的扩张,住户部门经济与金融发展也呈现了“需求跟随”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住户部门经济增长对金融规模有正向影响,而对金融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住户部门强调的是非法人企业,包括住户非法人市场企业和自身最终使用的住户企业两种。住户生产无论是从经营规模上还是管理层次上都与具有企业性质的生产单位不同,无法与现代化大生产相提并论。既然很多企业单位都无法获得外源融资,那么收益风险较大、利润率较低的住户部门就更不可能通过商业银行或资本市场进行间接或直接的外源融资以扩大生产。虽然金融规模和效率的提高并不是住户部门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金融结构的调整却会对住户部门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是股票市场的风险和震荡较大给住户部门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
3.经济现代化与金融发展的“供给导向”关系
中国金融发展为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与市场化提供了重要贡献力量,即二者存在“供给导向”关系。需要解释的是,虽然中国机构部门构成水平进步缓慢,但是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因为影响它的因素是多元化的,它的进步程度取决于各种影响因素的力量“碰撞”和“中合”,而对于其他因素是如何影响机构部门构成水平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四、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金融发展未推动非金融企业部门经济增长。非金融企业部门是对中国经济贡献份额最大的机构部门,随着该部门增加值的不断扩大,该部门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从而推动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金融发展仍然处于“需求跟随”阶段,金融功能仍然停留在支付、结算水平,金融体系资金配置功能的失效使得资金流向不合理,削弱了企业部门创新能力,无法引导产业链升级,阻滞了企业部门经济增长和经济模式的转变。
第二,中国金融发展阻碍住户部门经济增长。住户部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之一,其对经济绝对贡献仅次于非金融企业部门。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化,作为住户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户及乡镇企业增加值迅速扩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将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促进金融规模扩大。但是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满足住户部门的融资需求,这使得住户部门生产扩大化难以持续,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升级。
第三,中国金融发展优化了机构部门结构,推进了经济现代化、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看,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与市场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核心地位。金融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调整使得中国金融整体水平不断提升,金融发展又使得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得到了充沛的资金支持和保证,使住户经济为主的“乡村”向企业经济为主的“城镇”转变,也使得“农村”向“农业”转变成为可能,推动了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发生错位,金融改革陷入两难境地。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余震未退,全球经济尚未恢复元气,中国未来经济前景不容乐观,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对主导地位的争夺,金融资本的配置损失,由此导致的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错位。改变这种关系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发展很快、如今却已陷入两难境地的金融改革。如果“按兵不动”,金融资本配置效率低,阻碍了包括民族产业的实体企业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下的产业链升级举步维艰,不益于国家整体利益。如果“全速行军”,金融资本食利集团越发壮大,金融业泡沫不断膨胀,金融系统风险日益加深,未来政府信用压力会增大,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现实中可能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本文认为“全速行军”的方法不是不可行,而是时机尚未成熟,它实施的重要前提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以及人民币至少可以和美元、欧元、日元为核心的货币联盟分庭抗礼。因此,渐进式金融改革既是谨慎之举,亦乃明智之举,目前的关注点应放在对金融系统的适时整顿和对金融资本的合理疏导之上。
参考文献:
[1] King,R.G.,Levine,R.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108(3):717-738.
[2] Tadesse,S.Financial Archite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Evidence[R].William Davidson Working Paper,No 449,2002.
[3] Hung, F.S.Infl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3,12(1):45-67.
[4] Rajan,R.G., Zingales,L.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3):559-586.
[5] Wurgler,J.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 58(1):187-214.
[6] Fisman,R.J., Love,I. Trade Credit, Financial Intermediar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 Growth[J].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3, 58(1):353-374.
[7] Kunt,A., Maksimovic,V. Funding Growth in Bank-Based and 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s:Evidence from Firm Level Dat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2002,65(3):337-363.
[8] Castaeda,G.Economic Growth and Concentrated Ownership in Stock Market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06, 59(2):249-286.
[9] 冉茂盛,张宗益,钟子明.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联性的实证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2):617-648.
[10] 袁云峰,曹旭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7,(5):60-66.
[11] 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60-66.
[12] 钱方明,孙克,汤钟尧.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以浙江为例[J].上海金融,2008,(6);69-74.
[13] 孙杨,杨俊.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研究——基于我国三大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J].经济经纬,2012,(2):32-36.
[14] 韩正清,王燕,王千六.城乡经济金融二元结构:理论关系与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0,(2):118-123.
[15] 冉光和,吴昊,邵腾伟.金融支持与产业集群发展:西部省(市)的经验证据[J].广东社会科学,2011,(3):34-41.
[16] 孙佳钧,何家宏,刘厚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本账户视角的实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9,(9):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