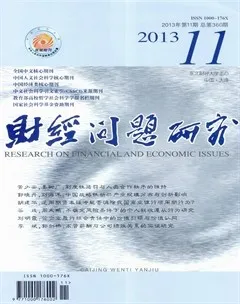逆周期资本缓冲能否消除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
2013-12-29胡建华
摘 要: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指引》,我国“十二五”规划也正式提出了实施的基本路径。逆周期资本缓冲实施的关键在于选择有效的识别指标,将资本要求与该指标挂钩。但在我国,由于指标正处于结构性变化之中,数据非平稳,含义不明确。且对于指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尚缺乏完整的周期性数据进行检验,所以指标的可靠性未被证明。本文建议慎用逆周期资本监管,如确实需要实施,可采取先相机抉择,后规则的方案,并在参考信贷余额/GPD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其他宏观经济变量。
关键词:逆周期监管;顺周期性;巴塞尔协议;HP滤波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1-0048-07
一、引 言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将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定义为一种相互强化的正反馈机制,在该机制下,金融系统会放大宏观经济的波动程度,反过来又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表现为信贷增长率与经济周期同方向波动,在经济上行阶段,信贷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在经济下行阶段,信贷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金融危机显示出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巨大破坏力,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提出缓解顺周期性的政策工具,我国也同意了二十国集团的方案;2009年11月,巴塞尔委员会成立宏观变量工作组,负责逆周期资本缓冲的研究,我国银监会也全程参与了该项目;2010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宏观变量工作组提交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并在全球征求意见;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指引》,要求各国遵照执行;我国“十二五”规划正式提出了实施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基本路径。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思路是,基于商业银行信贷顺周期性的各种形成原因,金融风险会在信贷扩展期积累,在信贷收缩期释放,从而带来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波动。逆周期资本缓冲在信贷扩张期计提资本缓冲,从而提高整体监管资本要求,以控制信贷规模;在经济转向下行,信贷规模开始收缩时释放资本缓冲,从而降低整体监管资本要求,以扩张信贷规模。逆周期资本缓冲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其为整个银行体系设置一个统一的资本缓冲乘数,无需考虑银行之间的差异性,也不必涉及银行微观层面的风险结构,可以降低措施的实施成本,并能够较为有效地防止监管资本套利。逆周期资本缓冲的目标在于通过资本的计提与释放,控制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降低信贷扩张期所积累的系统性风险,从而防止信贷危机。实施的关键在于能够识别繁荣与衰退,把握增加和释放资本缓冲的正确时机。
但我国的金融结构相对特殊,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否能够发挥预期效果存在诸多疑问。目前,我国银监会对于逆周期资本监管尚未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本文旨在对逆周期资本缓冲在我国的可行性进行讨论,为监管部门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二、相关文献综述
对于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存在性的证据,Bikker和Metzemakers研究发现,银行拨备在GDP增速放慢时显著提高,在GDP 增速较快时则明显减少[1]。IMF对欧洲银行业贷款损失准备金同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前者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特征[2]。对于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因素的讨论, Catarineu-Rabell等指出,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银行更倾向于采用时点评级法而不是跨周期评级法,从而进一步加强了顺周期性效应[3]。Aguiar和Drumond对巴塞尔协议I与II进行了实证比较,指出一国的资本监管规定越接近于巴塞尔协议Ⅱ,顺周期性越显著[4]。Frank对巴塞尔协议所导致的顺周期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逆周期资本缓冲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的思想[5]。Repullo和 Suarez指出巴塞尔协议Ⅱ允许商业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测算贷款违约率(PD)和违约损失率(LGD),两者都具有顺周期特征[6]。Andersen对挪威1988—2007年个人、企业及金融机构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如果能基于一个足够长的观察期来确定风险权重,则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监管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可以被有效遏制[7]。对于逆周期资本监管,Panetta等指出监管资本、杠杆比率、会计规则、管理激励等工具有助于缓解顺周期性[8]。Hanson等认为动态资本监管以及流动性监管有助于缓解顺周期性[9]。Repullo等对GDP增长率、信贷增长率以及股票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GDP增长率的平滑效果最好[10]。Drehmann等的研究表明,信贷/GDP指标较GDP增长率更为理想,逆周期资本缓冲应着眼于金融周期而非整个经济周期[11]。
在我国冯科等人利用VEC模型对我国1998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和信贷规模进行了互谱分析,发现我国银行信贷存在顺周期性[12]。刘灿辉等对我国6家上市银行2003—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缓冲资本具有顺周期性[13]。李文泓和罗猛对巴塞尔协议资本缓冲政策框架在我国银行业的应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信贷余额/GDP指标在我国具有较好的适用性,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有利于提升银行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14]。杨柳等以金融脆弱性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了信贷余额/GDP指标在我国的适用性,也认为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我国可行[15]。孙志娟分析了我国银行信贷在经济下行时期凸显的一系列亲周期性隐患,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逆周期信贷路径的选择[16]。
三、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表现及成因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是否存在顺周期性,由于计量方法和样本区间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不存在信贷规模控制的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体现出了较强的顺周期性。对于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成因,其中包含一些具有我国独特制度背景的内容。
(一)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表现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是否存在顺周期性,许多学者做过大量经验研究,但由于计量方法和样本区间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经济意义也略显含糊。本文从顺周期性的内涵入手,认为顺周期性应表现为信贷余额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顺周期性讨论的前提是银行信贷具有内生性,如果信贷规模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那么信贷对于GDP的反应则会基于央行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进而成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由于货币政策天生具有逆周期性,所以当信贷规模被控制时,商业银行应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逆周期性而非顺周期性。一个更加明确的研究对象,是不存在信贷规模控制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的存在性。这样的定位也是因为:一方面,信贷规模受控制时,资本监管对于信贷规模的传导渠道被阻断,再研究逆周期资本缓冲已无意义;另一方面,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实施必然出现在未来信贷规模监管取消,银行信贷行为更加市场化的条件之下。从我国信贷规模监管的历史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贷规模控制逐渐淡出;2007年,由于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明显,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央行重新启用信贷规模监管。为了降低央行对信贷规模的直接影响,我们将区间划分为2007年之前,与2007年之后两段分别讨论。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7年之前,信贷余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依性,经统计测算相关系数为0.32,自由度(n-m-1)为58,根据相关系数检验临界值表明,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为0.25,说明两者体现出高度的相关性。所以,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不存在信贷规模控制的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体现出了较强的顺周期性。
(二)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成因
1. 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内生原因
第一,扭曲的同业竞争导致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羊群效应。首先,我国尚未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较高的存贷款利差为商业银行带来了垄断利润,而这种垄断利润需要通过做大资产规模来实现,加之我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并未出现过明显的金融危机,所以商业银行在经济上行时,通过激烈的竞争以维持或增加市场份额;其次,商业银行对贷款客户的信息搜寻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其会利用其它银行对于贷款客户的信贷行为作为其信贷决策的参考,这也同样导致了羊群效应;最后,目前我国的银行竞争主要体现为银行的排名,而非企业实际价值,与同业保持一致性行为也是规避排名风险的一种理性选择。
第二,尚不健全的委托代理制度诱导经理层盲目扩张。首先,在我国目前较为短期的考核制度之下,在经济上升期,过度信贷在短期内会导致银行利润增加,却不会立刻带来不良贷款,同时也能够维持或扩大银行的市场份额;其次,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依然处于规模竞争阶段,管理层利用经济上升期较为宽松的制度条件实现信贷规模的扩张可以提高其行业地位,并增加其收入水平。
第三,银行自身还不能摆脱适应性预期的非理性思维。适应性预期是人类普遍采取的一种预期方式,与理性预期不同,其根据近期的经济走势来判断将来的经济走势。表现为在经济上行期,人们普遍继续看涨,在经济衰退期,人们普遍继续看跌,这也导致了灾难短视现象。
2. 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外生原因
第一,资本监管下银行风险评估方法存在顺周期效应。在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模式下,银行风险评估的顺周期效应主要是通过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分母即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实现的。巴塞尔委员会在对银行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详细规定了处理方法,其中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IRB)使银行对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估计值成为计算资本的主要参数。然而,无论是基于当前经济状况的时点评级体系还是基于完整经济周期的跨周期评级体系,其风险评估结果都与经济周期呈负相关关系,从而强化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行为。
第二,会计准则下银行资产计量方法存在顺周期效应。在现行财务会计准则下,银行资产计量的顺周期效应体现为贷款损失专项准备计提的顺周期效应和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效应,它主要是通过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即资本的计量来实现的。商业银行贷款损失专项准备计提的顺周期效应的根源在于会计准则的可靠性和谨慎性原则使贷款损失专项准备只能根据当前时点显现的风险状况计提,因而与时点评级法下资本计提的特征大致相同,即与经济周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估计受到市场价格随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背离了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
四、我国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实证分析
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12月发布的《指引》对逆周期资本缓冲已经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计算框架,包含了具体的实施步骤与模型参数。本文依据《指引》所给出的方法,运用我国1998—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模拟了如果我国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各历史时点的资本缓冲要求。
(一)巴塞尔委员会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介绍
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实施的关键在于选择有效的识别指标,将资本要求与该指标挂钩。巴塞尔委员会建议使用信贷余额/GDP作为识别指标,用该指标对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计算是否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以及所需计提的数量。巴塞尔委员会的建议,是通过对近四十年,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四十多次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得出的。其对比了GDP 增长率、信贷增长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信贷余额/GPD等宏观经济金融指标,银行业利润率和损失率等业绩指标以及存贷款利差等融资成本指标,3大类近10个指标,其中信贷余额/GDP具有最佳的识别效果。
具体操作步骤:第一,计算信贷余额/GDP的数值(Rt),Rt=Ct/GDPt,其中Ct表示第t期的名义信贷余额,为广义统计口径,具体包括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个人理财中的信贷资产和资产证券化等。GDPt表示第t期的名义GDP。第二,计算信贷余额/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度(GAPt),GAPt = Rt-Trendt,其中Trendt是根据HP滤波法计算的信贷余额/GDP的长期趋势,巴塞尔委员会建议HP滤波使用单边趋势法,其中参数λ=400 000。第三,将偏离度转化为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VBt),巴塞尔委员会建议,在偏离度低于下限L时,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设定为0;在偏离度高于上限H时,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设定为2.5%。下限L为2,上限H为10。当偏离度处于上下限之间时,偏离度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计提比例升高0.3125个百分点。
(二)逆周期资本缓冲在我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了与《指引》相同的计算方法与模型参数,选用了1998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1季度的季度数据。因为1998年,我国正式放弃信贷规模控制,信贷市场化初步形成。其中GDP季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季度数据统计,折算成了年度GDP,并消除了季节影响;信贷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统计。实证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在2002年第1季度至2005年第1季度这3年中,以及2009年第2季度至今的4年中,信贷余额/GDP显著性的高于长期趋势值,有必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且在大部分季度资本缓冲数额达到或接近上限2.5%。2013年第1季度,我国M2超过100万亿元,全球第一,信贷余额/GDP也接近了150%。巴塞尔委员会的研究认为,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逆周期资本缓冲不会频繁使用,而是10—15年使用一次。但中国的情况却是在过去的15年内,有7年时间需要持续地,大幅度地使用逆周期资本缓冲。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我国信贷余额/GDP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
五、我国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实施困境
巴塞尔委员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思路,已经被绝大多数研究人员所接受。但实施的关键在于识别指标是否有效。由于金融结构的变化以及数据的缺乏,我国尚难建立行之有效的识别指标。而信贷余额/GDP指标在我国的适用性,面临诸多挑战,且难以得到数据的有效支撑。
(一)识别指标正处于结构性变化之中,数据非平稳,含义不明确
信贷余额/GDP指标的高速增长,我们认为源于以下四方面原因,而这些因素在近期都可能出现方向性转变,导致信贷余额/GDP指标的有效性遭质疑:第一,货币化进程。持续的货币化进程,是我国信贷余额/GDP指标在过去几十年内高速增长的首要原因。对于货币化是否已经结束,以及何时会结束,尚存争议,但是学者们公认一点,就是我国的货币化进程已经处于尾端。所以,由货币化进程所导致的信贷余额/GDP的上升即将结束。第二,以投资追逐GDP。我国GDP持续高速增长,排名世界第一。投资是推动GDP增长的首要动力,投资结构又以政府或国有企业为主,其资金来源几乎都集中于银行信贷。这也是我国近年来信贷余额/GDP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其他问题,各界对于此种模式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反对态度,且中央领导人也表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以,信贷支持投资以推动GDP增长的方式很有可能在近期出现转变。第三,信贷主导型融资结构。银行信贷在我国的融资结构中长期处于主导型地位,这使得信用扩张需求大多需要通过银行信贷予以满足。但近年来直接融资模式快速增长,银行信贷以外的影子银行在2012年与2013年更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调整融资结构,降低银行信贷比例已经是必然的发展方向,而在原有结构下形成的信贷余额/GDP指数可能也难以服务于新的金融环境。第四,高存贷款利差导致银行长期规模竞争。尽管利率市场化呼声不断,但是在存贷款利率管制下,我国商业银行已经享受了十多年垄断利润。而由存贷款利差所导致的垄断利润需要通过扩大信贷规模予以实现,所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商业银行始终处于规模竞争阶段,这也导致了信贷余额/GDP的高速增长。2012年7月利率市场化再次启动,垄断利差与规模竞争可能很快成为历史,这将大大削弱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动力。综上所述,我们预测信贷余额/GDP指标将出现拐点,此后其增长速度会显著下降,并长期低于趋势值。与此前需要高比例、大幅度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相反,在此后的若干年内,按照巴塞尔委员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测算,我国可能都无需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但这其实并不意味着我国就不具有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必要性。
此外,信贷余额/GDP指标有效性实施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该指标的时间序列在统计上平稳。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由于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显著性变化,所以信贷余额/GDP指标表现出较好的平稳性。但我国正处于改革过程之中,尤其是近10年来,正是实体经济改革基本完成,金融领域改革快速进行的阶段,所以每一期的数据实则并非生成自相同的模型。从图3可以看出,信贷余额/GDP指标并不平稳,体现出越来越快的上升趋势,且波动幅度也越来越大。一阶差分则能更好地反映出这种非平稳性。单位根检验也支持了我们的结论,信贷余额/GDP指标并不平稳,有效性存在问题。
(二)对于指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缺乏完整的周期进行检验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目标在于通过资本的计提与释放,控制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降低信贷扩张期所积累的系统性风险,从而防止信贷危机。识别指标应能够表征信贷的扩张与收缩,在信贷扩张阶段,指示监管部门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在信贷紧缩阶段,指示监管部门释放逆周期资本缓冲。但信贷余额/GDP指标是否能有效识别信贷的扩张与收缩呢?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信贷的扩张与收缩?解决上述疑问,必须通过实证检验。但是近30年来,由于各种经济增长动力的释放,以及政府高效率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并未出现过经济危机,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经济周期。而要检验信贷周期的识别指标,需要多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尤其需要积累经济危机的数据。国内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通过信贷规模/GDP指标与表示金融脆弱性的指标体系之间的关联度,来检验信贷规模/GDP指标的效率。主流观点认为,信贷规模/GDP指标具有较好的识别功能。但金融脆弱性指标体系毕竟不是金融危机本身,且信贷规模/GDP指标是大多数金融脆弱性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较高的关联度更多的是因为检验本身就是自己解释自己。所以,数据的缺乏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于识别指标可靠性的把握。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是否存在顺周期性,由于计量方法和样本区间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不存在信贷规模控制的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体现出了较强的顺周期性。第二,我国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具有一定的制度特色,包括扭曲的同业竞争,尚不健全的委托代理制度,非理性的银行决策以及资本监管与会计准则所具有的顺周期性等。第三,我们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所发布的《指引》,模拟了如果我国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各历史时点的资本缓冲要求,表明在2002年第1季度至2005年第1季度的3年中,以及2009年第2季度至今的4年中,有必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且在大部分季度资本缓冲数额达到或接近上限2.5%。第四,巴塞尔委员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思路,已经被绝大多数研究人员所接受。但实施的关键在于识别指标是否有效。信贷余额/GDP指标在我国的适用性,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信贷余额/GDP指标正处于结构性变化之中,数据非平稳,含义不明确;另一方面,对于信贷余额/GDP指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尚缺乏完整的周期数据进行检验。所以,无法证实信贷余额/GDP指标在我国是否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提出几点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慎用逆周期资本监管。首先,现有制度的扭曲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通过制度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顺周期性,其路径比引入逆周期资本缓冲抑或更为可行;其次,在信贷规模控制尚存时期,资本监管对于信贷规模的传导渠道受阻,且监管部门完全可以通过信贷规模控制直接调节信贷余额,无需借道逆周期资本缓冲;最后,由于信贷余额/GDP指标的有效性存在诸多缺失,所以目前实施逆周期资本监管存在较大风险。
第二,先相机抉择,后规则。如确实有必要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我们建议首先采取相机抉择的方式,由监管部门通过主观判断来决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规模,而不采取与指标直接挂钩的方式。首先,巴塞尔委员会并未否决该种方案,且国际上大多数学者也都认为在实施逆周期资本监管之初,相机抉择可能是比规则更加合适的方案;其次,我国其他银行监管规定大多使用相机抉择的模式,这与整体决策逻辑基本吻合;再次,在信贷余额/GDP指标可靠性获得证明之前,主观判断可以考虑更加丰富的因素,比规则更加安全高效;最后,在实施相机抉择之中要处理好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切勿将逆周期资本监管工具用于货币调控。
第三,综合考虑其他宏观变量。一方面,信贷余额/GDP指标受到结构性变化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在单一指标可靠性无法证明时引入多个指标将有助于降低决策风险。我们建议在参考信贷余额/GDP指标的基础上,引入房地产价格指数、CPI、PPI和用电量等指标,同时考虑经济运行情况、银行业风险状况和宏观政策变化等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 Bikker,J.A.,Metzemakers,P.A.J.Bank Provisioning Behaviour and Procyclical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2005,15(2):141-157.
[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EB/OL].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gfsr/2009/02/2009.
[3] Catarineu-Rabell,E.,Jackson ,P.,Tsomocos,D.Procyclicality and the New Basel Accord-Banks’ Choice of Loan Rating System[J].Economic Theory,2005,26(3):537-557.
[4] Aguiar,A.,Drumond,I.Business Cycle and Bank Capital: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under the Basel Accords[R].FEP Working Papers No 242,2007.
[5] Frank,H.The Cyclical Effects of the Basel II Capital Requirements[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7,31(12):3885-3900.
[6] Repullo, R.,Suarez, J.The Procyclical Effects of Basel II[R].CEPR Discussion Papers No 6862,2008.
[7] Andersen,H.Procyclical Implications of Basel II: Can the Cyclicality of Capital Requirements be Contained?[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1,7(3):138-154.
[8] Panetta,P.,Angelini,P.,Albertazzi,U.Financial Sector Procyclicality Lesson from the Crisis[R].Questionidi Econonimia e Finanza (Occasional Papers),2009.
[9] Hanson, S.,Kashyap,A.K.,Stein,J.C.A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Financial Regul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1,25(1):3-28.
[10] Repullo,R.,Saurina,J.,Trucharte,C.Mitigating the Procyclicality of Basel II[R].CEPR Disscussion Papers No 7382, 2009.
[11] Drehmann, M.,Borio,C.,Gambacorta,L.,Jimenez,G.,Trucharte,C.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 Exploring Options[R].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317,2010.
[12] 冯科, 刘静平, 何理. 中国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及逆周期资本监管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10):91-96.
[13] 刘灿辉, 周晖, 曾繁华, 李章祥. 中国上市银行缓冲资本的顺周期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3): 176-177.
[14] 李文泓, 罗猛. 巴塞尔委员会逆周期资本框架在我国银行业的实证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 2011,(6): 81-87.
[15] 杨柳, 李力, 韩梦瑶. 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金融体系应用的实证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 2012,(5): 34-40.
[16] 孙志娟. 关于我国商业银行逆周期信贷路径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2,(5): 158-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