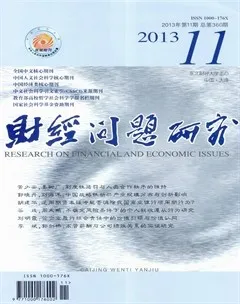制度性惩罚与人类合作秩序的维持
2013-12-29黄少安姜树广
摘 要:在存在广泛合作交往的当代大规模社会下,人类仍面临公共品搭便车、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现象所导致的合作困境问题。惩罚是维持人类合作秩序的基本机制,但是对人类合作起源与演化有重要影响的同辈惩罚学说需要利他性惩罚者的存在,在人类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制度性惩罚是保证任何规则都能够得以实施的基本前提。制度性惩罚是解决各种合约中潜在困境问题的关键,其有效实施的前提包括权利规则明确合理、具有权威公允的第三方以及通过激励改变惩罚的成本收益,以使惩罚成为“合算”的事情。
关键词:制度性惩罚;人类合作铁序;社会困境
中图分类号:F062.9;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1-0003-07
一、引 言
无亲缘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大规模合作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Pennisi[1]认为,这种合作生产的能力为人类祖先带来更多的食物、更好的保护和儿童照料,从而带来繁殖的成功并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Griffin等[2]以及Nowak[3]等学者认为,合作是个人背负一定的成本而使他人获益的行为,但是进化意味着个体间激烈的竞争,人类可以在大规模群体中与非亲属成员进行合作的现象令人十分困惑。Colman[4]指出,人类合作行为如何演化与维持是摆在演化生物学家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家面前的重大命题。对合作行为起源与演化的科学解释,出现了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网络互惠、群体选择以及基于利他性惩罚的强互惠等理论,这些理论为探讨人类合作演化的终极原因提供了部分解释。
探究合作的起源与演化固然重要,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如何维持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虽然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功解决了许多合作难题,但是在大规模社会下,人类仍然面临如公共品搭便车、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所导致的合作困境。人类发展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促进社会成员的合作,激励生产创造。惩罚在保障制度有效运作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在抑制违规行为、解决社会困境以及促进人类合作扮演着独到的角色。制度性惩罚是大规模社会条件下保障人类秩序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分析合作、制度与惩罚的相互关系,借鉴相应学科的研究成果,集中论证制度性惩罚如何保障社会基本合作秩序。
二、合作中的合约类型与社会困境
Hobbes[6]在《利维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讲述了由于个人追求自利的理性行为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悲剧状况,这就需要社会成员订立契约来规范个人行为。现代社会以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为特征,所有人都处于紧密的社会合作链条中,社会的运转实际是由一系列的合约组成的,当合约以明确的方式确定下来时,就形成正式的制度体系,默认的合约以社会规范的方式为人类行为规则提供指引。广泛的利他行为都可被视为一种合作行为,不论是市场交易、政府行为,还是家庭或朋友的交往,都可以抽象为一种合作,而交往中明确的或是默认的规则体系就构成了合约,这个合约具有为交往主体所公共认可的性质。根据参与方的地位状况和参与者数目,可以将合约进行如下的划分:
1.同等责任合约
同等责任合约的订约各方在合作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公共物品问题和公共资源问题是典型的同等责任合约。这类合约的参与者一般可以简化为同质的代理人,每个人对合约规范的责任是同等的,在执行规范和违反规范的选择权中的地位也是对等的。公共物品的合作困难主要在于搭便车问题,而公共资源问题则常被Hardin[7]描述为公地悲剧,合作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公共利益相冲突,理性自利人的占优策略必然是背叛。
2.不对等责任合约
同等责任合约的参与者常是多方的同质参与者,而所有不对等责任合约均可简化为双边的,即由参与双方正式或非正式地确定合约。合约双方的qG0mkb+e0BuGO4CmDXhDNg==责任一般是不对等的,双方在合约中的利益常常是相互冲突的,一方违约直接导致另一方的损失。根据合约参与者数目的不同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一对一合约。
双方签订的正式交易合同是常见的一对一合约,双方的市场势力基本对等,但双方掌握的信息常常不对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合约签订时和签订后都可能存在一方对合约默认规范的违反。这里的合作难题不是违约直接导致相关合作的瓦解(在违反规范的同时一次性合作已经实现),而是引致社会同类合作和后续合作意愿的降低,导致Akerlof[8]描述的“劣货驱逐良货”甚至市场的消失。现实中,信用在保证这类合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整个社会的道德信用又是一个“社会困境”问题。
第二,一对多合约。
一对多合约同样存在信息问题,且合约双方的地位(市场势力)一般是不对等的(如企业与员工的雇佣合约、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交易合约等)。具有市场优势的一方经常可以随意地更改订立的合约或无视合约规则,这时人数众多的弱势方的单个个体无力与另一方抗衡以保护合约规则。当强势方违约行为严重时,弱势方有时会走向联合惩罚(如罢课、罢工等),或建立工会、消费者协会等联合组织以对强势方施加惩罚威胁来保障自身利益。在弱势方的集体行动中,又存在着搭便车导致的合作困境问题。第三,多对多合约。
多对多合约涉及人类交往的各种活动(如竞争市场的交易合约),理想的情况下合约规则简化为价格信息。而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市场并不存在,以上涉及的各种阻碍合作实现的问题在垄断竞争的情况下同样存在,并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合作问题。具有相同市场地位的一方参与者中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协调,他们的合作常常构成对市场另一方参与者利益的伤害。市场的复杂性使得参与者本身很难自我发展出对各方都公允的制度规则并自我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独立地位的第三方存在,根本无法保证所有合约得到执行。而现实的情况是,第三方除了及时的惩罚违约行为,常常还需担当制定规则的角色。
尽管Hamilton(1964)的亲缘选择、Trivers(1971)的直接互惠、Alexander(1987)的间接互惠等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类的合作行为,但是在以上各种合约的执行中,由于囚徒困境、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惩罚威胁,合约规则很可能会形同虚设。惩罚可能是人类维持社会合作秩序的主要机制,Gchter等[9]认为,惩罚行为的存在可以有效确立社会合作秩序。而对于自发的同辈惩罚,Boyd等[10]发现,只在群体的规模足够小或个体有不合作的选择权利[11-12]等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原因在于当群体规模很大且成员之间互动交往很少时,惩罚的未来收益不能被内化,因而第三方强制性的实施机制是任何规则都能够得以实施的基本前提,这呼唤制度性惩罚的介入。
三、惩罚与制度性惩罚
1.惩罚与人类合作秩序的维持
人类是自然界独一无二的能与陌生群体在大规模情况下合作的物种,对合作演化之谜探索的大量证据表明,人类通过惩罚执行社会规范的能力是其中的关键机制。人类维护合作秩序的手段主要包括奖励、惩罚和驱逐(驱逐本质上也是一种暗含的惩罚)。Szolnoki和Perc[13]发现,以正面奖赏激励遵守规则的现象在人类社会十分少见,而惩罚却无处不在。这可能源于人类社会的成员大多更倾向于遵守群体规范而不是违反,因而惩罚就成为一种威胁少数行为不端个体的手段。而对所有遵守行为的个体都进行奖励会复杂的多,因而逐渐演变成当今的约束性法律制度,而不是大规模的奖励制度。
在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文献中,惩罚常被认为是由他人执行的为当事人所厌恶的事件。Spitzer等[14]发现,对规范的遵守不仅来自合作和公平交易带来的直接利益,还依赖于对背叛不良后果的可信威胁。由于背叛可能会遭受严厉的惩罚,使得背叛的成本大于合作的成本,因而使得合作而不是背叛成为理性的选择策略。Brock和Parker[15]发现,在动物界中也广泛存在着惩罚行为(如确立支配关系、阻止寄生和欺骗行为、调教后代和配偶,以及维持合作行为等),因而惩罚行为可能是一种生物进化来的本能。Fehr和Gchter(2002)、Camerer和Fehr(2006)、Nakamaru和Iwasa(2006)、Herrmann 等(2008)的大量实验以及Boehm(1993)和Henrich(2004)等的人类学证据表明,许多人愿意自己承担成本去惩罚背叛者,甚至在一次性交往情况下也是如此。从人类进化的行为学角度看,惩罚是人类保证合作的重要条件,这种机制在人类的长期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已内化在人性之中,因而Fowler(2005)、Boyd和Richerson(1992)等认为,赏善罚恶是人的内在需要和合作的前提。
但是惩罚需要付出成本从而使惩罚者的适应性降低,于是在Fowler[12]等看来,纯粹合作者相对于惩罚性合作者来说就是二阶搭便车者。由于惩罚者相对于二阶搭便车者来说需要担负额外成本必然在进化中丧失优势而消亡,则减少个人适应性的惩罚行为如何能通过自然选择得以进化?Gintis[16]提出强互惠者的角色,认为强互惠者虽然自身背负一定的成本,但是他们的利他行为提高了所在群体成员的适应度。在Bowles和Gintis(2003—2004)、Boyd等(2003)、Gintis(2000)、Henrich和Boyd(2001)等几乎所有相关的合作演化模型中,合作都是以自身背负成本而通过降低群体灭绝几率等机制为群体所有成员带来收益。但是这些模型均假设惩罚者能够低成本对背叛者实施严厉惩罚,即惩罚者付出的成本要小于惩罚对背叛者造成的伤害。由此,一个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索的问题将是:社会如何保证惩罚者能以低成本对背叛者进行严厉的惩罚?本文认为,正是人类发展出以制度性惩罚为主体的社会机制才保证规范的普遍得以执行。
2.第三方惩罚与制度性惩罚
上文所提到的合作演化模型中的惩罚行为一般是指第二方惩罚,即“你伤害我,我惩罚你”。然而现代大规模的社会稳定依赖于公正的第三方,即不受到违反规范本身影响并从惩罚中没有直接受益的公正的决策者,其通过惩罚执行道德规范的能力和意愿。能够以独立第三方身份执行惩罚的能力可能是人类合作规范得以稳定运作的独特机制。以黑猩猩为例,虽然其广泛表现出第二方惩罚,但是并不会对违反规范的同种个体进行第三方惩罚,而Reidl等[17]发现一个3岁的儿童就会对第三方的规范违反反应强烈。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个体会承担成本以惩罚那些违反公平和分配规范的个体,即使惩罚者本身与之无关。这些证据表明,第三方的规范执行可能是独特的人类行为并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已出现。这可能是支持以第三方惩罚制度的演化作为人类稳定的合作规范得以发展的重要证据,因而Buckholtz 和Marois[18]认为,人类大规模社会的合作秩序依赖于公正的第三方执行惩罚的能力。
Henrich等[19]和Greif等[20]发现,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为了提高惩罚的效力,群体趋向形成自我管理的机制,惩罚背叛者的权力被赋予特定的权威集中者。如Gibson和Marks[21]发现,传统社会的村民会请求他们的首领来调节争端;Greif[22]发现,中世纪欧洲的商人创立了工会来维持商业秩序。惩罚基金可被看做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雏形,如Ostrom[23]描述了许多小规模社会自筹资金保证合约执行的例子(如雇佣一个执法者)。Guth等[24]认为,由于集权化的制度可以更有效地克服协调问题和二阶搭便车问题,且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比同辈惩罚更有效率,因而将这种基于集权化制度的惩罚称为制度性惩罚。制度性惩罚在人类社会中实际担当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责任。Sigmund等[25]的模型显示,人们会自发地采取自我管理的制度来监督对合作的贡献和惩罚搭便车者。在复杂的大规模社会,集权化的惩罚和法定权威对维持社会的合作秩序更有意义,且作为权威的监督者扮演重要角色。
在现代人类社会,规范的执行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对于维护法律规范,主要是通过违法行为得到法律和社会的正式的惩罚而实现。第二,社会规范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为法律规范提供支撑,是通过在本地社区成员之间自发的监督和控制得以执行的。以执行法律规范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制即制度性惩罚,制度性惩罚的主体是以国家权力作为强制力的一套制度体系,由国家管理的公平公正的第三方决策者来充当裁判者,其在执法中不涉及个人利益。Darley[26]提出,在当代主要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决策方主要包括陪审团和法官,他们负责对证据做出评估,判定有罪还是无罪并做出惩罚判决,在理想的情况下应与民众对规范违法严重程度的直觉一致。
从社会实施的目的角度来看,制度性惩罚的正当性有两种观点:第一,个体以社会规范不允许的方式做出违反规范的行为而对社会造成了损害,正义的天平就失去平衡,对违法者的惩罚会恢复平衡。在这一观点下,违法者理应得到与他过去所犯错误相应的惩罚(罪有应得理论),这一理论主要为Kant(1952)所倡导。第二,惩罚被用于阻止未来违规行为的发生(功利主义或结果主义),如Butterfield等[27]理学家们认为,惩罚可产生动机以抑制特定的行为,Bentham[28]认为,预防应该是惩罚的首要目的,这是惩罚得以存在的真正理由。惩罚的阻止作用原理是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其通过改变特定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使违规行为不合算,边沁认为,如果行为后果产生的痛苦明显超过产生的快乐和好处,一个人会绝对避免去做。法律角度惩罚目的还包括使罪犯失去进一步伤害的能力或通过惩罚以拯救犯罪者。虽然Carlsmith等[29]的研究表明,“应得”的动机可能是普通人更主要的心理动机,但作为社会实施的目的,惩罚更主要的功能应该用来阻止违规行为的发生,以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
四、制度性惩罚的前提与具体实施
黄少安[30]的论述表明,制度作为人类行为规范已在学界取得较为普遍的共识。North[31]认为,制度由三个基本因素组成,即被社会习惯和习俗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正式约束以及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实施机制的功能在于形成对个体行为的塑造,包括对遵从规则行为的激励和对违反规则行为的惩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就是从实施惩罚的机制上进行区分的,即惩罚是自发的发生还是有组织的发生。惩罚可以由正式的法律制度执行,也可以由非正式的某个组织(如家庭)或个人执行。当人们违反非正式制度的时候,惩罚的机制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而发挥作用的,如同等级的压力、流言蜚语和社会排斥等。韦倩[32]认为,正式制度的惩罚是有组织的,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和后盾,其方式主要包括罚款、法律施加约束、个人对违规者付出货币和时间施加的约束等。
制度性惩罚是保证任何制度得以运行的前提。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国家在现实中承担主要第三方的角色,斯密把这种国家角色描述为“守夜人”。制度性惩罚作为保障和促进合作的手段,并非普遍适用,必须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有效发挥。
1.规则与权利划分明确合理
作为合作的制度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家强调产权界定的重要性。权利界定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而权利划分本身是一种规则,如果权利的划分不合理,难以得到所有合约参与者的认同,那合约的执行力就会大打折扣。按照科斯定理,在零交易成本下,只要产权充分界定,资源就可以得到有效配置。但是现实中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平合理的权利界定有自己的观念认识,Tyler[34]和Darley等[35]发现,当个人感觉到制度给人以公平的对待时,个人更可能自愿遵守法律规范。
规则合理是保证制度实施机制发挥的前提,规则合理的一项重要标准在于得到合约参与者普遍一致的认同。在大规模的人类交往环境下,人们普遍需要公平的制度规则以达到一致认同,公平是基本的制度规则和实施惩罚的前提。人们通过协商或历史实践对于什么是好的制度规范往往可以达成一致,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领域,已经形成共识性的规范体系,这些共识性规范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可以有力他促进合作进行(如产品质量合格、守时守信、不得伤害别人、不可贪污腐败等)。同时,合约规范都是公认而清晰的,对于破坏这类规则的个人,社会需要施加恰当的惩罚,以反向激励对规则的遵守。当权利合理地得到充分界定后,规则需要得到全体参与者的明确理解。现实中由于立法与法律普及的有限性,很多违法者并不知道自身在从事违法活动,受害者也不知道有保护自己的规则,这就要求国家和企业组织在制定规则时一并做好普及传播。
2.第三方权威并且公允
现代国家作为正式制度安排,主要依靠自身权威管理全社会的秩序体系。国家角色要求其本身不受市场行为的影响,在执行中不涉及个人利益,简言之就是要作为公允的第三方对所有的合约可以提供必要的裁决。LaFave[36]认为,在当代的刑事司法体系下,当一个人被确定为犯罪需要无可置疑地证明他从事了一项被禁止的行为(犯罪行为)并且其行为伴随错误的或有罪的意图。Darley[35]认为,施加的惩罚同时受到犯罪意图和造成伤害的严重性的影响,这意味着第三方决策者必须具有如下的认知机制:第一,对犯罪行为和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做出评价。第二,评价犯罪者造成的伤害。第三,整合这些评价并结合法典对惩罚的内在动机做出陈述。第四,在一系列的惩罚方式中做出行动选择。
不论是作为正式制度的第三方,还是非正式制度的第三方,权威性和公允性都是有效实施惩罚的基本前提。第三方需要评估参与方的合约权利责任对违规做出评价,并对违规者做出相应惩罚。如果权威不足,不可能得到被惩罚者的接受,惩罚无从执行。而如果裁决一旦失去公平性,将产生比没有裁决更坏的结果,成为对违规的正向激励,并加重受害者的损失。
3.惩罚的成本收益与具体实施
制度的一项重要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而制度性惩罚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可以及时实施低成本惩罚。惩罚的成本收益分析涉及到惩罚执行者和被惩罚者两个方面。惩罚的首要目的在于提高违规者的违规期望成本并降低违规收益,给合约参与者以威胁,使违规成为不合算的事情。North[31]认为,违规行为是否合算取决于监督的有效性和惩罚的严重程度。违规行为被惩罚的概率乘以惩罚程度构成违规的期望成本,当这一成本高于违规的期望收益时,理性行为者不会选择违规,反之亦然。卿树涛和刘立[37]对腐败问题的分析表明,当一部分腐败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罚或者有逃脱惩罚的可能,短期之内腐败收益远大于腐败成本,就会使政府当局反腐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效。而新家坡独特的严刑峻法在一定程度保证了其制度的有效运转和较高的廉政水平。
韦倩[38]的分析表明,人类是唯一可以以低成本对受罚者施加严厉处罚的物种,但是惩罚仍然是一项成本较高的活动。由于实施惩罚的成本过高,如在Fehr和Rockenbach[39]的一些公共物品的实验中,惩罚所导致合作的增加甚至抵不上惩罚的成本,结果总的最后支付反而下降了。中国文化中有“枪打出头鸟”的说法,敢于挺身而出执行正义者往往得不到什么好处,大家逐渐养成了“让别人出头,有好处共享”的习惯,理性的群体选择最后导致对违规行为的漠视和无可奈何。
众多违法违规行为不能及时得到制止和纠正,主要原因在于惩罚成本的高昂。虽然制度性惩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惩罚的私人成本问题,但是制度执行者仍然面临同样的搭便车问题。North[31]认为,发现违约行为、度量违约程度、找到并处罚违约者都需要付出大量成本。惩罚执行者也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的惩罚行为会牵扯到自身利益,要达到提高违约成本的目的,就必须同时降低惩罚执行者的成本,提高其收益。由于惩罚是一项公共物品,其使群体受益而由小部分的执行者背负成本,因而制度必须为这些惩罚的执行者提供激励,否则执法者犯法情况可能会蔓延进而瓦解根本的制度体系。由于二次搭便车者的收益大于惩罚者,故必须给予惩罚者以额外补偿,使他们的收益等于甚至超过搭便车者。在国家的层面,缪尔达尔[40]主张,如果不能对公平惩罚的实施施加有效的激励会导致“软政权”现象,使所有规则成为软约束,是否执行取决于当权者的成本计算,而不是是否违反规则,这些都使惩罚走向反合作的方向。
提高违规成本的渠道有如下两种:第一,提高监督水平,使违规及时得到发现,给予处罚。第二,加重处罚的力度。一般来说,虽然惩罚执行者需要权威的第三方,但比较起参与方自发的监督,第三方监督往往是较低效率的。韦倩[38]总结了增强惩罚能力的三种社会机制,包括规范的内化、缔结同盟与第三方介入,但是并没有给出在具体的社会中有效实施的方法。落实到具体的实施,最有效的手段在于加重惩罚的力度并提高监督举报和惩罚者的收益,特别是在具体制度环境中要提高对参与者监督的激励。目前在制度设计中比较有效的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其指由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赔偿数额,这一制度在英美法系中有长期的成功历史,对此王利明[41]有较系统的论述。惩罚性的赔偿制度安排可以显著改善惩罚者与违规者的成本收益状况,但目前仅适用于法律中特定的领域,如何推广这种机制与普遍地维护规则是各种应用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
五、总结与对策
惩罚不仅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且对于保证制度有效运行,从而促进人类合作繁荣都具有重要作用。虽然人类是绝无仅有的能进行高水平合作的物种,但是由于人的逐利本性,存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社会困境,以及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而会阻碍更全面的合作繁荣。即使人群中存在着利他者和互惠者,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约束,自利者的逐利本性必然导致追求违反合作规则,最终导致合作的崩溃。而惩罚作为一种反向的激励措施,能够对违规行为施加威慑从而阻止其经常性的发生。
在过去极长历史时期内,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特征在于交往的个体之间极为熟悉,交往活动重复频繁,此时,守信守约是大家的理性选择。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经历了剧烈的变迁,由于人口的频繁高速流动,人们的交往范围也得以迅速的扩大,这时大量的合作或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欺诈、卸责和机会主义等就成为合算的行为,这也是社会出现道德诚信危机的深层原因。在小规模的社会模式下,非正式的惩罚机制具有重要作用,而大规模社会更需要正式制度性惩罚施加的强约束来保证规则。Jansson等[42]认为,中国已经从小规模社会向大规模社会结构转变,但目前主要的惩罚机制仍然是非正式的,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制度性惩罚机制的建设,使惩罚满足激励相容并成为“合算”的行为。
参考文献:
[1] Pennisi, E. How did Cooperative Behavior Evolve[J].Science, 2005,309(5731):93.
[2] Griffin, A. S., West, S. A.,Buckling, A.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Pathogenic Bacteria[J]. Nature, 2004, (430):1024-1027.
[3] Nowak, M.A. 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J].Science, 2006,314(5805):1560-1563.
[4] Colman, A.M. The Puzzle of Cooperation[J].Nature, 2006, (440):744-745.
[5] West, S. A.,Mouden,E.C.,Gardner, A. Sixteen Common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in Humans[J].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11,32(4): 231-262.
[6] Hobbes, T. Leviathan[M].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0.
[7]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1968, 162(3859):1243-1248.
[8] Akerlof, G.A.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84(3):488-500.
[9] Gchter, S., Renner, E.,Sefton, M. The Long-Run Benefits of Punishment[J].Science, 2008, 322(5907):1510.
[10] Boyd, R., Gintis, H.,Bowles, S. Coordinated Punishment of Defectors Sustains Cooperation and Can Proliferate when Rare[J].Science, 2010, 328(5978):617-620.
[11] Hauert, C., Traulsen A, Brandt, H., Nowak, M.A., Sigmund, K. Via Freedom to Coercion: The Emergence of Costly Punishment[J].Science, 2007,316(5833): 1905-1907.
[12] Fowler, J.H. Human Cooperation:Second-Order Free-Riding Problem Solved?[J].Nature, 2005, 437(7058):E8.
[13] Szolnoki, A.,Perc, M. Effectiveness of Conditional Punishment for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Cooperation[J].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013, (325):34-41.
[14] Spitzer, M., Fischbacher, U., Herrnberger, B., Gron, G.,Fehr, E. The Neural Signature of Social Norm Compliance[J].Neuron, 2007, 56(1):185-196.
[15] Brock, C.T.H., Parker, G.A. Punishment in Animal Societies[J].Nature, 1995, (373):209-216.
[16] Gintis, H. Strong Reciprocity and Human Sociality[J].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000, 206(2):169-179.
[17] Riedl, K., Jensen, K., Call, J., Tomasello, M. No Third-Party Punishment in Chimpanzee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 109(37):14824-14829.
[18] Buckholtz, J.W., Marois, R. The Roots of Modern Justice: Cognitive ad Neur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Norms and Their Enforcement[J].Nature Neuroscience, 2012,15(5): 655.
[19] Henrich, J.,Ensminger,J.,McElreath R., et al. Markets, Religion, Community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Fairness and Punishment[J].Science, 2010,327(5972):1480-1484.
[20] Greif, A., Milgrom, P.,Weingast, B.R. Coordination, Commitment, and Enforcement: The Case of the Merchant Guild[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4):745-776.
[21] Gibson, C. C., Marks,S. A. Transforming Rural Hunters into Conservationists: An Assessment of Community-Based Wildlife Management Programs in Africa[J]. World Development, 1995, 23(6):941-957.
[22] Greif, A.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The Magrhibi Traders Coali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83(3):525-548.
[23]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4] Guth, W., Levati, M.V., Sutter, M., Heijden, E.V.D.Leading by Example with and without Exclusion Power in Voluntary Contribution Experiment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91(5-6):1023-1042.
[25] Sigmund, K., Silva, H.D., Traulsen, A., Hauert, C. Social Learning Promotes Institutions for Governing the Commons[J]. Nature, 2010, (466):861-863.
[26] Darley, J.M. Morality in The Law: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itizens Desires to Punish Transgressions[J].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2009, (5):1-23.
[27] Butterfield, K. D., Trevino, L. K., Ball, G. A. Punishment from the Manager’s Perspective: A Grounded Investigation and Inductive Model[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7,39(6):1479-1512.
[28] Bentham, J. Principles of Penal Law[M].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2. 396.
[29] Carlsmith, K.M., Darley, J.M.,Robinson, P.H. Why do We Punish? Deterrence and Just Deserts as Motives for Punishmen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2002, 83(2):284-299.
[30] 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31]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2] 韦倩.影响群体合作的因素:实验和田野调查的最新证据[J].经济学家,2009,(11):60-68.
[33] North, D.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 Norton, 1981.
[34] Tyler, T. Why People Obey the Law[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5] Darley, J. M., Carlsmith, K. M., Robinson, P. H. The Exante Fun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J]. Law and Society Review, 2001, 35(1):701-726.
[36] LaFave, W.R. Criminal Law[M]. Ontario:West Publishing Corperation,2003.
[37] 卿树涛,刘立.腐败与反腐败理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经济评论,2004,(6):19-25.
[38] 韦倩.增强惩罚能力的若干社会机制与群体合作秩序的维持[J].经济研究,2009,(10):133-143.
[39] Fehr, E., Rockenbach, B. Detrimental Effects of Sanctions on Human Altruism[J].Nature, 2003,(422):137-140.
[40]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41] 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122.
[42] Jansson, H., Johanson, M., Ramstrm, J.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 Network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Russian, and West European Market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7, 36(7):955-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