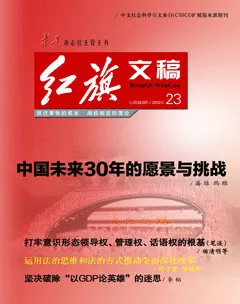“李鸿忠:改革要向不作为风气开刀”等8则
2013-12-29
李鸿忠:改革要向不作为风气开刀
凡是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市场经济往往发展得比较缓慢。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上升到“决定性”,体现了党对市场经济规律的遵循,是中央对市场作用的新定位。现在很多领导干部在面对市场这只“手”时很不习惯,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怪。这类干部习惯于当官做老爷,习惯于“别人求我办事”,把手中的权力当作包治百病的“神药”。今后,我们要坚决向这种不良风气开刀,进一步强化市场意识、服务意识,自觉运用市场规律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首先要破除本位主义风气。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一些原本可以下放或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有些部门为了本部门利益,以种种借口拖着不放或者“分期下放”;在机构改革中,有些部门担心削弱了自身地位,不愿改甚至反对改。这些都是本位主义的表现,深化改革,局部必须服从全局。其次要破除机会主义风气。这里所说的“机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而是指不愿付出改革成本,只希望他人承担改革成本,自己坐享其成“搭便车”的投机取巧风气 “搭便车”的行为,这种行为将延长本轮改革的时间,错过最佳改革时机,增加改革成本。最后要破除不作为风气。这些不良风气是影响改革的负能量,是推进改革的绊脚石。面对新一轮改革的繁重任务,消极等待、被动应付没有出路。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置身其中,勇当改革践行者、推动者。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日)
林毅夫:经济转型离不开有为政府
有为的政府,对于转型国家尤为重要。这是由于,转型国家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需要政府来促进就业、关注民生、稳定社会。资金、资源如何避免盲目性,制度如何完善,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支持。所以,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甩手不管,更不会自然而然形成市场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推行的就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比如双轨制,既让市场发挥作用,也让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完善上层建筑,这也正是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5倍的关键性因素。往前看,要应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解决好一些领域的垄断、寻租甚至腐败,既要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消除各种扭曲市场的保护、补贴、行政垄断,另一方面要依靠有形之手,因势利导,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环境,解决外部性等改革开放中累积的矛盾。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6日)
张砥:让群众看到改革的好处就能凝聚共识
共识是改革向前的推进器,改革的好处则是凝聚共识的共鸣点。近些年来,人们对改革的期盼空前高涨,各种讨论和争论层出不穷,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但往往都是各陈己见、交锋激辩,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不可否认,今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达成共识难度不小,统筹兼顾更为不易。但越是这样,就越需要拨云见日,从多元多样多变的环境中寻找最大公约数,越需要把庞杂的民意诉求最大程度转化为广泛共识。改革开放35年的成功实践离不开这一点,如今全面深化改革仍要坚持这一点。改革的好处要让群众看得到,更能摸得着。正所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改革只有尊重人民、为了人民,才有可能最大范围地凝聚行动共识。
(来源:《北京日报》2013年11月22日)
陈述:改革没有“顺风车”
今天的改革已处于深水区攻坚期,面临的是难啃的骨头、难闯的险滩。情况更加复杂,挑战更为艰巨,人们的期待更高,支付的成本也更大。过去建一个工厂带动就业、增加税收,各方欢欣鼓舞,现在则要面对种种质疑;“三公经费”公开、异地高考推进、金融改革提速等改革举措,一经推出,每每引来舆论挑剔。“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每个人都渴望改革、呼唤改革,然而,改革一旦动了自己的“奶酪”,哪怕只是一丁点儿“奶酪”,立马不肯改、不许改,有的还站到改革的对立面,阻挠甚至反对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既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单兵突进,而需要统筹部署、协同推进。改革没有不劳而获的“顺风车”可搭。人人都是参与者,个个都是当事人。在历史的大潮面前,当看客没有出息,搭“顺风车”没有出路。只有投身改革、率先改革,抓住机遇、认准方向,大胆探索、稳扎稳打,全社会才能在改革中进步,个人才能在社会进步中得到更大的收益。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5日)
王国刚:以回归实体经济为牵引完善金融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弊端屡屡受到社会各界的诟病,如融资难、金融产品少、设立金融机构门槛高和金融服务质量差,等等。究其主要成因在于,对实体经济部门而言,实行的是一种外部植入型的金融体系,由此形成了金融机构的卖方垄断格局。这种外植型金融体系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存贷款市场中卖方垄断。由此,在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缺乏与商业银行竞争能力的条件下,存贷款利率就难以由市场机制决定。第二,将原本多维一体的有机经济活动,人为地分切为若干相互缺乏关联的部门活动,使得各种资源的整体关系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不仅降低了实体经济部门的运作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而且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本不应有的风险。第三,金融机构为自身服务的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脱离于实体经济的状况逐渐加重。货币市场成为金融机构彼此间进行短期资金和短期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也只能是金融机构彼此之间的游戏。要改革外植性金融体系,就必须让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回归”的含义在于,扩大实体经济部门中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各自的金融选择权,把本属于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的金融权力归还给实体经济部门,推进内生性金融的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2日)
高书生:特殊管理股制度成为意识形态管理的一大创举
文化体制改革10年,大量的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已转制为企业,民营文化企业不断增加,使宏观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主要是文化事业单位,现在主要是文化企业。受习惯性思维影响,过去总是以为文化企业不好管理,只有文化事业单位才可靠。与这一认识相关联,常常会把市场和资本、导向对立起来看。不同于工商企业,文化企业是创作生产精神产品的,是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这一特殊性要求文化企业必须自觉地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决定》提出特殊管理股制度,在文化企业内容生产上加了“一把锁”,为在特定问题上行使“一票否决权”提供了制度保证,是意识形态管理的一大创举,必将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一大步。从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看,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底线。当前要进一步调动文化企业的积极性,使其在内容导向上切实负起责任,实现特殊管理股制度,有利于文化企业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在内容把关上强化自律,最终形成宏观管理微观化,党委、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5日)
杨运忠:体制编制是我军改革重头戏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我军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发展方向,由此拉开我军新一轮改革大幕。目前我军体制编制问题已成制约战斗力生成的最大瓶颈,它与信息化战争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战,军兵种和大的作战单元之间没有联为一体;机构庞大,作战部队比例偏少;层次繁多,职能重叠,军事效能的发挥受到较大牵制。深化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涵盖三大任务,即革旧、建新、优化。革旧就是改革和摒弃陈旧过时的体制编制。建新就是建构与打赢信息化战争和应对安全威胁相适应的体制编制。优化就是调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重点是解决机构臃肿、头重脚轻、作战部队比例偏小的问题,形成科学合理的力量配置。
(来源:《环球时报》2013年11月25日)
[美]李世默:“中国崩溃论”和“和平演变论”都错了
从奥巴马将亚太经合组织系列会议上的风头让给了习近平,到疯狂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治经济风向,中国这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常常成为西方政治讨论的焦点。不幸的是,这种讨论常常建立在错误的框架基础上。有关中国的西方主流观点一直由两种政策理论所主导。一是“中国即将崩溃论”,二730a9bd5f7fed460d3ccec60a6dbe76e72ec84b2ed20991bed55914f021f9f57是“和平演变论”。在有关当代中国重新崛起为大国的这两种观点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学术和政策界已经观察实践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结果成绩单并不漂亮。先说“即将崩溃论”,几十年来,冷战分子们不得不把他们的预言有效期不断地往后推。看起来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阻止现代化,而是在领导现代化。最新的成果是,它成功实行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高度复杂转变——在这一点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还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最大数量的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最显著的提高。再说“和平演变论”,在共产党实行大幅改革的过程中,这个国家保持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做到的国家独立程度。其一党体制没有受到影响,党的制度日趋成熟和加强。冷战之后,很多人羡慕西方的物质成功,并不管自己的文化根基和历史背景,照抄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今,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了选举制度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都还陷于贫困和内战之中。而在发达国家,政治瘫痪和经济停滞成了常态。即便是最天真的中国和平演变论者也不可能再相信中国会效仿这些“光辉”的范例。
(来源:《参考消息》2013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