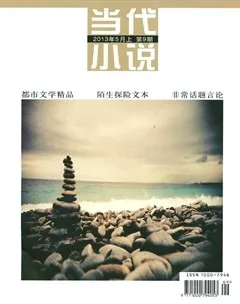喝酒
2013-12-29陈再见
有一次,金枪在酒桌上说:“不瞒你们,潘红霞是个处女……”金枪边说边晃着他的杯子,杯子里装的是53度茅台。如果金枪喝的是红酒,就有意思了。可惜他从不喝红酒,他说那是女人才喝的酒,更不喝啤的,说那是尿,连翻起来的泡沫都像,他就喝白酒,高度白酒。喝完之后,可以想象,每次都会像那次一样,说起他众多的女友。
潘红霞是金枪早年的恋人,关于她是处女的说法,我是第一次听说,自然倍觉兴奋。那晚我把妻子折腾来折腾去,妻子显然烦了。后来我也烦了,我的大脑突然就控制不了我那两片薄唇,我没头没脑的,就说出了一句:“你要是和潘红霞一样是个处女就好了。”
自觉失言,不敢再说二话。妻子问我说什么。我说没什么我说什么了吗。尽管如此,妻子还是一脚送给了我一张大床——冷冰冰的地板。
关于我的妻子嫁给我的时候是不是处女这个问题,我一直心存侥幸。妻子在我之前有过男朋友,这在我那个朋友圈子里谁都知道,且那个男的曾经也是我的朋友。热恋时,我问过妻子:“你和他睡过吗?”妻子倒也坦诚,说睡过。可她一坦诚,我就觉出她是在故意打击我。那时我还年轻,刚混进报社,躲躲闪闪,可不敢像金枪那样在办公室就干起来。我们的初夜在一个古旧的宾馆,颇有《花样年华》的味道,半途我想爬起来看个究竟,紧要关头却停电了,至于那次见没见红,就无从考究了。我倒相信是见了的,尽管金枪一直无情地打击我:“不可能,她和他的事,我还不清楚。”金枪那时不知道我们后来会结婚,否则也不会说那种没脑袋的话。而我,也得出一教训:千万不要在一群玩得忘乎所以的朋友堆里挑出一个当你的妻子,即使她真的是个处女,和天使没两样,最好也不要。
结婚后,妻子深居简出,当起了贤妻良母,且开始抗拒我和之前那帮朋友们来往,尤其是金枪,说金枪不三不四,是个酒鬼、色狼,总之一句话:不是好人。我说城管办出来的哪一个是好人呐,把他和好人对比你算是抬举他了,你应该说他不是坏人,是条恶魔,比坏人还可怕……这话看似调侃,事实也是心里话。有一次我和金枪在会所松骨,酒后不得不的舒坦,我们弄了个隔壁房,缘分好得无须解释。中途隔壁房那女的突然大喊大叫,如遭杀害,“神经病!”那女的哭着逃出了房间。尽管妻子不喜欢,我还是和金枪保持着来往,且关系越来越密切。当然,金枪从不主动往我家跑,而我也从不在家里提起金枪,至于我们干过的“一起嫖过娼”的属于好兄弟范畴的事情那更是守口如瓶,睡梦中都得时刻惦记,以免走漏风声。男人也就这么点本事,在妻子面前。当然,我和金枪也不纯粹是酒桌前后那么点事,别看我们晚上面目模糊,大白天,西装革履混在办公室里,还是有模有样的。金枪早在政府大楼里混得如鱼得水,是条人精,有些事我办不了,找谁都办不了,只能找金枪。去年,妻子的小侄女余小淘大学刚毕业就进了社区办公室当文秘,靠得不就是金枪的关系。金枪不止一次跟我说:“你那小侄女长得真好看,那……”我立马叫他闭嘴。金枪大笑:“开玩笑开玩笑。”可我不相信金枪是开玩笑,老实说,他就是一大色狼,且是有权又有钱的资深色狼,看谁都一眼暧昧,只要对方是个母的。我想余小淘迟早有一天会让金枪得逞,反过来想,那也不一定是个坏事,且不说金枪这人有太多利用价值,我也不能肯定现在的女生有多么纯真,说不定人家就愿意。事情就是这样让人揪心。我又何必忧愁?为这操蛋一样的现实。
金枪叫喝酒,听金枪说女人,才让我感觉一天没有白虚度。
金枪说,他对女人的爱是天生的,那种像是母性一样的情怀,在他那里像是瓶子装满了水一样汩汩作响。
“你听,它们又在汩汩响了……”说着金枪放下酒杯,转头看着远处走过来的女孩,“我看见心爱的女孩总是想着上去抱一抱她们,也不全是要和她们做爱,不管你信不信,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想爱她们,我喜欢她们,我要帮助她们,保护她们,当然,这样子一来,我和她们是必须得做爱的,我喜欢这样,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这样的,你明白吗?或者说你信不信……”我听着,在他对面笑而不语。金枪和我说这些时,我们都是在酒桌上喝酒,离开了酒桌,我们只谈工作和交易,也只有在酒桌上,我们才会说说心里话。我相信金枪在酒桌上的话都是真话。从这点看,和金枪喝酒,其实就是听金枪说真话。我和金枪的感情还真不是一般的交情,我们九十年代初就认识了,那时彼此什么都不是,整天在大街上闲逛,大热天的,跑商场里吹空调,还得担心被商场里的保安识破,赶我们出来。那时金枪也爱喝酒,但没钱喝。那时金枪还对女人不是那么关心,他一心想赚钱,想要成为一个有钱人。他说在深圳没钱就是一条狗,不,连狗都不如。
照金枪的说法,想要有钱,一是做生意,像犹太人那样有头脑;二是抢银行,像史泰龙那样有小山一样的肌肉;三就是混进政府大楼,像李白那样千杯不醉,还得像马尾巴一样能准确地拍到马屁股上。这是金枪年轻时候的言论,那时我们那些朋友只当它是玩笑话,时隔多年,回想起来,惊为圣言。当年玩在一起的那些人,如今是找不齐了,凡是能叫到一起的,也都混得不错。通常是在晚上,几个电话一打,“干嘛呢?”“金枪叫喝酒啊。”大家都乐意见到金枪,也喜欢听他高谈阔论,一场酒喝下来,准是金枪用话语包场。金枪有一些妙论,颇得朋友们的赏识,有时我也不得不佩服,有一次一个朋友说起有人向他借钱,还不还。金枪马上说:“我倒喜欢有人借了钱不还,不就几千块,当给了,要是及时还了,我还得提防着他再借,再借就几十万了,又不能不借了,人家有借有还啊,多讲诚信。”金枪这么一说,在理,大伙纷纷称是。金枪便以智者自居了。
妻子一连几天不理我,也一连几天不让我上床睡觉,叫我找潘红霞睡去。我只好在书房里临时搭了个铺位,睡了几夜,一晚被冻醒好几次。半夜三更,爬起来抽烟,心里有气,却不是气妻子,而是气金枪,他就不该提潘红霞是处女的事。我故意打金枪的手机,想把他也从被窝里拽起来,不能让他太舒服。如果金枪和我一样有妻室,我大概不会这么残忍,好在他早就离婚了,女儿在国外读书,他那大得出奇的家里,就住着他一个人。电话通了,我劈头就骂:“你妈的,我被你害惨了。”听我说了事情的缘由,金枪笑个不停,他说兄弟对不住,我又不能叫你来我家睡,我身边还躺着人呢!我一听,火冒三丈,好家伙,他躺在被窝里不说,还躺在女人的怀里。可是金枪立马把电话挂了,我再打,已经关了机。
要说潘红霞是个陌生女孩,妻子大概不至于这么小气,问题是潘红霞和我妻子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俗称闺蜜,两人有过一段时间形影不离,在我们那个朋友圈子里出了名的团结。她们的好却是短暂的,很快便因一些扯不清楚的缘由而分开了,分开也不是说闹翻,只是不怎么说话,不怎么来往,但见了面了,还是会叽叽喳喳说个不休的,很好似的,背后又说对方的不是。我便极为佩服女人这点素质。我和妻子好上之前,说实话我的暗恋对象是潘红霞。潘红霞是个美人,她肉乎乎的,每次见面都让我浮想联翩,甚至和她稍一接近就发生了勃起,对此我很害怕——那时我乳臭未干,容易大惊小怪。
我喜欢潘红霞,却不敢说,不但不敢和潘红霞说,连金枪他们也不敢说,怕他们笑话我。没过多久,金枪和潘红霞好上了,出双入对,挺般配,这事对我打击极大,几近想着和金枪断交,想想又不能怪金枪,要怪也应该怪潘红霞,似乎也不能怪她,该怪的还是怪自己。或许是出于报复,报复说不上,主要还是因为挫败后的空虚,妻子刚和她的前男友分手,我便积极顶了上去。此后见面,金枪带着潘红霞,我带着妻子,像是家庭聚会了。
我们四人还结伴去过海南,看天涯海角。我那时想着我们就这样定局了,一人一个女人,这辈子算是这样了,然后结婚生子,执子之手,与子同老。事后证明金枪没我天真,没过多久,他就把潘红霞甩了。潘红霞为他怀过孩子,他坚持要与潘红霞分手,她只好哭着去医院流产,还是我带着她去的,作为金枪的哥们算是尽职尽责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走到了头,或者说是金枪已经把潘红霞玩腻了——他就这样,喜新厌旧。我却因此而暗自兴奋,我亲眼看着潘红霞落泪,便忍不住想上去抱着她。可我不敢。我真后悔和妻子好上,我却使不出金枪那样的手段。
……后来,听说潘红霞出了国,嫁了一个胸口长毛的老外,金枪为此还耿耿于怀,说真是可惜了,让外国人捡了便宜。金枪几近无耻了。几年前又听一个朋友说,潘红霞回国了,好像离了婚,只是我们没再见到她。这么多年过去了,经过国外雨露的洗礼,我在想潘红霞会有很大的改变,即使是见面了,也不一定能一眼认出她来。有时喝了酒,头昏脑涨的,开着车在街上走,偶见路边站着一个丰腴性感的女孩,我都会误以为是潘红霞。我想着要是在街上遇到潘红霞,我该说些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什么都不想,就想在潘红霞面前骂一句金枪他妈的是个混蛋;有时在休闲会所,我也不止一次把身下的女人唤作红霞。我说红霞啊,金枪他妈的真是个混蛋,你跟他睡觉时,你还是个处女,你屁股下面垫着的几层报纸都湿了,都是血——可他最后还是不要你了,不但不要你了,他现在把女人弄一次就不要了,就当你们女人是一次性的筷子,而他只是来吃个快餐的,吃完,筷子也就顺手扔了,他真是个混蛋……
更多时候,我还是清醒的,虽然也喝了不少酒。莫名其妙的,我会给会所里的女人背篇古文——我喜欢背古文,好多古文都能倒背如流,报社里的人说我是社里的才子——我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溟溟,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我如入忘我之境地,会所里的女人大概没见过我这样的顾客,她以为我醉了,便转过身子去看电视,手里拿着遥控器,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地转换着,没有一个节目合意,不厌其烦,事实上她一点耐心也没有,她比我还要浮躁,还急不可耐,虽然,表面上看,她这种女人比谁都清闲——我忍不住会想象她们白天的生活,她们应该也爱逛街,爱逛商城,跟余小淘差不多的年龄、差不多的心态和爱好。如果我晚上和她睡了,白天在大街上遇到,我们还是陌生人,谁也不敢相信就那么一点钱,就能把一对陌生的男女弄到同一张床上,比恋人还要熟悉和忘记羞耻。城市却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传奇。
我也会和她们聊几句。我给其中一个姑娘讲过一个故事,故事也是在酒桌上听金枪的,我说的时候却把它当亲身经历了。我问:“你为什么干这行啊?”问这话时,我的手一直活动在她的胸部。她笑着回答:“为了赚钱呗。”语气坦诚、爽快,是一个久经场面的女孩。我说:“给你说个故事,哦,不是故事,是真事,有一年,我回老家过年,一个当年的小学同学来家里找我,提着一只老母鸡,一看就有求于我。你猜猜,他求我什么事?”她说:“找你借钱。”“不是。”“叫你介绍工作。”“不是。”“那是什么,猜不出,你说嘛。”我说:“他找我,说,听说城里女人卖淫很能赚钱,你能带我妻子出去卖淫吗?”“不会吧,你骗人。”“骗你小狗。”可很快,她就不言语了,很长时间的不言语,我怀疑她已经哭了,偷偷在哭。也许我伤到她了,或许我高估了自己,像她那种女人,什么风浪没见过,什么狠话没听过,她们的内心比谁都强大——她们说,老娘赚个三五年,腰缠万贯,出去动个小手术,还是处女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嫁不到。
星期天,余小淘过来做客,吃饭。余小淘这小女孩挺懂事,也是因为我帮她托金枪弄关系进了社区办公室,每到周末,必定来家里呆一午,来了也不空手,带着菜和礼品,菜是附近的商场买的,多次这样,以至于妻子在周末这天都不用上商场,就等着小侄女来;礼品则多种多样了,有时是送给我家小孩玩具,有时是给她姑姑买的化妆品等等。妻子越来越喜欢她的这个小侄女。我自然也喜欢,我觉得她一天天在成长,已经不是刚毕业出来那时候的模样了,她高挑的身材,搽了淡粉的脸蛋,一点都不减潘红霞当年的风姿。这样想着时,我吓一跳,我怎么就把余小淘和潘红霞联系上了呢。
余小淘的到来,让我家持续几天的冷战气氛有了好转。妻子总不能在小侄女面前流露出在生我的气,生气总得有个理由,如果余小淘问及,作为女人家里长家里短总得说几句,妻子总不能说我们之间是因为做爱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你要是和潘红霞一样是个处女就好了”的话而冷战几天吧。妻子已经几天没说话了,平时嘴巴就碎的她都快憋死了,所以余小淘的到来,让她如水中抓到稻草,嘻嘻哈哈的,两人在厨房里说个没完。中间还故意对我说:你啊,别顾着等吃,把报纸收拾一下吧,人家看报纸翻着来,你看一张就撒一张……我忙说遵命。余小淘呵呵笑着,说姑丈你真有意思,连看报纸都和金枪叔一样。
显然,这话让我们三人都吓一跳。
找金枪帮忙的事我是交代过余小淘的,不能告诉她姑姑,也就是说她得假装不知道有金枪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否则妻子就知道了我仍和金枪关系密切,还找他帮忙,存在交易现实。再说妻子连我和金枪交往都反对,万一小侄女也和金枪有了往来,那不就更危险,羊入虎口了都。妻子后者的想法,我也颇有同感。我真不愿意让余小淘和金枪有来往,这小姑娘的美丽、可爱,别说是金枪会心动,我这个做姑丈的也难免动些颇具罪恶感的想象。
余小淘意识到说漏了嘴,她看着我,垂下眼睑,脸唰的就浮起了红晕。妻子问余小淘怎么认识金枪。没等余小淘回答,我便插嘴说:“嗨,人家政府大楼里的领导,社区办公室怎么会不知道呢?”余小淘忙说:“是啊,早就听说,他来我们办公室找过人,坐沙发上撒了一沙发的报纸。”
演得还算默契,显然也是拙劣的,好在妻子心情大好,没再追问。她或许不愿过多提起金枪。不但是我的妻子不愿多提起,朋友们的妻子也不愿意,她们都不喜欢自家的男人跟金枪走得近,都把金枪当成了危险人物,所谓近墨者黑,一不小心就被带坏了。然而她们的抗拒也是徒劳的,金枪一圈电话打下来,她们的男人就会以各种借口逃出家门,聚在了金枪的酒桌上,听他慷慨激昂,听他说起不同的女人,听他阐述人生的奇论妙理……最后脚步蹒跚,移步休闲会所,如皇帝选妃……事后都是金枪埋单,金枪单身,财务独立,不必因为花个千儿八百而要向谁解释。金枪也乐意为朋友服务。
金枪的大名就这样常常被妻子们咬在嘴里,都恨不得能咬出血来,吃进肉,吐掉骨头。事情坏就坏在妻子不但没把金枪咬出血来,吃进肉,吐出骨头,反而是自己的小侄女,有入金枪虎口的危险。妻子万没想到这一层。我已经从余小淘的眼神里看出了蹊跷,说起来,是我害了她,把她往金枪的虎口送,这事要让妻子弄清楚了,非扒了我的皮不可。但愿,一切都是我多疑。
我还是做了些工作,包括向余小淘一个办公室的人打听,却没打听出什么来,余小淘的同事们都说余小淘挺乖的,是个好女孩。甚至还跟踪过她,也没跟踪到什么可疑行踪,她下了班就回宿舍楼,偶尔出来,也只是逛商城,或者去麦当劳。她甚至在城市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朋友,更别说圈子了。看着她孤身一人,我暗生怜悯。
然而我已经是她姑姑的丈夫,她开口闭口叫我姑丈,她每叫一下,我的心就往下沉一点。
金枪那,我也留意了一些,有时趁着喝酒,想从他嘴里听出点蛛丝马迹,然而没有。
日子就这么过着,无论有意义没意义,它就F8rjkzr0v6CmtruboxIqVg==这么过着,如一个赶路人频繁交替的两条腿。城市还是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变化,又似乎啥也没变到,一切变化都是假象和掩盖。白天忙忙碌碌的人们,一到夜晚,依然两眼放着青光。一切秘密都隐藏在黑夜的静谧的似乎已经安睡的状态之下。
这一个周末,家里还是发生了一点变化:余小淘没来。妻子等着余小淘来却等不到她,这让妻子很不适应,仿佛这一天没有余小淘她便会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过了。妻子给小侄女打电话,问她怎么啦?得到的回答是病了。妻子要我过去看一下,必要时陪着去医院。当我把车停在宿舍楼下时,余小淘的同事便跟我说:“你找余小淘啊,她好像出去了。”我心想坏了,余小淘撒谎。我问余小淘跟谁没有,那人说不知道是谁,就开一辆黑色丰田。金枪开的便是黑色丰田。上楼一看,果然,余小淘的房间紧锁着,再打余小淘的手机,提示已经关机。我接着拨金枪的手机,也提示关机。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回家,妻子问我余小淘怎么样。我说没啥问题,天气转凉,感冒而已。妻子说这小姑娘啊是时候找个人照顾了。我说是啊不过说不定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我半开玩笑。妻子仿佛不高兴,似乎在怪我乱说话。妻子说余小淘是个乖孩子,在家里一直听她妈妈的话,读书时,班里的男孩子喜欢她,夜里约她看电影,她却躲在屋里学习。妻子还说余小淘要是交男朋友了,第一个肯定就会来告诉姑姑的。我说那是必须的。隔了一会儿,妻子突然问:“你说余小淘将来嫁个什么样的男人好呢?”我说这不该是你操的心吧。妻子瞪了我一眼,自顾着说:“有钱人肯定不行了,有钱人没安全感,当官的也不行,当官的都狠毒,照我看,就嫁个打工仔,哪怕是在工厂里打工,人家生活简单,下了班就回家,从不到外面过夜,一生都不会搞婚外恋,想都不会想……因为他没钱。”“没钱怎么生活啊?”我冷冷地问。妻子就“没钱能不能生活”这个问题与我辩论了起来,她的观点倒是新鲜:没钱的生活也许更像是在生活。但我敢保证,曾经,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争辩,那时妻子的观点却截然相反,那时她把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也许可以认为是妻子的观念在改变,我则更愿意解释为女人的善变与狡猾。妻子当年之所以和前男友分手,原因在我们朋友圈里众所周知,妻子嫌得便是人家的不思进取、安于现状。
我真不想跟妻子说起往事,戳破她的卑鄙嘴脸。我甚至还夸她觉悟高。实际上,我心里在担心余小淘——不知怎么,我是那么的担心着这个小姑娘。事实上,我也不是担心她,如果她和别人相处,我大可放心,管我鸟事,问题是她和金枪好,为什么?偏偏和金枪好,这我就不高兴了。我的脑里总是浮现她娇小的身体被金枪一堆肥肉压在身下的情景。金枪可以把会所的女人都占为己有,可余小淘,他碰不得,我不允许。
这么一想,我突然来了胆子,继续打金枪的手机,还是关机。
仿佛一桩心病,我怎么也放不下。
一连好几个周末,余小淘都不来我家。妻子打了电话询问,余小淘说了不少理由,一会儿是同学来了,一会儿是和同事逛街。妻子向我确定:余小淘一定是交男朋友了。
金枪那里,我还是套不出什么来,估计他早已防了我,故意不提一字。期间我们在一起喝了几次酒,我问他怎么一到周末就关手机。金枪回答得顺畅,一点都不愕然,按他说的,老家有几个远亲戚,非得要他帮忙安排工作。金枪说:“他们想得可真容易,就好像他妈的政府大楼就是我家一样,想叫谁进就叫谁进,要花钱的嘛。”我笑而不语,听得出来金枪的远房亲戚托金枪办事没给钱,或者没钱,金枪这人我还是了解的,没钱,啥事也没门,我开玩笑说你不该叫金枪应该叫金钱。可当初帮余小淘,金枪却没要钱,当时我就纳闷,心里一直疙瘩着。现在想来,金枪早已经打好算盘了的。
好你个金枪,算计到我头上来了,别逼我出狠招。至于什么狠招,鬼才晓得。我只是喝了酒胡思乱想罢了。我是真拿金枪没法子的。
——突然,在一次酒席上,金枪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对我说:你不是想知道吗?你不是一直怀疑我吗?我就告诉你,你妻子的小侄女余小淘是和我好了,我们每个周末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去云南的大理、杭州的西湖、浙江的周庄,我们是一对恋人,夜里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嬉闹、做爱、聊天。满意了吧,啊,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瞒得了你的妻子,你瞒得过我么?你不也跟我一样,想着和你的妻子的小侄女发生点关系,你也想跟她做爱,你肯定这样想过,可能还手淫了,或者把你妻子的脸想象成余小淘的脸,别跟我说你什么都没想过,别跟我说你是一个纯洁的中年男人。哈哈,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余小淘也是一个处女,第一次和我做爱时,她把屁股下面的白色床单染成了红旗一般的颜色,哈哈……没等金枪说完,我抓起一杯酒朝他脸上泼去。奇怪的是,酒结结实实泼在金枪的脸上,却湿了我的脸……
呀——的一声,我坐了起来。我在床上,时间是半夜,窗户没关,外面下起了雨,雨水泼进了房间。妻子问怎么啦。我说没事,做了一个恶梦。妻子说你是不是又喝酒了,一身酒气,真不知道怎么说你。
我没说话,我倒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就是金枪说潘红霞是个处女的那一次。那一次,金枪同样眉飞色舞,侃侃而谈。中途,包厢进来一个服务员,是个中年妇女,中年妇女突然抓起我眼前的酒杯,把酒泼向了正大声说话的金枪,泼了他满脸红酒,如血流满面。当时金枪都蒙了,站起来要打人。我们以为服务员是无意的,便推搡着她出了包厢。服务员看着我,满眼含泪,我定神一看,咦,这妇女怎么看着眼熟?当时稍有醉意,也没多想,进了包厢继续听金枪说潘红霞。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