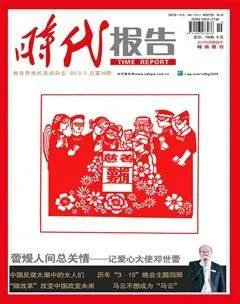朗读者
2013-12-29张亚丽
只要有足够多的“朗读者”,在互联网时代,盲人就能“看”到所有的书。
2012年12月的一天,气温骤降到零下9度。清冷的北京市鼓楼西大街上,一个普通小院的二楼里,30平方米的小屋被分割成4个三到五平米的录音间。或苍老或稚嫩,或平和或急促的朗读声,在每一个隔间里响起。
红丹丹心目图书馆
早上9点钟,一些录音间的门上已经挂上“正在录音”的牌子。拉上厚厚的隔音窗帘,面对录音的电脑,手边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汉语词典,脚畔卧着个小型取暖器,戴上耳机,翻开提前准备好的一本书,“朗读者”刘孟春开始“读书”。
其实,刘孟春也是一个视力障碍者。因为患有先天性白化病,她的视力只有0.1,而且由于畏光,她不能戴眼镜。
刘孟春是“红丹丹心目图书馆”的全职志愿者,这个机构致力于为盲人录制、分享图书。工作之余,刘孟春也会充当朗读者的角色,用微弱的视力,把文字变成声音,为盲人服务。
这段日子,她读的是本意大利童话《电话里的作品》,她把脸紧紧地贴在书上,才能看清那一个个小字。
录音间外,一个狭小的过道,连着一扇通向外面的毛玻璃门。门外,青灰的石瓦屋檐和冬天枯瘦的树枝定格成一幅水墨画,毛玻璃上写着这样的话:留下你永不消失的声音——
楼下,挂着“心目图书馆”门牌的小阅览室里,盲人肖焕义坐在窗前,双手扶着桌前一个固定电话大小的“听书机”,歪着头、凝神接收里面传出的声音。这天,他听的是《北京不向北》,“一本商战小说,名字倒真怪。”阅览室隔壁的小制作间内,几个中学生正戴着耳机听音频,校对录好的有声图书。
时不时,会有人推开阅览室的门进来瞧瞧。肖焕义听着声音就知道是谁,“可可,帮我倒杯水来”,一口京腔。
可可也是“红丹丹心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负责招募朗读者和校对员。
朗读者们并不是专业播音员,难免有丢字落字、读音有误、或读错了句子串了行重读几遍的现象。一本书几百页,朗读者每次读上二三十页,形成一个音频,再由校对志愿者听一遍,标出错误。下回,朗读者录新的章节前,要先对需要校对的部分进行补录,再由其他志愿者进行编辑。
2011年,“红丹丹心目图书馆”正式挂牌并对外招募志愿者。一年多来,有声图书馆对几千位志愿者进行过培训,沉淀下来近百位稳定的志愿者,已经录制、编校和制作完成了130多部Daisy格式有声图书光盘,这种特殊的格式可以使用配套的听书机翻页、点播和加书签。录制的图书中,既有《活着》《京华烟云》《金陵十三钗》等经典小说,也有《不抱怨的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山楂树之恋》等畅销新书,还有播音、法律类的专业教材。
这些全部是由志愿者们抽空完成的有声图书资源。有的志愿者会定期到红丹丹的录音间来录书,还有人在家里完成录制。
读录完一本书,平均需要两到三个月,而对其进行校对和编辑制作,又需要两三个月。
志愿者们被要求,封面、插图、索引、出版信息、页码,明眼人能看到的信息,都要朗读或描述出来。
“我们没有权利决定盲人需要什么,而是应该把我们能提供的都提供出来让他去选择。给盲人主动选择的权利,才是给他们真正的尊严,才能让他们和我们平等分享社会文化产品。”“红丹丹”创办人郑晓洁说出了心目图书馆存在的初衷。
胃口很大的“杂家”
肖焕义五十多岁,你不出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可能压根不知道你的存在。但只要你一搭腔说话,肖焕义能立马神采飞扬地和你聊上。手扶盲杖,两腿撑地,稳稳坐在凳前,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甚至摇头晃脑,活像一个说书人。“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听广播,听评书,特别喜欢历史题材。”
“我从阜成门过来,顺当的时候50分钟,先坐107路公交车到鼓楼,再倒58路。一般周四周五听书,周六听电影。”
“第一次到‘红丹丹’来是2006年9月份,开始有志愿者带,后来我就能自己过来了。”
“那时候是听电影,听过《永远和你在一起》《我的父亲母亲》《小兵张嘎》《宝贝计划》……2006年底我做按摩工作到别的地方去,离得远,就没来了。”
“2011年3月我再来的时候,知道有了有声图书馆。嘿,开始那叫新鲜呐,摸着听书机,熟悉操作。以前我只听过广播小说,人家播什么你听什么,听到关键处还得等下回,慢呐。一本小说,广播里也不全读,有删减,走马观花不过瘾。国家电台的广播,题材也比较偏政治,不轻松……”
2011年6月份,肖焕义“看”完了他的第一本有声图书,《乔冠华与龚澎》,这是他喜欢的近现代历史题材。“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写的,乔冠华后来又娶了章含之嘛……”虽然看不见,多年来肚子里存了不少“谈资”,肖焕义喜欢和人聊天。
“我20多年前从北京盲校毕业,那时候也读了不少盲文书,医学、科学、文学、艺术……”虽然作为盲人只能学按摩做按摩,肖焕义读书的兴趣很广泛,是个胃口很大的知识“杂家”。
自从可以“看”有声图书,肖焕义读过《乔冠华与龚澎》《黄河殇》《解密上甘岭》《尘埃落定》《副县长》《北京不向北》《金陵十三钗》《旗舰》等近十本书,是来这儿最勤快的读者,因此得名“粉丝”。每次一坐在听书机前,他都能静静地聆听几个小时。
八十岁的志愿者
听书时间长了,盲人读者会熟悉一些朗读者的声音。
“《解密上甘岭》《黄河殇》都是石木兰阿姨读的,她虽然有些南方口音,但我能接受。跟年轻人读的不一样,她读得感情很投入,像老年人讲故事,娓娓道来。”肖焕义说。
石木兰是有声图书馆稳定志愿者里最年长的一位朗读者。近八十岁的她仍被一家肿瘤医院返聘为老专家。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九点,石木兰在录音间准时出现,大衣,提包和环保袋挂在椅背上,穿上件背心,打开录音软件,翻开书,接着上次的进度开始读书。一直读到下午一点钟,她存好今天录完的音频,拿出准备好的盒饭或面包,就着保温杯里的茶水吃午饭。吃完正好一点半,她会到楼下办公室登记下今天的进展,和工作人员聊上两句,然后匆匆打车去医院上班。从2011年上半年起至今,除了出差或者有急事,她从不间断到这里朗读。
一年多时间,她已经读完了《旗舰》《京华烟云》《黄河殇》等好几部大部头小说,一部五六百页的小说,每次能读三十来页,读完一本差不多要两三个月时间。因为是广东人,虽然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石木兰说话仍然有些口音,有些字的发音吃不准。在她读过的书上,密密麻麻都是她用铅笔做过的标记,在哪儿断句,一些重点字词的发音,她都会注出来。“你得提前准备好,预读一下。”
石木兰也偏爱历史、传记题材,很对“粉丝”肖焕义的胃口。偶然碰到,他俩会聊上几句。
“我读的有口音,你听不听得惯?” “我就喜欢南腔北调……马一凡(《旗舰》里的人物)说话结巴,您学得可真像。那时候的人都不会拍马逢迎……”
“我正在读的《中国远征军》,你也可以听一听,应该会喜欢。”
“心目图书馆”征集志愿者意见的时候,她专门写了一张A4纸大小的意见和建议:受众对藏书的感受如何?他们希望听些什么书?他们是哪个年龄段的人群?文化程度如何?志愿者不知道,就怕读了没有听众……
49岁的盲人周玲是一个固定的听众,她家里也有部从“红丹丹”借来的听书机。除了不能“看”书,出门买菜、洗衣服做饭,“明眼人能做的事儿我都能做。”她在积水潭医院有份“电话咨询”的工作,每天上班负责接听热线。下午四点半下班后回到家里,烧好开水,做上饭,她一边听书一边等家人回来。吃完晚饭,和儿子老公聊聊天,她会在晚上睡觉前再静静地听会儿书。
听小说《活着》,福贵跌宕起伏的人生让周玲泪流满面,她听了整整一晚上。
与社会相融
学盲文、学游泳、学电脑,每一年,周玲会让自己学一样新东西,这些让她感觉到自己活着。
但她最怀念的还是眼睛看得见的时候,晚上睡前,在台灯下读一本书,是多么惬意的生活。
听完小说《活着》之后,周玲激动地跟丈夫分享自己的感受,丈夫告诉她,这是一本不错的书,拍成的电影还被禁过。而这些话题,原本离她很远。
周玲不止听“心目图书馆”提供的小说,最近,她反复听的是志愿者专门为她录制的《思想道德法律基础》和相关的习题册内容,这是她考心理学自考的第一门课程。
“考自考,主要是想圆自己一个梦,拿不拿学位不重要,得让自己的脑子动一动。”周玲说。
平时的生活里,周玲是家人和朋友的“心理医生”,她经历得多,乐观开朗,总能提供不同的视角。周玲希望能当个心理咨询师,可以接触社会,帮助别人,这是她最大的渴望。
在北京,盲人能参加自考也与红丹丹有一定关系。在“红丹丹”的帮助和社会的呼吁下,2012年,盲人女孩董丽娜参加了自考公共课第一门笔试,北京市自考办自此打开了“盲人自考”的大门。
“中国目前已经有1700万盲人,只有三个大学可以选择,还都是按摩,针推,民乐,调律这几个专业。限制性太强。现在经过努力,自考办为盲人提供了更多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是关键的第一步。”郑晓洁告诉记者。
渴盼细水长流
周玲准备自考的同时,志愿者们需要抓紧时间为她读录相应的有声教材和练习册。专业的教材,由大学生或律师事务所的志愿者在周末时间集体合作完成。
北京有近十万盲人,全国有一千多万盲人,不是谁都有幸能享受到这样的“点对点”服务。
目前,“红丹丹心目图书馆”已经完成的图书只有一百多本,离真正的“图书馆”还有很大距离。而只有当有声图书馆的藏书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效应,服务更多盲人。
理想的方式是,音频的录制或者下载收听都能在网络平台上完成,这样,获得权限的志愿者可以在网上上传、编辑音频,分工协作,提高录制效率。盲人也可以足不出户,通过残疾证号登录浏览书目,选择自己喜欢的图书下载阅听。
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了。
郑晓洁说,目前“红丹丹”的有声图书数量还很有限,处于积累阶段。
而盲人对有声图书的需求,也是在了解的过程中才培养起来的。“盲人不像我们,了解的信息多,他们也不知道有哪些书可以读,自己想读那些书,只有我们先提供给他们,介绍给他们,他们才能选择。”
“助盲必须发动社会机构的力量,单靠政府是无法完成的,因为盲人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服务。”在多年的探索中,郑晓洁渐渐感到,民间的助盲机构比起资源雄厚的官方组织,虽然只是弱小的细流,却能顾及到政府顾及不到的层面,并且能更加直接地了解盲人的需求,在服务的理念和细节方面走在前面。“当残联提供助残券进行基本救助的时候,红丹丹已经在尝试为盲人提供更平等的精神和文化选择了。”
“红丹丹”希望在2015年前完成一万本书的录制,这需要他们提前完成一万名志愿者的培训。只是,真正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志愿者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