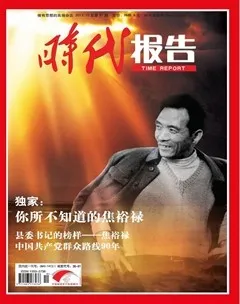周原、陈健:从未披露过的焦裕禄报道始末
2013-12-29
1966年初,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从北京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取道郑州,在河南分社短暂停留。
到达后,穆青与同行的冯健、杨居人等召集河南分社记者座谈,座谈会上周原一直保持沉默:“谁能发言谁不能发言,事先已由分社社长朱波内定,他没有安排我。”
那时的周原,身份是“摘帽右派”,业务上他们夫妇二人均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主力,政治上却是备受排挤、歧视的边缘人。1957年,周原因一篇反映三门峡工程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内参,被划成“右派”,1958年发配河南林县劳动改造,四年后才“摘帽”。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他能够重回新华社当记者,已算特殊的“照顾”。
出乎周原和分社领导意料的是,在指定的记者全部谈完后,穆青直接点了周原的名:“周原,我来了,你为什么不发言?”
穆青早就知道周原。原名乔元庆的周原,父亲是与范长江同时代的新闻人乔秋远。1942年在太行山随左权将军采访时,乔秋远与左权同时被日军杀害,同墓安葬。周原15岁时跟随开辟豫西革命根据地的皮定钧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九死一生。1948年为继承父志,他放弃了担任区委书记的安排,主动要求调到新华社当记者。
既然穆青指定他谈,周原便将自己在豫北黄河故道老灾区采访七个月了解的情况和盘托出。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就饱受“旱、涝、蝗”之苦,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更是千疮百孔、困难重重……他给穆青讲了一个故事:“ 原阳县农村有位老太太,经常在粮店一坐就是半天,问她坐在这里干什么?她说:“俺连年吃国家的救济粮,啥时候能拿条小手巾提一兜自己种的余粮到公社走走,心里就舒坦了。”
周原讲完,穆青很激动,留下了一句话:“在河南当农村记者,不到灾区采访就不是个好记者!”
第二天穆青一行就去了西安。临走时交代分社社长朱波,让周原替他去豫东灾区物色采访线索、找出一个典型,十天半月后他再回来听周原汇报。
周原当天出发,第一站是穆青的老家杞县。接待他的人说县里干部都看戏去了,采访要等明天。周原决定不在这里停留。第二天一早,他在汽车站旁的小摊上吃完一碗元宵,正想着该往哪里去,一辆开往兰考的汽车刚好启动,于是他跳上去,补了张票。
他在豫北采访七个月都没有找到的那个“典型”,就这样,在兰考找到了。
周原到兰考的时候,焦裕禄已去世一年半。此前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张应先、鲁保国已经写过一篇1700字关于焦裕禄的新闻,发在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二版左下角,《河南日报》一版也有刊载。但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周原也没有印象,还是听了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的介绍,他才知道。
刘俊生给周原看一把藤椅,椅子一侧破了个洞。他告诉周原,藤椅是前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坐过的,焦书记患了肝癌自己却不知道,肝痛难忍时就用根棍子一头顶住肝部一头顶住藤椅,久而久之把椅子都顶破了。就是带着这样的疼痛,焦裕禄坚持工作,最后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周原摸着藤椅和刘俊生一起哭了。
按照当时记者的采访程序,刘俊生首先要向县里一把手、新任县委书记周化民汇报,周化民同时也是兰考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周原回忆周化民的答复:“他说他刚来兰考不久,情况不熟悉,‘你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吧,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找我’。”
周原与张钦礼一口气谈了十八个小时,一直聊到下半夜。张钦礼详细介绍了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积极改善兰考贫困面貌的事迹,期间,谈话经常被两人抑制不住的抽泣打断。“如果他当时主要介绍焦裕禄如何抓阶级斗争,我们不会谈那么久,我也根本不会继续采访,会掉头就走。”正因为张钦礼谈的是焦裕禄抓生产,谈的是“如何让群众吃饱饭”,才与周原的“寻找”一拍即合。
周原并没有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张钦礼的讲述:“张钦礼这个人,一张铁嘴,能言善道。他把焦裕禄的事情讲得非常圆满,可信不可信,我还要再深入了解。”
天一亮,两人一人一辆自行车,去了张庄。“张庄有一个大沙丘名叫九米九,焦裕禄提出的封沙丘办法在这里最能看出成效。另外张庄也是张钦礼蹲点的地方,在点上最能看出他的为人、做派和群众关系,能进一步证实他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可靠程度。”
“我在张庄住了几天。白天采访群众,把张钦礼对焦裕禄的介绍向老百姓求证。晚上和张钦礼住在一间草屋里,继续聊。”
由于穆青“十天半月”之后要听汇报,周原在兰考只能停留五六天,这五六天里他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地连续采访。离开兰考后,他用剩下的时间去了民权、柘城、虞县等地,对豫东做了个整体调查。回到郑州,穆青一行也正好从西安折返,住在河南省委南院。
穆青决定去开封采访,一路上周原继续向穆青汇报情况。焦裕禄这个重大典型也引起了穆青的兴趣。鉴于焦逝世已近两年,现在再做大的文章,需要新闻由头出现。穆青想先去下面看看,等焦裕禄迁坟时(焦裕禄病逝后就近葬在郑州郊区,后来才遵照他的遗愿迁葬兰考)再写这篇通讯。
从开封去各县之前,穆青对同行的所有人说:“这一次到豫东采访,时间是半个月,由周原提问,你们只管备记,周原说去哪个县就去哪个县,周原说停留几天就停留几天,他就是这个采访组的秘书长。”
有了穆青这样的支持,周原便把整个采访的重点安排在了兰考。他先用一个县一天的进度,把之前到过的几个县都重去了一遍,最后来到兰考。
到兰考时,是上午十点。“张钦礼有些紧张。兰考是个穷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北京的记者。他把我拉到一边问:‘前几天都跟你谈过了,怎么你又带了个副社长来?还要谈什么呢?’我说,你上次怎么跟我谈的,这次还怎么跟他们谈,可以更细致些。”
起初的拘谨过去后,张钦礼越谈越开,穆青也几次泣不成声。因为哭得太厉害,穆青甚至吃不下饭。他们听了张钦礼一天的汇报,“哭成一团”。周原说:“当晚穆青变了态度:不用等到迁坟,这篇通讯要立即写出来!”
第三天早饭后他们就离开兰考,回到开封,住在了当时河南省条件最好的开封宾馆。
在开封宾馆,穆青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周原写焦裕禄这篇通讯,冯健写另一篇通讯介绍豫东抗灾全景,杨居人写社论,朱波写短评。要求第二天一早交稿。
周原回忆:“晚上,大家各自在屋里写稿,穆青在不同房间当中巡视,走来走去。当我写下‘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穆青拍着桌子说:‘这样的句子多来几句!’”
十个小时没有停笔,一个通宵之后,周原交出了草稿。
早饭后他们回到郑州,周原回分社,穆青等人仍住在省委内部的招待所。陈健回忆:“周原一晚没睡,到家后继续写稿,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写出了一万两千字。穆青通知他去招待所向省委汇报,并且要他在汇报会上读初稿。”
当晚,穆青就带着这份初稿回了北京。
但当时已是文革前夕,整个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阶级斗争论盛行。这一篇完全无涉阶级斗争、主要谈生产的通讯稿,能不能顺利刊发,不仅周原心里没底,连穆青也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是,“穆青解决了这个问题”。周原承认,如果没有穆青,焦裕禄大通讯也许又是另外一种命运。(本文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