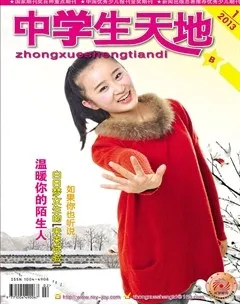票友小金
2013-12-29翁云骞
11月11日,杭州知名的草根票友俱乐部咏秋社在杭州图书馆的报告厅里举办折子戏专场。其中有一场,叫做《古城会》,讲的是三国刘关张的故事。当一个旗牌出来的时候,台下坐着的不少大学生戏迷沸腾了,大声地叫着“好——”。他们是专程从下沙高教园区赶来看自己的同学金天添的。
司马懿?曹操?
如果不是手里那把乌漆漆的扇子,实在是很难把金天添跟票友这个身份联系在一起。将近190cm的个头,超过80kg的体重,这位浙江传媒学院2012级新同学,“端的是气度不凡”。
其实,参加这么大规模的折子戏表演,金天添也是平生头一回。虽然唱词不多,他还是很兴奋。
小金今年20岁,搁几十年前的梨园,这是个该出成绩的年纪。电影《霸王别姬》里,少年流着泪自言自语,“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唱戏的都希望自己成“角儿”,小金也不例外,虽然,他现在只是个业余得不能再业余,偶尔跑跑龙套的小票友。
尽管没能走上正经八百的科班路,小金的京戏“生涯”,却着实不短。
“怎么爱上京戏的?……还真说不清了。那会儿才多大啊,怎么可能还记得?”
上世纪90年代末,金天添大概也就三、四岁的样子。对那个时候的小朋友来说,能玩的东西已经不少了,不过,他只记得那会儿中央三套每天下午都有戏曲节目。
“那时候就看故事呗,佩服诸葛亮,也认识曹操,刘备,当然那时候没什么觉悟,看到《空城计》里的司马懿,我老觉得很奇怪,咦,怎么曹操亲自来领兵打仗了。后来才明白,司马懿跟曹操都是大白脸。哈哈!”
随着年龄的增长,金天添看懂了更多戏,认识了更多人,慢慢的,他也就爱上了京戏这种在温州并不怎么流行的东西。小小年纪的他摆开架势,故意压低清亮的童声,有模有样地唱起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卡带机岁月
温州市信河街,有一个当地的戏协,金天添小时候就是在这里跟着老师学戏的。“一起学的基本上都是5、6年级的哥哥姐姐,我是最小的。想想那个场景还是挺喜感的,那么个小毛孩……”
不过金天添学得特认真,每当老师讲完一段唱词的要点难点,他总会不厌其烦地回家练习,然后,迫不及待地表演给爸妈看。
听京戏更是成了金天添每天的必修课。那会儿,MP3已逐渐在身边的同学中间流行开来,可金天添的随身听装备,还是那种老式的略显笨重的卡带机。
金天添的一大爱好,就是将经典的京剧音像材料,倒到随声听里,一边温习功课,一边轻轻地跟着哼。
“那会儿很痴迷啊,就好奇怎么会有人能把京戏唱得那么有味道?”从早上听到晚上,又从晚上听到早上。卷带了,金天添就会用小螺丝刀很仔细很仔细地打开盖子,用铅笔轻轻地往回卷……
听得多了,自然就能唱。当班里同学正讨论周杰伦哪首歌更火的时候,角落里发出的一声高亢叫白,往往会瞬间把大家统统“雷倒”。金天添清清嗓子,把卡带机摁成外放模式,旁若无人地在自己的位子上表演起来,有时,他甚至还会模仿京戏舞台上那类特别悲情的场景,大喊一声,飞快摇晃脑袋,“扑通”跪倒在教室的地板上……
“别唱了,老师来了!”同学们有时爱吓唬他,金天添可不上当,照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每到文艺汇演那几天,金天添算是找着发挥的地方了,在老师和同学们崇拜的目光里,他二话不说,身段一摆,信手拈来。
这段愉快的卡带机岁月,一直持续到金天添高中结束。现在,他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不过,内存卡里,装的还是各种京剧段子。“1个G的卡,里面有486首MP3,全是京剧,我自己从磁带中转录的。”小金得意地告诉我。
“悔不核心猿并意马”
因为变声的关系,小金的调门从上中学以来就一直上不去,这让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耿耿于怀。不过,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金天添对须生唱法尤为感兴趣。他最欣赏的演员是四大须生之一的杨宝森,最爱的唱段,是杨派的代表作《洪洋洞》。
“杨派的戏唱来有一种特悲凉的味道,我喜欢。”金天添告诉我,“比方说吧,《捉放曹》,陈宫在明月之夜,因为自己轻信了曹操,纠结不已,那种心理描摹,真好……”
百多年来,作为最受中国人推崇的戏曲门类,京戏的地位和价值,是不用多说的。金天添一直试图弄清楚京戏的这一种奇特的魔力,究竟来自哪里。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故事承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受人推崇的精神,比方说忠义、诚信等。”金天添告诉我,“虽然咱们也受西方的影响,可有些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改变不了的。”
“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戏曲中找到自己。你会发现,很多京戏里的词,即便放到现在,也很有现实意义。‘悔不该心猿并意马’,我觉得就很适合那些失恋了的同学唱……”
可是,在金天添这样的90后群体里,爱听京戏的,是比大熊猫还要稀有的存在。“一说起京戏,很多人都直摇头,说看不懂、欣赏不来。不过我倒是觉得与其说真听不懂,还不如说你是一开始就没有想听进去的念头。相比其他戏曲,京戏的咬字是非常规范的,经过一代代京剧人改良,已经打破了很多原来方言的局限,完全听得懂。”
说到这,小金又耐心地跟记者普及起京戏咬字的话题来。“以前在科班是这样的……”
一直在坚持
虽被誉为国粹,京戏现状实在很难让人乐观。 “我们传媒学院也有戏曲社,当时,我也是兴冲冲地跑过去,结果发现,所谓的戏曲社团,只有我一个人是唱京戏的,其他人都是越剧……”
京戏,这种在金天添眼里,太过“精耕细作”的传统玩意,在时代的演进中,遭遇到了尴尬的冷场。
这让小金多少有些失落啊。不过他能理解。“京戏么,总感觉有点像小农经济……不太适合现在的社会化大生产啊,网络时代,大家宁可玩网游,听口水歌,很少会耐着性子欣赏你的那些个唱腔、身段。”
即便如此,小金一直在坚持。高三那年,来杭州专业考试的间隙,他主动找到杭州知名的“草根票友俱乐部”——咏秋社,要求加入。现在,他已经成了这个俱乐部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每到周末,坐上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市区跟票友们交流,对小金来说,是一大乐事。此外,他还开始跟着咏秋社里一群已经工作的票友,鼓捣起了很潮的戏曲动画。
《西方哲学思想要义》《西方哲学史纲要》《德国电影心理史》……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金天添啃掉了好几本书。涉猎这些固然跟专业(小金的专业是文艺编导,因为“从小喜欢戏剧和表演”)有关,不过,金天添同时也希望能从中西方戏剧的对照学习中,了解京戏背后的一些东西。而这些,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京戏兴起和凋敝的原因吧。
此外,在2012年的秋天,小金还做了一件事——那会儿,正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剑拔弩张的时期,金天添利用课余时间,特地为这事儿写了一段戏词,然后,配上西皮二六或是西皮快板,在室友们面前,大声唱起来。
“好久没这么痛快地说过话了……不会吧,两个钟头了?”
正聊着呢,小金忽然停下来,看了眼手机,问我。
我疑惑地看着他:这么一个开朗的、活跃的男孩,也有找不到“倾听者”的孤独和寂寞么?直到他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在邮件里告诉我,“他就是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我们可能会因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放弃很多小时候喜欢的东西,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瞬间我仿佛有些懂了。
就像手里的那把略显不合时宜的扇子一样,小金对京戏,对传统的热爱,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或许,在同学们的眼里,小金总是个微笑着的、个性爽朗的家伙,空了也爱跟大家侃侃NBA,或者足球比赛。可是,在他高大、阳光的身体里头,却似乎一直藏着一些,用他朋友的话说,“细腻”,“文艺”,甚至是“多愁善感”的东西。
这些,到底是京戏带给他的呢,抑或是天性使然?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无论怎样,从他认真的背影中,我看到了一种这个浮躁的时代里,年轻人少有的踏实和淡定。
喜欢一件事,并坚持下去,这,永远都是值得鼓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