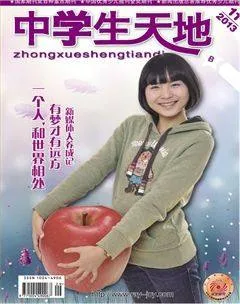关于爷爷那些事
2013-12-29沈来吉
山东烟台,朝阳刚刚探出漆黑深邃的海面,滚滚浪涛击打着斑驳的礁石。一声嘹亮的号角响起,海军战士们精神抖擞地排成几列,坚毅的眼神中,透射出保家卫国的决心!
我的爷爷,便是这些战士中的一员。
上世纪60年代,政府来村里征兵,爷爷鼓起勇气前去应征。听他说,那时候家里穷,自己去当兵,也算是早日独立吧。于是,爷爷就成了一名海军。
爷爷退役归来,政府给他在村里小学安排了一个代课教师的职位,这对于能文善画的爷爷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差事了。但那阵子老天爷好像打了个盹,几次转正的机会,都与爷爷擦肩而过。
不久,镇里建起电影院,爷爷便“跳槽”当上了影院的售票员。上世纪70年代末,在镇上的电影院里工作,可算是一个荣耀的美差了。当时文化产品极其贫乏,电影票价也不贵,对村镇居民特别是年轻人而言,看电影绝对是莫大的享受。每每电影院放映新电影,都会是全镇轰动的一个大新闻,排队买不到电影票成了人们最大的苦恼。
每当电影开场前,“饥渴”的消费者们便会一拥而上抢票,倘若忙中出错少收了钱或者在混乱中丢失了电影票,那爷爷是要自己掏腰包赔的,所以他便去定制了一个铁笼子,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售票,万无一失。可惜这个铁笼子现在不知所踪,不然,绝对是中国农村文化娱乐发展历程的一个有趣的佐证。
再后来,爷爷在印染厂做了几年,之后回家养鸭子、腌白菜。听爷爷说,那时他还是壮年,脚力大,腌出的白菜又脆又香。这手艺至今还被村民津津乐道。
爷爷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是管理航坞山采石场的炸药库。六十大寿一过,到了退休年龄,爷爷便不再工作了。于是每天凌晨,他会推着那辆老古董的永久牌自行车,去航坞山下的水库附近晨练,车肚子上总会挂一个土黄色的军包,里面装着各种外出的必备品。有时候我沿河边走着出去买早饭,看到锻炼完毕的爷爷迈着不紧不慢的小步,正推车回家。见我问候他,爷爷便嘴角一咧,大手一挥,然后继续一脸淡定地推车前行。回到家吃完饭,爷爷便会打开那台小彩电,磕磕瓜子吃吃花生,优哉游哉地开始欣赏电视节目……
是的,自退休以后,爷爷的生活便是优哉游哉的。但另一方面,听妈妈和姑姑说,爷爷和奶奶自从结婚起就一直在拌嘴。以前因为爷爷要工作,他俩一天相处不了多久,也不怎么吵得起来,自爷爷退休后,两人为点鸡毛蒜皮的事也会爆发“世界大战”。我不禁感慨,不愧是“老拌”!
有时着实是爷爷理亏,可他依然会瞪大眼睛憋红了脸,为了面子朝奶奶大吼大叫。奶奶当然也不甘示弱了,结果越吵越激烈。这时妈妈不得不站出来,理智地判断谁对谁错,然后加入占理的一方。当然了,帮人的方式也不同。若是奶奶理亏,妈妈便会耐心地劝奶奶消消气,别再与爷爷争论了,因为平时奶奶为大家烧饭、干杂活很是辛苦。对于爷爷的态度便没这么好了,老妈那霹雳般的话语如同豆大的雨点一样朝不占理的爷爷身上砸去,着实有效,不一会儿爷爷就消停了。不过,一番养精蓄锐之后,爷爷又会卷土重来。
我终于忍不住开始干涉。其实爷爷是很卖我面子的,一经我的干涉,若觉得有理便也会消停,而且再不会就此发作。当然了,我干预的方式绝不像老妈那样大呼小叫。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新新青年,自然是以理服人了。爷爷常到马路边的修车铺那里坐坐,和好友阿亮师傅畅谈,谈着谈着就谈到了自己的孙子。爷爷很自豪,常说我明白事理,家里一些争吵的导火线,被我三言两语就熄灭了。
从小到大,爷爷或许不像奶奶那样对我慈爱,不像妈妈那样照顾我无微不至,但是他对我的关心,回忆起来也觉得别有一番温馨。
小时候我酷爱养鱼,常去家附近的池塘捕鱼。每次奶奶拿着自制的鱼兜带我去捞鱼,若被爷爷见到的话总会极力阻止,而那些话总被稚嫩的我当作耳边风,刮过了就没了。多年以后当我明白水的极度凶险,才领悟到那些扫兴的话其实是对的!当然,我也早已过了爱抓鱼养鱼的年龄。
后来上初中了。每逢周六,家里就剩我和爷爷。每次吃完早饭之后,爷爷总习惯性地问我,中饭该不该把我的那份加进去,我也会亘古不变地回应他:“是的,在家里吃!”我不会像老妈那样去损他:“你说我不在家里吃,那在哪儿吃?”因为我懂得对一个老年人没必要拐弯抹角,爷爷希望我在家吃饭才会这样问,尽管显得多余。
晌午,爷爷备好了美味的菜肴,总会乐呵呵地问我:“今天爷爷的茄子汤很鲜啊,要不要再来点?”吃饭的时候,爷爷喜欢喝两盏。酒到开怀处,便会大声朗诵《沁园春·雪》之类的革命诗词,或者滔滔不绝地讲起那些古老的往事,他的青年时代……这时候,作为一个聆听者也是一种享受。
日子悄然溜走,转眼我已经是一个高中生了。
现在对于我,学校像家,家却像旅馆。我回家的次数渐渐减少,与爷爷的交流也屈指可数。周五回到家,总会看见爷爷安静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打盹,有时他会木讷地盯着前方,或许是在想一些事。看到我,爷爷一下子就会高兴起来:“你来啦!”然后便兴冲冲地听我讲学校里的见闻。我想,也许孙子回家也算是他老人家的一大乐事了吧。
我走在成长路上,爷爷的背却一天天地佝偻下去。我长大了,也读了一些书,龙应台的《目送》、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毕淑敏的《孝心无价》……渐渐明白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理解爷爷身怀才华、心比天高,却一辈子不被人重视的苦闷,也能接受爷爷理所当然地早早退休养老。尽管隔了一辈,我想爷爷还是很爱我的,只是不善于流露与表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