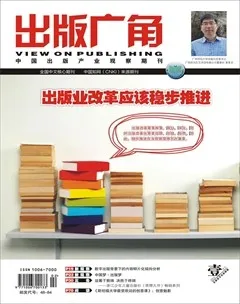从《千古绝唱·二泉映月》重温阿炳的艺术意境
2013-12-29段志敏于大海
阿炳,原名华彦钧,著名的民间音乐家。他的一生历经坎坷,生活漂泊、困顿,同时又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然而,身处逆境却愈发坚强,他坚持音乐创作和演奏,一生创作并演出了270多首乐曲。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他的二胡曲《二泉映月》了。他的《二泉映月》名气很大,蜚声中外乐坛,但是,对它艺术意蕴的解读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更科学、准确地理解呢?窃以为,应从还原历史情境、研究音乐本身的形式、研究听众的接受三个角度去把握。
在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方法叫做“知人论世”,意思是说,要想准确把握一篇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必须了解这个人的生平经历、社会背景和思想性格等方面,再结合作品本身,才能准确还原当时历史情境下作品的原意。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包含了创作者的人生阅历、思想性格和历史情境下的特定情感,所以,研究一首音乐作品的艺术意蕴,同样要知人论世,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
阿炳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他的父亲华清和是无锡三清殿的一名道士,精通道教音乐。他四岁丧母,寄人篱下。八岁就跟随父亲做了一名小道士。由于他聪明好学,心无旁骛,所以到了十二岁就已经能演奏多种乐器。
当他二十五岁时,父亲去世,三十四岁时,双目失明。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在北方,北洋军阀执政,在南方,革命的风潮在酝酿。可以说是举国上下混乱不堪,平民百姓艰难度日。阿炳身处乱世,又双目失明,其生活之悲惨可想而知。后来,时局更加动乱,日军侵占东北,继而侵占华北。由于战乱不断,人民生活更加艰苦。为了谋生,他背上二胡,自编自唱,在街头卖艺,沦为街头艺人。由于他饱经沧桑,创作的唱词很是感人,演奏的乐曲满含着时代的沧桑与悲凉,因此深受当时大众的喜爱。著名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二泉映月》中的“泉”指的是惠山泉,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西郊的锡惠公园。中唐诗人李绅曾描写道:“惠山书堂前,松竹之下,有泉甘爽,乃人间灵液,清鉴肌骨。漱开神虑,茶得此水,皆尽芳味也。”可见其清幽清冽之特色。清代乾隆皇帝封其为“天下第二泉”。阿炳以“二泉映月”为他的二胡独奏乐曲命名,有其独特的用意。《阿炳曲集》一书中曾这样说:“他……用音乐形象来描绘他想象中旧时曾目睹的美丽风景……但当时感到的却是周围漆黑的一片。这就使得他在宛转优美的旋律中,时时流露出感伤凄凉的情调来”。
通过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原作者的人生经历,探讨阿炳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追溯作品中的“泉”的意象的生活原型,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音乐的艺术意蕴。
从乐曲本身来看,《二泉映月》的体式结构是变奏曲。由一个引子、一个主题段、五个变奏段构成。音乐开端是短小的引子,下行的旋律好像一声揉满了酸甜苦辣的轻轻叹息,开始慢慢带领听众进入情境。接下来就是主题段,它的第一乐句一入手就开始倾诉,低沉、悠扬、婉转的调子如泣如诉,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这时,第二乐句突然翻高八度,声音纤细,渐趋高亢,演奏出难以抑制的伤感和哀怨,把听众的情感带入了主旋律之中。第三乐句在第一、二乐句的情感发展之后,更加强化重音和顿挫感,进一步抒发纠结的、令人心潮难平的情感,这是乐曲的首个高潮。后面的变奏段以此旋律为基调,稍加变化,达到了反复吟唱、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二泉映月》就是以上述音调为主要旋律,通过多次变奏,在反复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主线,逐步展开,构成全曲。它通过变奏这一艺术手段使阿炳压抑、激愤的音乐形象得到层层深化,仿佛能使人感受到阿炳那难以抑制的感情顷刻就要爆发。乐曲一遍遍地诉说他的遭遇和苦难,感人至深。《二泉映月》的后半部分,情调更加激昂,情感的倾诉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再次把乐曲推向高潮,表达了阿炳难以释怀的苦闷和深深的忧伤。它深刻反映了阿炳那刚毅、倔强的性格,展示了他对坎坷命运乃至险恶环境积极的斗争和反抗。回环往复的主题音乐,使人联想到一个戴着墨镜、拄着拐棍的盲艺人,在处处艰难的人生道路上颠沛流离,道尽了他的无限感伤、不尽凄凉。
《二泉映月》音调借鉴了江南一带的民间音乐,也借鉴了在道观中学习的道教音乐,风格凄凉中有清丽,行云流水的韵律中有感伤。它的曲式结构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循环,一个是变奏。通过循环,表达一唱三叹、情思不尽的情感样式;通过变奏,即利用乐句的扩充、缩减,再结合个别音符音高的升降,使得音乐产生层层推进的效果和迂回往复的特点,从而强化了阿炳的音乐形象。它的旋律采用了中国民间首尾衔接法,使音乐呈现出行云流水一般的起伏感和律动感,令听众为之泪下。此外,乐曲于深沉中包含质朴,感伤中犹见苍劲,就这样刚柔相济,起到了动人心魄的效果。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美学家姚斯提出,美学研究应该把作品放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去研究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他认为,不能仅从作品这一个方面去研究,还应研究作品的接受过程。假如一部作品经过作者的创作已经成型,并不能说明这部作品已经实现它的存在,只能说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只有经过读者的接受、鉴赏、反馈,进而继续影响作者的创作,才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存在过程。
作为一部音乐作品,我们也不能单单从作品的形式本身去解析,还要把它放在听众(接受者)的角度来研究,研究接受者的接受心态、接受水平和接受特色。现代人往往不能很好地理解阿炳的《二泉映月》,或者不能体会其中的艺术意蕴,就是因为没有站在接受美学的立场去研究。
从作品的产生过程来说,《二泉映月》的艺术意蕴同阿炳所处社会环境,以及他低下的社会地位有关。这首乐曲问世以后,对于它的评判的权利就不在阿炳手中了,它面对的是不同时期的不同演奏者和不同听众,面对的是演奏者对《二泉映月》的二次创造和听众对《二泉映月》的重新定位。在这种情况下,《二泉映月》意蕴难以穷尽,新的理解又会不断出现,人们在沉醉于乐曲营造的优美、忧伤的氛围之外,自然也会将自我的人生经历投射其中。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不能说现代人难以理解阿炳内心的情感和他的创作,是因为时过境迁,时代变了、环境也变了,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也不一样。必须承认,演奏者、听众与阿炳之间必然存在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但这不能成为曲解《二泉映月》的借口,亦即,现代人不能从自己的主观出发,随意曲解阿炳及其《二泉映月》,也不能完全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不着边际地去评判作品的艺术意蕴和价值内涵。
要想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地理解、把握阿炳的精神世界和他的《二泉映月》,首先就应该深入到他曾经生存的、作品借以产生的历史环境,还有作者经历过的思想感情中;其次是深入研究音乐作品的文本,从纯粹的形式入手,揭示其艺术规律,进而探讨它的艺术意蕴;再次,还应该站在接受美学的立场,研究接受者如何演奏、欣赏和评价这部音乐作品。只有站在不同的角度,综合地看待和理解音乐作品,才能更好地把握它。虽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完全理解阿炳的本意、完全把握作品的全部意义、完全理解作品的艺术价值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从各个方面抵达的力度有多大,作品向我们展示的意义就有多深,离作品的原意也就更近了一步。
(作者单位:段志敏,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于大海,河北省教育发展研究与信息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