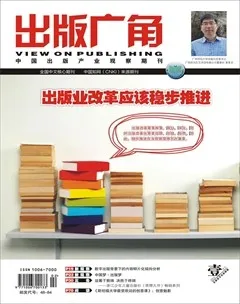背后的故事
2013-12-29周飞
近代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学识渊博,治河、天算、乐律、辞章、天文、医学、兵学俱诣臻精绝,又酷爱古玩收藏,是个具有极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的人。小说的主人公老残也很有学问,为人爱好风雅,喜读宋版古书,还兴致勃勃地去寻访古书,又常常因感慨时事而题壁作诗,就连吃饭也颇为讲究,喜欢吃起来有松树清香的“松花鸡”。刘鹗借老残行事的不凡,映衬其人品的高雅脱俗,这种艺术化的做法是对自己不平凡的为人处世方式的另类注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老残游记》中的音乐描写,例如“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一段,称得上此书最为精彩的文字之一。刘鹗通过丰富的想象、大胆出新的词汇将难以把握的声音描绘得生动可感、异彩纷呈,读来令人为之神往,他的文字功底、学识涵养也由此为人所称道。不少论者就此段的艺术技巧和特色进行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分析,有的已成为不刊之论。而细细品读之下,透过其精彩的表层文字我们尚能发现许多丰富和深刻的信息,这对于深入理解刘鹗和《老残游记》都有很大的帮助。
《老残游记》中有很多地方是刘鹗自身亲历之事,在某一方面可称得上“实录”,明湖居听白妞说书也是如此。刘鹗在书中曾借茶房之口向读者介绍了白妞这位说书人和她的说书艺术,而据跟随刘鹗多年的老仆李贵回忆:“二太爷在书中(指《老残游记》)所说在济南明湖居听白妞儿和黑妞儿说书,是确有其事,也确有其人。姐姐叫白妞儿,妹妹叫黑妞儿。白妞儿说的《黑驴段》,我虽然站在最后排,也听得清清楚楚。就是说到最快的时候,也字字入耳。”
不唯此书,在他人的笔下也留下了许多对这位负有盛名的民间女艺人及其说书艺术的记载。王以慜(字梦湘,湖南人)在《檗屋诗存·济上集·济城篇并序》中更为详尽地描绘了王小玉(白妞)和她的演唱,许多地方可与刘鹗明湖居听书中所写相互印证。更为巧合和有趣的是,刘鹗在书中还写到了这位梦湘先生也在听王小玉演唱。他们的笔都使得王小玉和梨花大鼓得以流芳后世,这算得上《老残游记》此段文字的文献功绩之一了。
刘鹗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他本人就是一个精通音乐的音乐家。刘鹗的母亲朱太夫人“精音律”,继室郑氏“亦能度曲”,二姐鲍氏善弹琴,他的内外两家表姐妹中擅长此道者不乏其人。刘鹗本人从家庭中受到熏陶,后又拜师聆教,先从劳泮颉学琴,后得名琴师张瑞珊指教,因而妙解音律,弹奏颇精。其侄刘大钧曾著文特意描绘过刘鹗弹奏《平沙落雁》曲的情状,此曲是他苦心学习的琴曲之一。在其现存的《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谈到音乐的地方不下二十处,其中乙巳六月十七日记有“《平沙落雁》温竟”、六月二十五日记有“温《平沙落雁》一曲”,足见他对音乐学习的重视。刘鹗还精通乐理,曾为张瑞珊编著的《十一弦馆琴谱》写过序,其中有些评论颇有见地和史料价值,例如“琴之为物也同乎道。《参同契》《悟真扁》传道之书也。不遇名师指授,犹废书也。琴学赖谱以传,专恃书又不足以尽其妙,不经师授,亦废书也。故学琴重谱,尤重师传。”“琴之妙用在吟、揉,在泛音,张君悉能于琵琶得之,谓非神乎技耶?”“常考古人制曲之道,不出三端:一曰以声写情最上,如《汉宫秋月》《石上流泉》《高山》《白雪》《胡笳》《捣衣》《平沙落雁》之类是也;二曰按律谐声次之,如《梅花三弄》《一撒金》之类是也;三曰依文叶声又次之,如《释谈》《秋声赋》《赤壁赋》之类是也。张先生所制之曲,大概按律谐声之类。节奏则采之於古妙,用则独出心裁,宜古宜今,亦风亦雅。”这些评论均有见地。又言道:“古今各家所制之曲,传於今有谱可稽者,大概二百三十六操。明末国初人所制者居其半,近百年内自制曲者未之有闻。有之,仅我大兴张瑞珊先生一人而已。”此于琴曲史可备一说。
明乎刘鹗于音乐之修养,就可窥知其写音乐之妙的秘诀了。能用如此精彩的文字描绘出白妞说书的音乐之美,不仅在于他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还在于他比之常人能将乐感更为敏锐地捕捉住并能传神地将其表达出来,可以说刘鹗是带着知音难觅的真诚的心,以一位音乐家的耳目来聆听和评判的。刘鹗并没有因为白妞说书是上不得台面的民间技艺而有所轻视,而是在书中不吝笔墨,浓墨重彩地为其出场喧声造势,经过层层铺垫方令其一展歌喉,技惊全场,可见是由衷地钦佩和赞美白妞的说书技艺的。此中原因不仅仅是刘鹗在她的音乐中欣赏到了美,更在于他从白妞的成功中找到了思想的共通之处,引起了他心灵上的强烈共鸣。白妞这一“天生的怪物”广泛吸取西皮、二簧、梆子腔等艺术营养,博采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等艺术大师之长,把本来“没什么出奇”的“乡下的土调”,改造成令人神魂颠倒的“绝调”,这与刘鹗一向赞成并为之实践的道路——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暗暗契合,刘鹗怎能不赞之为心灵上的同道呢?而此时刘鹗笔下的老残也恰好刚刚“略施小技”,治好了大户黄瑞和的“奇病”,正当信心百倍、志得意满之时,方欲大展身手地做一番大事业,让上至达官、下至平民都为他的“绝调”叹为观止!笔者认为这才是刘鹗饱含真情的笔墨所要传达的真正信息。
读者们还可以从 “三月不知肉味”“于我心有戚戚焉”这些评价音乐的字眼中,更深刻地体会出刘鹗当时的心境。《论语·述而》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八佾》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郑玄注云:“《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 毛诗大序》又言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刘鹗认为白妞说书深受民众喜爱,为各阶层的人都带来美的享受,可以说臻于尽善尽美的妙境,这不仅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乱世亡国之音,反而正是他所期盼的政和人安的治世之音。这种官民和乐的景象也正是儒家先贤称颂的、刘鹗自己为之极力奔走的理想的社会太平景象。也就是说刘鹗有感于“棋局已残”的国家现况,因而希望统治者能采用“尽善尽美”的方法来治疗“创伤”,让民众得以安享太平世界。而刘鹗的这种美好的心愿却在现实当中遭到了一次次的打击,正如小说中所写到的那样,玉贤、刚弼之流暴虐残忍、刚愎自用,宫保不能接纳自己的正确意见,一切都如同严冬的天气般令人感到心寒、压抑,让老残为之唏嘘不已,恰与此时听白妞说书时轻松惬意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见这段明湖居说书并非字面上显露的那么简单明了,更非单纯的就音乐写音乐以显示自己的文字技巧,而是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内涵,这更应得到我们的重视。
言为心声,乐为心曲。其实,刘鹗这种借音乐以抒情和寄托理想的笔法不唯此处。在第十回“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箜篌”中黄龙子与玙姑一个弹琴一个鼓瑟,合奏了一曲《海水天风》曲。这段描写较之写白妞说书亦毫不逊色,更见高雅不俗,可见刘鹗音乐造诣之高,雅俗俱通,确为描音之圣手。作者还借申子平之口叹道:“此曲妙到极处!”而玙姑对此曲中蕴涵的“君子和而不同”这一哲理的一番解说则更是大有深意,正可与刘鹗致同门黄葆年的信相互印证。刘鹗在信中言道:“……闻诸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每蒙不以强同苦我,真知我者矣。弟与诸君子殊途而同归,必不能同辙者也。……弟之所为,几无一事不与公相反;然至于所以为,窃又自以为无一事不与公相合也。……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可见在他看来,实现教养天下,富国强民的大业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必拘泥于成礼,正所谓“殊途不妨同归,异曲不妨同工”。而他自己正是选择了一条不太见容于一般人甚至是自己的同门能理解和支持的道路,由此遭到了世人的诘难。于是刘鹗借《海水天风》一曲,婉转曲折地表达了他心中由此产生的曲高和寡、知音难觅的感慨,同时又对世人的理解寄予了希望。
不管是白妞说书的明朗可亲、《海水天风》的清逸磊落,还是《胡马嘶风》的凄清悲壮,无不与作者的心境一一契合,且都能在音乐的美妙氛围中融入丰富的信息,令读者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作者的思想。这正是刘鹗以其高超的文笔极力描绘音乐之美的最终目的和最大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天津职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