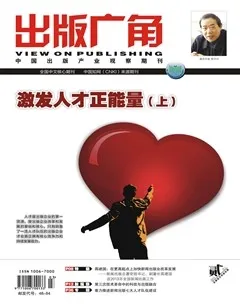翻译出版的社会历史性视野
2013-12-29宋祎凡
[摘要]翻译出版与社会历史语境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在研究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上海译文出版社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初出茅庐即锋芒毕露,三十余年来始终紧随社会发展的历史足迹,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市场化以及21世纪以来由市场主导到多元分化的出版环境中一直处于国内翻译出版领域的领先行列。从译文社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质量翻译出版的背后所体现出的对于时代、市场以及社会品位等要素的高层次追求。
[关键词]上海译文出版社 翻译出版 历史视野
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中国影响力极大的综合性专业翻译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1月1日,1992年被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命名为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单位,是中宣部表彰的全国首批优秀出版社之一。自1978 年成立以来的30多年,该社共介绍重要外国作家1000 多个,出版系列图书5000多种,辐射语种20 多个,现属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员,年出版总量在400种左右,出版码洋约1亿元。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在历史大环境的背景下以一种连续的视野考察某一事物的总体发展规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研究翻译出版的过程中,就非常有必要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认识到,翻译出版与社会历史语境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用出版行业的术语来讲,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大环境决定了翻译出版的选题策划等一系列出版行为,而不同的选题策划又会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开拓、引领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
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凝练、系统地介绍上海译文出版社三十余年来图书出版的基本情况,力图将译文社翻译出版的总体情况与社会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翻译出版行业的发展历程与足迹,进而从中摸索出一些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历时视野下译文社的出版足迹
(一)1978—1985:初出茅庐,锋芒毕露
上海译文出版社应该算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1978 年1月1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挂牌成立。据孙家晋、包文棣等第一代译文人回忆,译文社并非白手起家,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前身是成立于50年代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外国文学编辑室。它是将分散在上海各个出版社的翻译力量和稿件资源重新整合的结果,其组成人员不仅包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室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骨干,还有来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少儿出版社和作协等单位的编译力量。
1978年4月,《斯巴达克思》中译本出版,该书是“文革”十年后,首次公开发行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为了满足当时群众的阅读需要,在译文社成立之际,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在国内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呈现出丛书化、系列化的趋势。这时的译文社一方面加紧安排原有纸型的重版工作,以满足读者需求;另一方面,努力争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的机会,着手开始“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与此同时,译文社还凭借丰富的译者资源,在翻译质量上大下工夫,进行经典名著的重新翻译。如荷马史诗《奥德赛》,过去曾有从英文转译的译本,而译文社则找到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根据希腊文原文并参照其他现代通行注释本重新翻译。这一译本至今仍被读者奉为经典。
这一时期的译文社除了主要进行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外,也开始着手外语词典和外语教材的出版工作。在《斯巴达克思》中译本出版的同时,32开本的新一版《新英汉词典》出版,这是我国唯一一部编写于“文革”时期的双语词典。除英汉词典外,译文社还出版了《简明西汉词典》《德汉词典》《法汉词典》等多语种外语词典。
(二)1986—1990:追随“文化热”的足迹
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规模逐渐扩大,经济国门大开的同时也带进了西方各种知识理论、社会思潮,国内进而掀起“文化热”思潮。知识分子与年轻学子们有感于中西社会的巨大差距,出于对国家命运的焦虑,对各种时髦理论、新奇思潮如饥似渴。这就为翻译出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这一时期的译文社继续进行着前一阶段外国文学与外语工具书、外语教材的出版工作。在文学作品中,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受到读者的欢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是其中的代表。在外语工具书方面,我国第一部由英语专业人员自行规划设计、自订编辑方针编纂而成的大型综合性英汉词典《英汉大词典》上卷于1989年8月出版,但这些都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化热”的真正动力来源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推动。
1985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国内学者甘阳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恩斯特·卡西尔的代表作《人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部《人论》助燃了80年代中国的新一轮“文化热”。而收纳了这部《人论》的大型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已经影响了中国知识界30余年来的几代知识分子,至今方兴未艾。除此之外,译文社还从1987年开始推出一套“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并于1989年5月主持召开“当代学术思潮译介和研究”座谈会。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思潮中,译文社扮演了出版界的排头兵,彻底奠定了其在国内翻译出版界的领军地位。
(三)1991—2000:向着全面市场化进发
经济体制改革暨市场化改革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力度最大、突破最大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时的出版界就已现商业大潮的端倪,只是在“文化热”的锋芒下显得相对低调。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市场主导已成社会基本格局,出版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开始步入正轨。
邓小平南行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意识形态部门对文化出版方面的控制日趋宽松,减少了行政干预,一方面使得出版社在图书选题、出版形式上享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也让出版社失去了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者所独享的体制庇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版社的首要任务就是完善自身的市场化机制,摆脱行政依赖心理,由单纯的生产者转变为独立的组织经营者。这也是译文社所必须要面对的形势。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译林出版社的崛起与非法出版物的兴风作浪,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时期,译文社在转型过程中开辟出了两条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出版业先河。从1988年与1990年开始,译文社先后推出“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与普及本,大开翻译出版业“分众市场”的风气。两种版本不仅在装帧上用料不同,选题上也区分了读者的文学修养与艺术格调,在当时绝属颇具胆识。到1991年,15种珍藏本销售100万册,15种普及本销售600万册,其中1991年普及本发行量达360万册,几乎每天销出1万册。1991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签约购买下美国通俗小说名作《飘》的续作——《斯佳丽》的版权,并在11月5日的《新闻出版报》上刊出声明,表示获得《斯佳丽》中文简体字版版权。这是中国出版界中首次取得国外畅销书的独家版权,而此时我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国内很多尚且没有意识到版权意义及规范的出版社还在沉迷于享受“免费午餐”。
无论是细分市场还是购买版权,都很好地体现出译文社的市场意识,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走市场化道路的过程中,由庸俗的商品化带来的“物化”与“异化”确实在所难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改革不彻底的环境下,就更容易幻化出畸变的市场。这一点,出版业也不会例外。
就译文社来看,市场化中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出版格调的庸俗化倾向。如英国作家萨克雷的作品 Vanity Fair 通译《名利场》,在上文提到的“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丛书中却被译为《花花世界》,其意图明显是为了吸引某部分读者的眼球。其次,过分追求市场利益也导致了图书质量的下降。以译本的产生方式为例,之前的译本多为译者精心打磨多年方交由出版社审读,出版社又经过多次审校才最终付印,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多为译者自主选择或是编辑与译者协商一致后的结果。但在市场化浪潮的席卷下,选题多为迎合市场而定,翻译者也是随便找来,编辑过程中的审校更是马马虎虎——这些都是翻译出版的大忌。
译文社就在这种市场化的腥风血雨中又走过了十年。1999年2月,经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上海译文出版社与上海人民社、上海古籍社、上海远东社等14家上海出版社共同组成了国内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企业集团模式的新天地中,译文社走入了新世纪。
(四)2001—2011:由市场主导到多元分化
走过思想启蒙的80年代与市场导向的90年代,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市场化格局逐步完善的社会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又逐渐呈现出一种多元分化的局面,曾经靠几本世界名著就可以打遍天下的出版历史一去不返。
从物质层面上看,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强烈冲击了人们传统的价值取向和固有的文化心理,以“符号消费”为基础的“消费社会”全面蔓延,读者的基本阅读追求不再是获得心灵的永久丰富而是一时的麻醉快感。从制度层面上看,市场化社会的进一步完善消解了原先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依附关系,个体独立性得到加强,但同时又因为人际关系的疏离导致个体心灵的空虚与悲寥,读者阅读的小众化、细腻化因而突显。从技术层面看,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刺激作用更强的媒介对传统阅读构成空前挑战,读者逐渐趋向于影像阅读、有声阅读、无纸阅读。
基于以上种种现实情况,出版业再一次走到了荆棘密布的道路上,但机遇与挑战往往并存,能够“化危为机”者方能脱颖而出。译文社在翻译出版界显然属于高手,继引领了80年代“文化热”,顺应了90年代市场化潮流之后,又掌控了“多元分化”时代的主动权。
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图书总目中可以发现,除了对传统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新出或再版以外,译文社还出版有“村上春树文集”“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译文新流行”“译文童书”“青春译丛”“环保大特写”“美味系列”等针对各种不同受众的丛书、书系,将大众市场与小众市场紧密结合。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足见译文社对于市场的煞费苦心,但这绝对不会是一家之为——在今天日趋多元化的出版环境下,如果不做到如此程度又何以抢占市场?
2003 年1月,《新民晚报》刊出《2002 年十大文学现象》一文,其中第十条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 10 多本文集,《挪威的森林》(全译本)销售近 20 万册。文集以新、齐、装帧漂亮而在外国文学书籍中独占鳌头。”上海《新民晚报》的评价应该算是切中肯綮的,出版“村上春树文集”是译文社在新世纪中的一次突破自我的成功案例。它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准确把握了多元化时代背景下以失意小资、懵懂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的情感取向;另一方面则是出版社在市场环境中的成功运作(包括版权垄断、规模效应、译者品牌、精美装帧等)。其实在2001年译文社推出“村上春树文集”之前,村上的作品早在1989年便被译介到国内,但却只有译文社在十年后的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村上热”,个中原因着实值得国内翻译出版界细细品味。当下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使得译文社在村上春树选题上不会永远保持“垄断”地位。从2008年开始,财大气粗的南海出版社开始接过村上作品的出版大旗,并于2010年出版号称“村上春树巅峰杰作”的《1Q84》,开启了“村上热”的又一时代。
二、共时视野中译文社的出版启示
回顾译文社的发展历史,虽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却能真实地反映国内翻译出版业三十余年来的前进历程。笔者通过较大篇幅以“大历史”的视野叙述译文社翻译出版活动的发展足迹,挂一漏万而无法面面俱到,只希望能从宏观上表明:翻译出版与社会历史语境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这种“互相建构”的价值往往要大于单纯的、机械的历史本身。
与此同时,按照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在我们通过纵轴以历史视野考察事物发展过程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横轴以共时视野发现被考察者相较于其他共存者的独领风骚之处。这样一来,在文章的最后,笔者不妨从上文对于译文社的历史考察中总结出一些可资国内翻译出版业借鉴的成功启示。
首先,在翻译出版与社会历史语境能够实现“互相建构”的前提下,翻译出版业必须能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风向有着敏锐的觉察。这一点是译文社从“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到“村上春树文集”一路走来得以独领风骚的核心要素。
其次,在出版业向着全面市场化大步进军的时代,“细分市场”与“购买版权”是翻译出版业务必须要抓好的两个环节。在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中,事实上却大有文章可做。特别是在版权方面,出版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财大气粗者胜出,“沟通”(Communication)永远是出版行业,特别是翻译出版业的关键词。
最后,正如前社长杨心慈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所讲,“高质量高品位”与“社会效益第一”是译文社三十年来成功的基础原则。这两点在今日市场主导的出版环境下也许显得“不切实际”,但无论如何,大部分的读者永远是心明眼亮的。一部格调庸俗、翻译拗口、错漏百出的翻译作品,无论市场营销做得如何天花乱坠,最终也难逃成为“出版垃圾”的结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1] 上海译文出版社 编. 走过的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2] 上海译文出版社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三十年图书总目:1978—2007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 肖燕.从两个17 年看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变化——以建国后1 7 年文学翻译作品与改革开放近1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比较为视角[J]. 科技信息,2010(24).
[4] 邹振环. 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