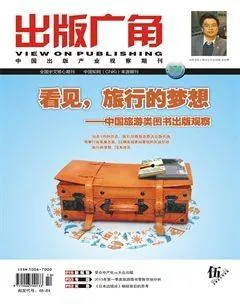编辑职业意识的养成漫谈
2013-12-29吴航斌
钱钟书说过这么一句话:“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里的光明,却在镜子里发现了自己。”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时常会想到这个问题:一个理想状态的编辑,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形象?或者说,怎样才是一个好编辑?这个问题,对“寻找光明”的意义而言,是受角色的指派而悬拟职业的佳境。众所周知,所谓理想的完美,恰在于它是遥不可及地无限接近。因此,出于求索光明而凝神审视,我们通常只能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我们已经够努力了,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苦苦寻找的光明,终究是要能落到我们身上的风采,才算真正的光明。
如是影影绰绰的感想,来自于“编辑的养成”这个话题。一茬茬的新手成长和老人退隐,一代代的出版人新陈代谢。新人初入出版社,于行业低迷、急需用人之际匆促上阵,入行之后,未加深思地接受了不少口耳相传的格言,也顺理成章一并收纳了许多本地偏见。至于多年的从业者,埋首罕抬头,习而相忘,惯而失察,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如果注意到一个行业缺乏中心思想,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思路匮乏废话不少,为什么客套话连篇而锐见罕闻。对此,思想家有现成的剖析:“人们有时并不寻求正确的东西,而是寻求与自己的愚蠢成见相吻合的东西。这是心理学规律。”
用编辑的字斟句酌来切入,比如,时下流行一句话叫“坚守出版”。也许它表现了一种职业信仰,惋惜内容却颇为空洞,反而泄露了弥漫在这个行业中的某种消极情绪。加之此话悲情意味太浓,口号感太重,是“决胜战”“攻坚战”的悲壮翻版,究其实际,坚守之“守”,多为换生不如守熟之“守”,而非家园留守之“守”。此外,尚有“为人做嫁衣”之类的职业理念。何以对“坚守”不以为然,是我总感到职业与兴趣固然难以两全,然而因职业参与总还有些乐子可寻。按照这个思路,“坚守”不如“乐在”,职业选择本是从业者的自由,既然此处痛苦,大可往彼乐土。因此,职业的光明,系于职业角色的充分发挥。
铺垫如此,基本意思是说,一个出版从业人员,理当经由编辑职业而成就为职业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有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即职业意识、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首先是头脑中时刻存在的职业意识,其次是专业技能的培养,再次是积久贯通的职业素养。专业技能可以决定本职工作的品格与质量,职业素养则决定着本职工作的持续、创新的发展。从职业主义的角度去梳理“编辑的养成”,就有一系列的命题,将之具体化和条理化,权且从职业意识、职业身份、职业深情和职业贡献等角度作一个考察。
第一,职业意识。职业意识是一种从事既久、自然而然的思维惯性,对于同一事件,职业意识能触发从业者的本职联想。笔者曾经读到一段关于画艺与文艺的参校,“好比西方的绘画,当前国内的写作也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种是无故事,无人性揭露,无社会意义的印象主义。以华丽伤感,精致颓靡的状态取胜,如梵高。一种是故事深沉,直抵人性的善恶,社会意义颇丰的批判现实主义。它以诚实、成熟、承前启后的态度与热情活着,如德拉克罗瓦。”读完之后,身为编辑,多年的职业训练据此作出反应,于是补上结尾,加上几句话发给作者:“前者拥趸不绝,后者无人问津。铺垫如此,是该祝愿大作畅销呢,还是祝愿大作滞销?一笑。”顷之作者答复:“正所谓,一本书有自己的造化。”编作之间于心领神会之际增进共识。
第二,职业身份。职业主义必先有一个职业身份的确认,所谓言行“得体”,恰是以职业身份为标准的。比如作为一名播音员,职业要求他的心情必须按照文稿的情绪走,这是基本的角色要求。不同的职业身份,对应着不同的职责,大而化之,那叫使命;朴实具体的,那叫目标。一个编辑,置身于专业出版机构这一平台,就要明白自己的职业角色,找对自己的水平线。职业身份的强调,即有一种职业修辞,比如,作为职业编辑,在出版分工上代表着权威和专业。可以说即便编辑本人未必权威甚至并不专业,但是职业角色要求你必须“表现出”权威的样子,这就是职业修辞。职业修辞是职业风貌的一种体现,要做到表里一致,就需要强化编辑的专业素养和表达能力,要提高职业技能,进修专业知识。而职业素养的要求,是不断调整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思考方法,从而去匹配你的岗位角色,契合度越高则专业素养愈为深厚,所谓人自治而后治人。
第三,职业深情。所谓“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精”,职业主义的态度,不管是科学、技术或工艺,从业者都要有优良的职业精神——有热情、真情乃至痴情,这是职业化的内在要求。那么,出版业既是文化行业,也必有文化业的特殊之处。它融合了人文意义上的职业深情,可以让职业主义变得有投入感和归宿感,可以让从业者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爱岗敬业”,什么是“职业精神”。对很多从业者而言,进入出版社做一名编辑,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在个人的职业选择中,也许只是将就着凑合,可是就算是凑合,也各有凑合的方式,凑合得好,也许惊喜不断,因缘美满。此中惊喜由来,缘在深情系之。申说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三个人在工地搬砖,有人明知故问,你们在做什么啊?第一个人漠然答道,你没看到我在搬砖么?第二个人态度平和,说我是在砌墙盖楼。第三个人则神采焕发,说我这是在建设家园。这个故事里,“搬砖”可以替换成任何别的职业内容,我们从中可以读出职业态度和事业精神。因职业深情之故,可以明晓“爱”之发自肺腑,“敬”之浸润人心。
第四,职业贡献。呼应前文提及的“一个行业缺乏中心思想”,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编辑出版职业的专业性、公共性和自治性特点,以此明晰自我,更好服务他人。所谓专业性,编辑出版是一门专业活动,作为编辑自己应该有一个职业认知,据此区分内行与外行;所谓公共性,出版本身是公开活动,必然有一种交叉参与,顾及新闻、媒体和社会的种种评价,要方方面面考虑如何引起兴趣与关注;所谓自治性,涉及职业分工的专业事务,职业出版人应当划出无形的界限,据此将各流程的分工内容具体化、数据化并实现可控化。
作为专业分工的特定酬谢,职业贡献要依托职业自信和职业自律。比如,职业出版人当有效率意识和增量意识。职业编辑与作者,亦师亦友,唯有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方能做到事实上的“教鱼游泳”。在数字出版高调现世之际,我也曾认真思考数字时代的编辑该怎么做,尤其是直接从事数字出版的从业者,倘若仅仅是审查一下网上作品的政治性、纪律性问题,是否就可以号称“数字出版”了?无论是传统还是数字出版,作为职业编辑,我想应当提供专业而不可替代的服务,这是与众不同的立身之本。所谓“最好的编辑”,代表的不是数量意义上最多的编辑或最少的编辑,而是编辑工作到了什么程度才能让一部作品的价值表现力度和传播效应达到最大化。
古人说“君子不器”,今人道“古人诚不我欺”。大道贯通,回到“搬砖”的小故事,可知不同的回答源于不同的职业认知、不同的职业心态和不同的职业追求。第一人,是极不情愿而迫不得已,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职业,但是眼下除了搬砖别无可搬;第二人,是标准的“人各有价”的职业主义者,他知道自己在砌一堵墙,这堵墙是一个局部成品,他的作为要对得起他的身份和待遇,他的态度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至于第三人,我们说,他怀抱理想,步伐坚定,很好平衡了现实与梦想,他是得其所哉,他是所谋远大,对于别人而言是职业的态度,对于他则是终生的事业投入感。这种人很了不起,因为他尊重本职,瞩目专职、理解天职,他因理性和效率,在达到一个又一个目标的基础上,使其使命感得以成全,境界至此,也就超越了时下所谓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