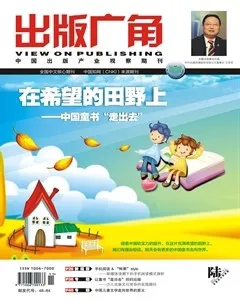泥巴上的辉煌
2013-12-29半夏
文字作为文明的火种,对人类的意义并不亚于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真火”,或许更是“真火”。不过,文字自产生之日起,便存在一个载体的问题。讯息的传播,只通过缺乏留暂的声音就太过窒碍了,必须通过记录在某个东西上面,才可以跨越空间和时间。这其实正是文字产生的缘起,也是之后书诞生的缘起。
文字和书从诞生之日起,便必须以物质的存在为依托。在石头、竹木、骨头、树叶树皮之类自然形态上刻画文字,当然是最方便的记录。而其中最富时间穿透力的,该是石头。这就无怪秦始皇要到处刻石立碑,他的立意也许在于自家王朝千秋万代的传扬,不料秦祚竟然如此短促,简直类同反讽。不过,那些刻在石头上的铭文,却真的传承久远。甚至比文字更为久远的人类印记,也都因为摩刻在石头之上而留存下来。
不过,石头的死穴在于它的质量沉重。相比之下,木头、竹子、骨头、树叶树皮当然更为轻便。但考古学的发现却证明,更早的文字载体或曰书的形式,却并非方便之物。在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生活着苏美尔人,他们创造了绚烂的文明,而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成就,便是他们的文字。苏美尔人大约在公元前第4千纪末期创造出来的楔形文字,是Kxm3dTZUmS3smd8liwxNVg==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意味的是,承载这种文字的主要载体,是绝不轻便的泥版。
泥版书的制作方法是:用粘土制成每块重约1千克的软泥板,然后用芦苇杆或者削成斜尖的木制笔在软泥板上刻划文字,文字刻划之后放在阳光下晒干,再放入火中烘烤。一部泥版书包括若干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和带有标记可容纳这些泥版的容器。木架是其中的一种容器,泥版按顺序放在木架上供人使用。
其实楔形字正诞生于泥版。早期的苏美尔文字原本是以图形符号为主,后来因为要在软泥板上用尖头的硬笔压刻文字,落笔处略略深宽,提笔处略略细窄,于是符号都变成一头粗一头细的短线条,因为形似楔子,所以得名。因又像钉子,也叫钉头字。而作为书的早期形式,鉴于它善存于泥版,所以就叫泥版书。
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楔形字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特殊的渔猎生活方式,但也有观点以为源于苏美尔地区发达的社会组织,为了行政管理,需要比较有条理的通讯。楔形字当然可以书写在泥版之外的载体上,譬如石碗和权杖,但这些坚硬的材料适合留存却不方便书写,所以只好在不计成本的王室中流行。而已经发现的大量楔形字文献,则基本都是泥版的形式。说苏美尔文明的辉煌建立在泥巴上,也许并不为过。
早期的泥版是圆形和角锥形,不方便书写和存放,于是才改为方形。烧制的泥版书蛀虫奈何不得,也轻易不会腐朽,面对竹木缣帛羊皮乃至纸张都惧怕的焚烧,经历“火其书”制作而成的它也不那么脆弱。但可以想象,每块1千克的重量,搬动起来必须花费相当的气力,在已发现的近百万块泥版中,最大的尺寸为2.7米长1.95米宽,足有5米多见方,无疑是狼犺的大部头,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真是贴切。这也让那个时代的阅读,成为一件颇不轻松的体力活。尽管如此,楔形字在西亚地区流行了3千年,还成为埃及和两河流域各国外交往来书信和订立条约的通用文字,看来耗费体力并没有成为它存在的短板,也许那时候的需求,有比体力更重要的元素催动。
苏美尔文明的辉煌时期的确有不少神话、史诗、寓言和王室赞歌,所以方文山老师想象的“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占据泥版书更多内容的,则是法规、讼案、遗嘱、账目、契约、收据、书信等干巴巴冷冰冰却相当实用的枯燥记录。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图书馆,是亚述巴尼帕国王在尼尼微建造的,内中收藏大量泥版书。据说国王身边网罗了许多精通楔形字的人才,专门预测国王和国家的威胁。想来那时的国师未必懂得如何拉动内需,却必须是文字功力深厚的学问家。
现存巴黎卢浮宫名头十分响亮的《汉谟拉比法典》,也是用楔形字写成的,它是世界上迄今完整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法典,不过它的原文刻在一座黑色玄武岩石柱上。这也是楔形字书写不止于泥版的例证。不过之所以刻在坚硬的石头上,用意则在于方便传播,本土也有将经书刻石的类似例子。
泥版书的制造与使用延续至公元 1世纪,现存最后一块楔形字泥版是公元后75年的遗物。它被羊皮书所取代——看来不方便该是压垮它的最沉稻草。载体真的能够决定文字的诞生流布以及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