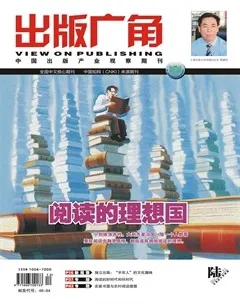农家书屋与农村阅读理想田建平
2013-12-29王静欣
全民阅读推广计划中,6亿多农民显然占据全民的绝对主体。从某种意义讲,全民阅读计划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6亿多农民的阅读。
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至今犹是。农民作为中国农业生产力的主体,从夏商至晚清乃至近代,一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地位。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农民诚然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得以翻身,但是在城乡经济“剪刀差”的经济背景下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出了巨大的劳动贡献。2000多年来,中国农民既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还要从事自身——人口——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句顺口溜,几乎可以视为中国农民的一种生存理想模式。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传统农业社会急剧解体,工业消费社会与商品社会主导与支配下的新型农村社会正在形成。不同地区的农村社会呈现为差异化的发展区域态势。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传统差异在巨量融合中呈现出碰撞、交锋、转化、模糊等多重矛盾及其复杂景象。例如华西村,经济上早已不是习惯定义上的农村,实际上已是一座城市。再如西部一些偏远地区,经济仍然落后,村民子弟上中小学都很困难。
“农家书屋工程”的一切意义及其实施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实际阅读效果,甚至成败与否,都直接决定于这一历史背景。
农村人口、教育与阅读推广
农村人口一直是中国社会诸阶层中数量最大的。封建社会,农村人口作为“编户齐民”,主要是国家征收“租庸调”的主要对象。封建教育主要是贵族教育、封建精英教育,对广大农村人口主要实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及愚民政策。把农民摆在教育主体地位上、思想上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它是直接同中国社会近代化密切相关的,或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主要议程。近代有识之士,如晏阳初、陶行知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根本进步,特别是文化上与政治上的进步,必须改变传统的农村社会,而又必须从对农民实行新式教育入手。中国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意识、理想及做法至今仍然值得重视、继承与实施。6亿多的农村人口,构成了全民阅读数量意义上的绝对主体。所谓全民阅读,如果农村人口做不到,显然不配称其为全民阅读。
出版转型、危机与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工程”的提出,事实上是以出版转型、危机及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为背景的。传统出版由于新技术、新媒介的挑战,危机四伏,急剧衰落,正在向数字出版转型。同时,传统阅读(文本阅读、纸本阅读、经典阅读)也大幅跳水,国民(传统)阅读率一度持续下滑。国民阅读率下滑导致传统出版危机日深,前途茫然。其实,国民阅读率下滑也可视为传统出版危机的一个主要方面(或表现)。当今,在城市阅读、大学校园阅读尚且明显下滑的困境面前,更遑论农村阅读!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版界才真正“发现”了广大的农村,“发现”了6亿多农村人口,发现了这个广阔无边的巨大阅读市场。出版危机似乎有望借助于这一巨大市场得以化解并振兴。遗憾的是,出版界很快就发现,这一巨大的市场主要是理论意义上的一个市场,或说主要是一个概念。
简言之,由于几千年来的历史原因,中国农村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阅读生活方式,更毋论普遍的阅读习惯。占农村总人口一小部分的广大中小学生,实行的是非常实际的应试教育,一时也不可能改变整个农村的非阅读生活方式。“发家致富”才是农村社会的普遍主题,打工潮、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传统生活方式及休闲方式(打麻将、聊天、看电视)、征地、占地、自然资源私有化诸方面,更使得农村社会的阅读力量显得十分苍白、孱弱。
出版界应当明白,广大农村——6亿多农村人口并不意味着一个等额等值的阅读空间——阅读市场。换言之,中国农村这一巨大的“阅读空间”——“阅读市场”,是需要研究、培育的,是需要长期作出无私奉献的,而这又是一项持久的艰巨任务。也许,把广大农村理解为一个阅读“市场”本身就是错误的。
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与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将“农村书屋”合理置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城镇化规划中,应当设置一个阅读空间,把“农家书屋”置于其中。新农村建设、农村城镇化的一个基本做法是农村社区化,每个农村社区均应考虑设立一个农家书屋。在此,“农家书屋”这个名称也可以加以变化,不一定全国农村社区都以“农家书屋”命名,也可以命名为“农村社区阅览馆”,或以“农家书屋工程”为据起一个有地方社区特色的本土化名字,这样做似乎更接近当地农民的心理。再者,“农家书屋”这一名字,似乎有意将城市书店与农村书店,将城市阅读与农村阅读的差异凸显出来,实际上有暗示农村文化落后的消极影响。农村社区“农家书屋”的具体命名,完全可以同当地农村的地名文化、地理文化、风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结合为一,甚至可以在当地村民中征集名字。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农家书屋”,就可以考虑以民族语言加以命名。
将“农家书屋工程”统一列为新农村建设、农村城镇化、社区化建设的必要项目,有利于保证农家书屋的公共空间、设备设施、阅览条件、人员配备、日常管理诸方面的正规化建设,从而避免出现诸如条件简陋、缺乏管理等弊端。
困境、新媒体与阅读行为
在全球传统阅读出现停滞乃至下滑的现实背景下,开展“农家书屋”建设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既有农村阅读落后历史语境的挑战,又有全媒体时代传统阅读陷入重围的现实语境的挑战。笔者在2013年5月初以“农家书屋对农村、农民阅读的作用、影响”为题对30多名大三学生作了一个书面调查,所得结论主要集中在“困境”“存在问题”“建议”三方面。笔者选取了一些学生在调查中有代表性的结论:
由于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的思想意识,因而大多数农民还没有从思想意识上完全建设起对图书的信任或信心。一般情况下,他们处理农业及相关问题都依靠以往形成的经验。
——代幸梅
每日的体力劳动使得他们大部分人不会去借书阅读,电脑的普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发展,让他们更倾向于每日劳动回家后去轻松娱乐,电视剧、电影等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的媒体比那些字迹密麻的书籍更加具有吸引力。
——宁瑞雪
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多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及儿童文化层次偏低,兼之儿童每天上学,因此书籍事实上很少人真正去读。
——刘甜甜、谭梦娜
那些真正身处偏僻山区、交通闭塞的农村还没有书屋的建设,图书更新建设慢。
——程诚
很多南方(如安徽)农村都把土地“出租”给外来投资者(如浙商)开工厂(如服装厂),我们家乡(安徽马鞍山一带)就有农村变成“马鞍山服装工业园”。农民要么是外出打工,要么是进附近服装厂工作。农村的性质在变化中,农家书屋也应当与时俱进,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引进图书,如我们那里可引进与法律有关、服装、城市变化方面的书。
——汤丹丹
调查还反映出诸如借阅率低、缺乏管理、面子工程、书籍种类少等具体问题。上述所有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从而制定出针对农村各种实际情况的“农家书屋”实施细则。笔者认为,推进农家书屋工作,目前应特别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新媒介对书籍媒介的替代是必须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村实行的电视“户户通”工程、三网融合,以及电脑正在急速占领农村青年人精神空间,实际上使得“农家书屋”的阅读设计方案一开始就置于一场“媒介战争”之中,并且必然处于下风。因此,“农家书屋”的建设必须与农村其他媒介的建设联系起来设计,如电视、网络中似乎也可以开办“农家书屋”,引导农民阅读。
第二,农家书屋应与农村中小学教育统一设计。可以考虑将“农家书屋”设在中小学校,由中小学生义务管理,阅读对象既包括中小学生、教师,也包括其他农民。偏远落后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等,条件特别艰苦的地区应当列为“农家书屋工程”的重点地区。让图书资源使用在最缺乏最需要的地区。
第三,县乡村三级基层政府书籍阅读考核制。农民阅读的推广,不能仅只停留在一种统一政策的层面上,必须由县乡村三级基层政府首先落实,政府人员必须首先成为阅读者。试想,县乡村政府人员不读书,村干部不读书,怎么叫广大普通农民去读书?农民阅读推广切忌成为一种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一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第四,青年志愿者工程。可以考虑由国家有关方面设立青年志愿者队伍,由大学生乃至研究生利用假期志愿投入“农家书屋工程”,开展实际阅读促进工作。也可以考虑将“农家书屋工程”工作纳入国家其他青年志愿者工程工作范围,并制定相关政策加以促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署领导出版界(学界、业界)制定由总署、省市县出版管理行政部门、出版界共同组成的协作机制,可由高校编辑出版专业选派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工作。
国家大力推广“农家书屋工程”,促进广大农民阅读书籍,其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农村的历史传统、急剧发生深刻变化的农村现实、新媒介的巨大挑战及现实替代,不可否认是造成阅读困境的三大因素。
全民阅读推广计划中,6亿多农民显然占据全民的绝对主体,从某种意义讲,全民阅读计划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6亿多农民的阅读。“农家书屋”作为全民阅读推广计划——广大农村地区、农村人口阅读的专项工程,可谓意义伟大、困境重重、使命神圣、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