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自助出版在中国的前景
2013-12-29刘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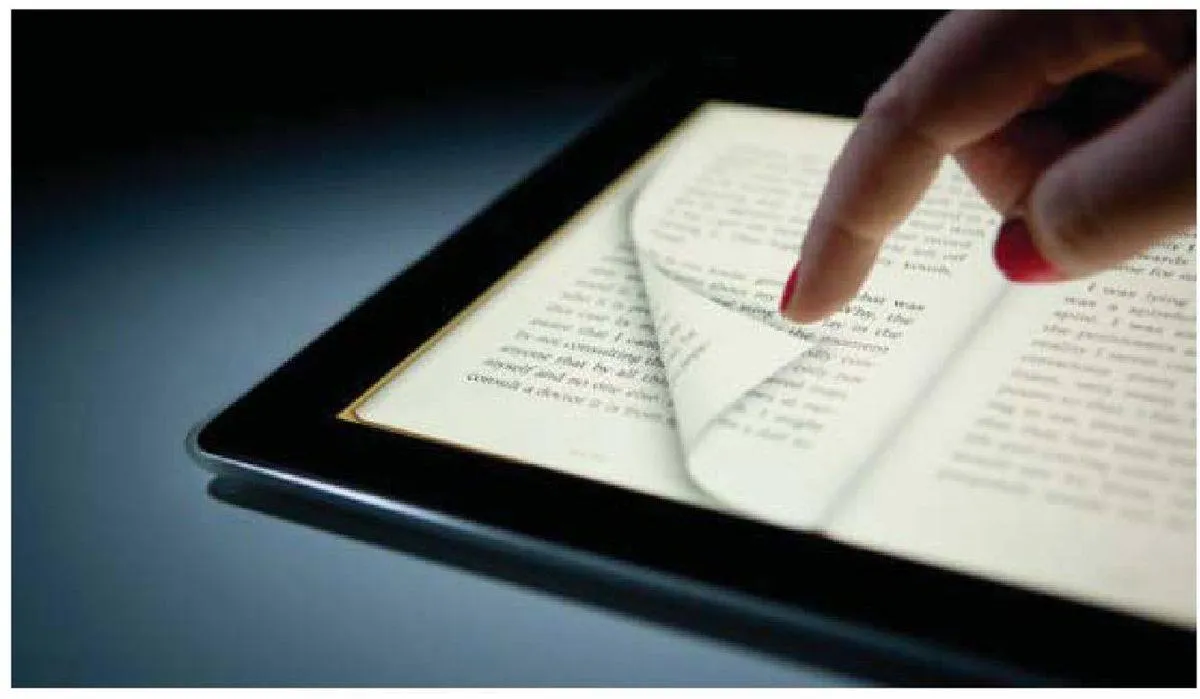
[摘要]数字技术促使自助出版在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繁荣,但其同时又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西方意义上的自助出版和我国的出版政策不同,但从技术和实践的发展来看,一些在线出版活动已经具备自助出版的内涵。在分析我国出版制度和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中小型出版社的数字化前景,提出适合我国数字自助出版的可行模式。
[关键词]自助出版;数字出版;出版流程;中小型出版社
[作者简介]刘荣,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委托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课题“当前社会条件下数字出版的双重效应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自助出版(Self-Publishing)是指作品不经过出版机构,利用社会资源自行编辑、印刷、发行图书的出版模式。自助出版者绕过了经纪人、出版社等垄断壁垒,直接同图书设计师以及印刷商、发行商打交道。相比传统的出版模式,自助出版需要较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并且存在更大的市场风险,但可以获得作品的全部盈余收入,并可以把握作品更多的控制权,因此自助出版在西方国家对作者颇具吸引力。而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以及其具备的经济优势,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自助出版的进一步繁荣。
一、数字自助出版在西方国家发展现状
1. 优势突出,数字自助出版风靡西方出版界
自助出版在西方发生、发展由来已久。以美国为例,许多著名作家或者社会名人如马克·吐温、理查德·尼克松都曾进行过自助出版。自助出版的常销书如《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的》曾22次修订出版,发行500万册,为作者赚取了巨额版税。数字技术是自助出版发展的催化剂,据美国出版业调查机构R. R. Bowker估计,得益于数字出版技术,美国自助出版的图书由2006年的51237种激增到2010年的133036种,增长了160% [1]。
数字自助出版解构了传统的出版流程。传统出版的流程为:作者→出版社(编辑、印刷)→书店(发行)→读者。而数字自助出版的流程为:作者→技术商/平台商→读者。相较传统的出版模式,数字自助出版具备突出的三大优势:一是缩短出版周期。这得益于数字技术和自助模式减少出版环节而产生的双重功效。二是降低出版成本。因为缩减了图书出版的产业链,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特别是数字技术节省了印刷和发行的成本,而这两个环节的成本构成了印刷时代自助出版者最大的成本投入。三是降低出版门槛。数字技术和自助出版模式的结合使普通人一圆出版梦。
数字自助出版的明显优势使其在西方受到热捧,其中以亚马逊的KDP系统(Kindle Direct Publishing)为典型代表。在KDP模式下,任何人都可以向亚马逊提交作品并定价,并由数字出版平台制作成电子书,直接向消费者出售这些作品,亚马逊从中抽取相应的版税。KDP出版模式不但绕过了出版社,而且绕过了发行商,由作者直接将作品销售给读者,节约了作品在流通领域的成本,极大地体现了数字出版的优势。因此,KDP自助出版作品的售价,不但大大低于传统纸质书,而且低于一般电子书,价格竞争力非常强。在该模式下,作者通常能获得70%以上的版税,远远高于传统出版的十几个点。在美国,KDP已经吸引了众多作家。在《纽约时报》发布的2011年十大年度畅销书排行榜上,KDP自助出版的作品占了两部[2]。
2.“数字+自助”模式的负效应
数字自助出版在西方蓬勃发展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主要表现为图书质量下降和侵权抄袭现象泛滥。
(1)图书质量下降。自助出版之下,作品不经过出版机构的筛选和编辑,直接借助数字出版平台推向市场。而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这决定了自助出版图书内容同样参差不齐。除了内容,许多自助出版图书从封面设计到排版,品质都很糟糕。这是因为KDP等数字出版平台本身只是作品的整合平台,而非作品的编辑机构,自然无法保证图书的质量。同时,因为数字自助出版的便捷性和经济性,面世的图书品种数量急剧增长。海量的图书品种加之绝大多数自助出版图书的作品都是名不经传的作者,读者根本无暇选择,真正优秀的作品要想脱颖而出非常困难。这和传统出版时代,出版社和名作品的品牌效应相得益彰形成巨大反差。
(2)抄袭痼疾加剧。在传统出版时代就令出版人头痛的抄袭和盗版现象在数字出版时代进一步加重。数字技术给抄袭和盗版提供了极大便捷,而互联网又给抄袭和盗版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源库。在美国著名的自助出版平台上,无论是亚马逊的KDP还是巴诺的NOOK,抄袭他人作品,然后改头换面在平台上销售的现象都在愈演愈烈。虽然平台商也采取类似高校使用的反抄袭软件,试图对内容进行原创把关(这些反抄袭软件的工作原理是将提交的文档与现有作品数据库进行比对,将高度重合的成段字符标出来),但无法对创意和构思的原创性进行判别,因此甄别效果欠佳。同时,有的作者利用网络的互动性,将自己作品的开头部分上传互联网,鼓励其他网友续写或者改变自己的作品,将其中精彩的部分作为自己的原创编辑成完整作品,在数字平台上销售。这种抄袭方式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对反抄袭制造了难题。
二、在中国发展数字自助出版的可行性分析
1. 自助出版,当前我国出版制度的禁区
无论是传统的自助出版还是数字化自助出版,都和我国现行的出版制度相抵触。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第2章第9条明确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而出版单位的设立,除了有主管和主办机关、固定资本、工作场所和专业人员的限制,还应当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因此,从制度的角度说,《出版管理条例》已经将个人直接进行出版活动的可能性排除了,自助出版也就无从谈起。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通过互联网进行包括出版在内的信息传播活动已经成为常态,因此,出版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作为《出版管理条例》的下位法规,对于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除了重复后者对出版主体的规定,又额外规定进行互联网出版活动必须申办《互联网出版许可证》。虽然网络传播实践的发展,已经使互联网出版主体超越了原先传统出版时代仅限于国有事业单位的范围,许多社会资本也可以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但对个人借助互联网进行出版活动,仍然没有松口,亦即从事互联网出版,只能是“法人”,而非“自然人”。
2. 盛大模式,自助出版的寄生式存在
盛大文学是当前中国网络文学内容提供商的领导者。通过收购和兼并,盛大文学掌握了国内网络原创文学90%以上的内容资源[3]。盛大文学的成功,在于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盈利模式:作者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盛大旗下文学网站的公共阅读区,供网友免费阅读,当点击数达到一定标准后,盛大将该作品加“V”,开始按每千字2分~5分钱的标准收费,盛大通过预先协议与作者分享利益。由此,盛大文学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换的过程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不仅颠覆了传统出版业的运行模式,更是世界数字出版领域的一次创新。
首先,盛大模式是符合我国互联网出版政策的。盛大持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具有互联网出版资格,盛大必须对作者上传的作品内容负责。其次,盛大模式又具备了自助出版的精神内核:降低出版成本,可以让作者的作品自由面向读者。同西方国家的自助出版模式相比,盛大也有独到之处:无论是传统自助出版,还是亚马逊的KDP数字自助出版,作者都必须有相当的前期经济付出;而盛大模式下,作者付出的成本更低,基本可以做到零成本。因为作者必须借助盛大的平台在线发表作品,我们可以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寄生式自助出版。
盛大的寄生式自助出版模式下,作者付出成本低廉,适合刚入行的作者。对于成名的职业作家来说,其弊端是明显的:利润分成作者只得50%,明显低于西方自助出版70%版税的比例;作者必须转让给盛大全部的版权,缺乏自己作品的控制权;甚至在点击量的统计上,双方也会产生争执[4]。对于后者来说,更适合的是西方模式的数字自助出版:发行单行本电子书,或者POD纸质图书,自己控制全部的版权。但是如前文所述,这种典型意义的自助出版与我国的出版政策相违背。
3. 数字自助出版在我国存在的可行方式
西方模式的自助出版和我国出版政策相抵触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出版主体不是法定的出版机构,而是独立的自然人。而绕过出版机构的壁垒,又是自助出版的出发点,两者似乎天然不可调和。但如果从规范数字出版的健康成长方向和协调出版活动参与者各方利益的角度来看,两者并非完全水火不容。虽然结合的产物可能会跟西方典型意义上的自助出版存在若干差异,但这种差异更多的是其成长发展的良性改进,其理由如下:
(1)西方典型意义上的自助出版,因为完全摆脱了出版机构的编辑把关,已经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顽固性问题,如上文所述的图书品质下降和抄袭成风。
(2)数字出版虽然是出版行业发展的前景,但现状是传统出版仍占行业产值的大头,即使是广义的数字出版也仅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9.5%。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决定了盛大在线出版——这种寄生式自助出版目前不可能被主流作者所接受。
(3)自助出版的出发点之一是节省中间成本,而某些环节的成本从现有实践来看,是不可或缺的,如编辑把关成本,这就为出版机构参与自助出版提供了理由。同时,从根本上说,西方自助出版排斥出版机构是因为利润分配问题,如果合理安排利润分配,两者完全可以做到相容共存。最重要之处在于这符合我国出版政策的要求。
基于以上三点考虑,在立足我国现有的出版政策基础上,同时借鉴西方自助出版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提出适合中国当前条件下的数字自助出版模式:作者在完成作品初稿之后,将书稿以外包的形式交给出版机构编辑审核,合格作品由出版社给予书号,由作者提交数字出版公共平台发行数字图书(这种数字出版公共平台可以是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所设想建立的数字出版的国家级平台,也可以是社会资本建立的商务平台),或者POD印刷发行纸质版图书。
从表面看,这种模式和现有的出版模式从流程来看别无二致,但本质上该模式下作者和出版机构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意义上,出版机构仍然是出版主体,需要对作品的社会效益承担责任;但在经营上,作者承担主要的市场风险并收获市场回报,出版社以外包形式获得作品的编辑把关业务,并收取佣金。该模式亦不是社会资本参与出版业的现行模式(如文化公司从出版社购买书号进行出版活动)的简单延续,而是结合我国出版业实践现状和数字化发展前景,统筹出版流程各参与方利益和社会综合利益的一种理性安排。
出版业尤其是数字出版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非常容易形成市场寡头垄断。在我国,因为出版业参与上层建筑的构建,而又添加了更多行政垄断的色彩。垄断经营者会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采取各种手段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支配产品价格、压迫产业链其他环节的企业等。这些都曾在出版业特别是数字出版领域发生过。同时,可竞争性理论(Contestability Theory)又告诉我们,如果市场是开放的,垄断经营者会因为担心过高的垄断得利吸引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使价格等各种市场要素维持在一个基本合理的水平上。自助出版正是这样一个可能的、维持出版市场公平环境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最佳候选者,因为它可能是每一个个体的公众,是力量无穷的汪洋大海。
[1] 文靜. 自助出版赚得更多[N].广州日报,2011-12-08.
[2] Secret Of Self-Publishing: Success [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11,2011.
[3] 杨柳,徐昊. 出版业后数字化时代[J]. 数字商业时代,2012(9).
[4] 邹玲.盛大文学之步步惊心[J].中国企业家, 20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