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的NONSENSE
2013-12-29孙建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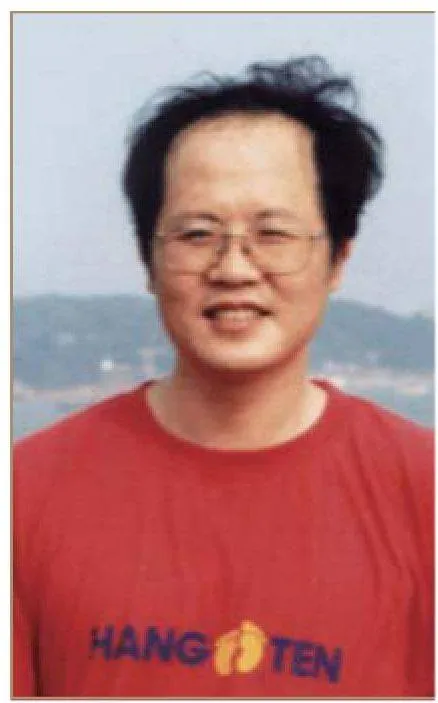
孙建江,学者,作家,出版人。主要出版的学术著作:《童话艺术空间论》《文化的启蒙与传承》《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意大利儿童文学概述》《童年的文化坐标》等。
我一直认为任溶溶的存在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幸事。
任溶溶生于斯长于斯,当然承续了中国文化的“载道”传统。在他创作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其间的“载道”意识。这方面,他与我们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没什么两样。但我想说的是:第一,任溶溶是一位天生的、难得一遇的儿童文学作家。具备儿童天性的作家,与儿童读者往往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天然的默契感,往往能更准确地把握儿童文学的精髓。任溶溶对儿童的热爱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在他那里,为儿童写作是非常自然和非常快乐的事情。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驱动力。对于他,为儿童写作除了使命感,更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渴望和享受。第二,作为一位通晓英、意、俄、日四种外语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任溶溶显然比其他的儿童文学作家更具有儿童文学的国际视野。他熟稔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的艺术范式、叙述手段、呈现方式。他更容易看出中西儿童文学之间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观察、审视、品评作为人类文明物儿童文学的全球化趋向及其内在质地。
正是这两方面的优势,使得任溶溶多了一份很多人所不具有的特质——儿童文学写作的纯粹性。生活中,任溶溶是一位幽默风趣、童心永驻的人。好多年前,我陪任溶溶先生去广州参加一个安徒生诞辰两百周年庆典活动,班马教授前来探访,我和班马当着任先生的面开玩笑说:“任先生啊,您好像本来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呢。”任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这话的意思是说像任先生这样才华出众、满腹经纶又天生乐观通达、玩性十足、真正富有童年精神的人在中国实在不多。
任溶溶曾说:“我天生应是儿童文学工作者。根据我的性格、爱好,我应该做这项工作。”为儿童服务,为儿童写作,可以说几近是他的生活乐趣之所在。他的这种天性和他的国际视野,使他对外国儿童文学中尤为强调注重的nonsense(有意味的没意思)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感和认同感。他认为,nonsense是一种童趣。这种童趣,小读者无师自通、心领神会,而缺乏童心的人是永远无法领略其间的奥妙。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任溶溶为什么特别喜欢,或者说特别热衷于“形式”和“有趣”。
在任溶溶的创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他对汉语语词的活用、巧用和妙用。比如,对“大”和“小”、“胖”和“瘦”、“高”和“矮”、“少”和“多”、“新”和“旧”、“长”和“短”等对比词性的组合运用。比如,对叠词、谐音字、绕口令的音乐性展示——《我牙,牙,牙疼》《这首诗写的是我,其实说的是他》《请你用我请你猜的东西猜一样东西》。比如,对汉字视觉美的构筑——《大王,大王,大王,大王》(按,字体从特大号到最小号)、《大大大(按,字体大号)和(按,字体中号)小小小(按,字体小号)历险记(按,字体中号)》。
像诗作《一支乱七八糟的歌》,并没有讲述什么“意义”,写的仅是“乱七八糟的歌”产生的过程,却非常好玩和有趣。三岁零两个月大的女孩不仅整天 “咪——多”“多——咪”, 乱七八糟吹口琴吹个不停,还执意让小舅舅唱歌,自己口琴伴奏。“她使劲地吹啊吹啊,/越吹她的劲头越大。/我也唱了/——不,叫了——/半天的歌。/不知唱了/——不,叫了——/一些什么。”结果可想而知:更加“乱七八糟”。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能够欣赏这节目的,/恐怕只有我们两个。/不错,/是支乱七八糟的歌,/不过唱得实在快活”。说得好,唱得实在“快活。”这就是儿童与成人不同之所在,这就是童趣,这就是作者的nonsense。尤其难得的是,任溶溶作品中很少有什么“成人化”“大道理”“疙里疙瘩”的问题。任溶溶讲述的大白话小读者都看得懂。这种大白话是经过精心挑选和打磨的,因而大白话中又巧妙地隐含了作者的nonsense意味。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并不认为任溶溶的创作、他的那些“形式”和“有趣”对中国儿童文学有多大的意义。既有的数种以作家为线索的儿童文学史,虽然对任溶溶有所论述,但重点多落在其译作的成就上。其实,任溶溶的创作绝对是超前的。他的儿童文学观明显超前于他的同时代人,甚至超前于诸多后辈儿童文学作家。可以说也正是因为这种写作的纯粹性,使得任溶溶的作品跨越了时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任溶溶的这一超前性其实已存在有相当时间了。惜乎一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反省和深思。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任溶溶的意义会愈加显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