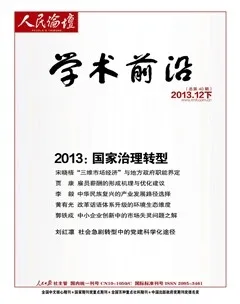改革话语体系升级的环境生态维度
2013-12-29黄有光

【作者简介】
黄有光,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经济问题、福利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
主要著作:《福利经济学》、《经济与人生》、《经济与快乐》、《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等。
摘要 经济高速发展而人们满意度相对低下,什么是今后中国应有的发展方向?笔者提出以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替代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家(以及各省县)的主要成功指标。本文也讨论与此指标有关的一些话语,包括快乐、幸福、福祉等。它们之间有没有差别?为什么偏好使用“快乐”?从快乐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出什么政策含义?如何以“轻度家长主义”的方法增加人们的快乐,而避免弄巧反拙?
关键词 转型 经济发展 环保 快乐国家指数
在中国,自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世界有目共睹。201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38420元,较1978年增长了16.2倍,年均增长8.7%。这样的成就在人口基数这么大的国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然而,现在中国的人们是否满足?是否快乐?社会是否和谐?是否稳定?中国能否长治久安?可否实现继续发展?即使是像笔者这么天生乐观的人,也不敢排除负面答案的很大可能性。造成如今生产消费大量增加而人们不满、不快乐,社会不很和谐的原因,以及其解决方法涉及的因素很多,包括环保、收入分配、权力的滥用与贪污、制度、道德等。笔者针对今后改革的应有方向,以及有关的改革话语体系问题,提出应该以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替代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家(以及各省县)的主要成功指标。本文也讨论与这个指标有关的一些话语,包括快乐、幸福、福祉等,以及一些政策含义。
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
对于快乐的心理,社会学与经济学者们近几十年的研究所得出的相当一致的一个结论是,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高的消费并不能,至少不能显著地增加快乐,尤其是在全社会的范围而言;个人可能可以通过相对地位的提高而略微增加快乐(Diener等,2010;黄有光,2013)。这个发现显然指明,至少在达到小康之后,不应该再用GDP或GNP(国内与国民总产量)为主要的成功指标。Borghsi & Vercelli(2012,212页)认为“真正的悖论是还在坚持使用GDP为人们幸福的主要指标”。因此,类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总国民快乐)等基于快乐的指标的提出非常必要。以GNH替代GNP,是以快乐替代产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中国国内近几年来对这类指标的提出与讨论,是令人振奋的。笔者也很喜见国内经济学者(如于席正、江莉莉,2012)对快乐问题的讨论。
然而,作为比较精确的指标,GNH是不完善的。GNH是总国民快乐。我们应该极大化的不是总快乐,而应该是净快乐。其次,一个国家如果极大化当年的GNH,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以及将来的人们造成危害,比如对全球环境造成破坏。因此,笔者(Ng,2008)提出比较容易接受的(尤其是每年度)国家成功指标——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缩写为ERHNI,“娥妮”)。“娥妮”主要为音译,但也取“娥妮”(美丽女孩)的美好意义,因此,ERHNI是美好东西的指数。
只是一天快乐,马上死去,肯定不好。因此,长期研究快乐的知名学者Veenhoven(1996,2005)提出“快乐年数”(happy life years)的概念。比如一个人的快乐年数=平均快乐×生命年数。如果平均快乐(满分为1)等于0.7,生命年数为80,则快乐年数等于56。
然而,如果一个人评价自己的快乐指数是0到1中的0.5,通常只是勉强及格,总快乐量与总痛苦量大致相等,净快乐约等于零。简单起见,不考虑对他者与对将来的影响。与其有情况A:0.4的平均快乐指数(净快乐等于负的),而长命200岁(很长的受苦生命),得到等于80的快乐年数,不如有情况B:只活80岁,而有等于0.8的平均快乐,虽然快乐年数只有64。因此,这种计算法的快乐年数有误导性。
笔者认为应该以净快乐取代快乐,只算0.5以上的快乐量。根据这修正了的净快乐年数,上述情况A的净快乐年数是负20【(0.4-0.5)×200】,而情况B的净快乐年数是正24【(0.8-0.5)×80】。
考虑到该国对他国与将来的影响,因此,计算每个国家的平均净快乐年数,必须扣除这国家的人均环保(对他国与将来的)危害,才得出该国当年的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因此,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娥妮)=平均净快乐年数-人均环保危害。
由于必须使用相互可比的数据(包括快乐与危害之间),因此上述指数的计算并不简单。不过,正如笔者(Ng,2008)论述过,娥妮是可以计算的。笔者与研究员梁捷博士也正在进一步(在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资助下)改善娥妮的计算与快乐的调查方法,使它更加可靠,可以进行人际比较。
如果用娥妮取代(至少是补充)GDP,就能够使人们与各国政府比较注重真正有利于提高人民的长期快乐的东西。例如,政府就应该更加重视避免“高速公路变成停车场,然后又变成垃圾场”(2012年国庆长假出现的情形),而不只是重视汽车的产量。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问题,例如环保、平等、食品安全、和谐、清廉、道德等。
对世界各国提出以娥妮取代GDP,大致是正确的(将来还可以进一步考虑通过科技、文艺、战争等对他国与将来的外部作用)。但从一个国家本身来看,邓小平强调的综合国力,也是重要的。虽然快乐会促进和谐而增加国力,但GDP也有相当大的贡献。因此,在还没有达到或接近世界大同时,不能够单单看当前的快乐,还要维持与增加综合国力。因此,对于本国而言,还只能用娥妮作为主要而不是唯一指标,补充而不是完全取代GDP。
幸福、福祉、还是快乐?
人们习惯上倾向于使用“快乐”来指当前的快乐,而使用“幸福”来指比较长期的快乐。福祉或幸福也是比较正式的讲法。给定同样的时段,不考虑讲法的正式与否,则快乐(happiness)、福祉(welfare)、和幸福(subjective well being)都是完全同义的词。如果某人当年几乎每天的净快乐量(快乐量减去不快乐或痛苦量)都是很高的,没有很痛苦的时候,则他当年是很快乐的,也是很幸福的,当年的福祉也是很高的。
英文的快乐(happiness)与中文的幸福的概念的历史演变,有一个相像的地方。根据《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等权威文献(详见Oishi,2010,38页),几百年前(1530)“happiness”的定义是“好运,幸运”,尤其是关于财富方面的。1591年后,开始引入“心中感受为好”的“happiness”的第二个定义。再后来第二个定义取代第一个定义。这与中文的幸福的字面上的“幸”与“福”的好运意义,以及现代“幸福”的主观感受意义是类似的。笔者猜想,这种转变可能是由于人们几百年前还在温饱水平线上挣扎时,能够在财富方面有好运,大致可以保障快乐。在温饱之后,财富方面的好运,未必对快乐有很大的贡献。
很多人(包括阿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应该排除不道德的快乐。例如一个强奸犯在某天可能因为强奸得逞而很快乐,但不能说他很幸福。笔者认为道德的问题很重要(详见黄有光,2012),但完全可以通过考虑对将来与对他者(不说“他人”,因为不排除动物)的快乐的影响来处理。那位强奸犯是把自己当天的快乐(说成幸福或福祉都无所谓)建筑在他人更大的痛苦上(多数也是建筑在他自己将来的痛苦上),因而是不道德的,是必须受谴责的。问题不在于他当天的快乐本身,而是他当天的快乐对他者及对将来快乐的负面影响。
用道德来定义幸福或快乐,笔者认为是因果倒置。用什么来定义道德呢?(道德不能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必须用其他概念来定义)笔者用快乐来定义道德。终极而言,不道德主要就是对他者快乐的负影响。可能有人会问笔者:“那你又用什么定义快乐?”快乐是一个基本概念,不必也不能用其他概念来定义,但可以解释如下:一个主体(例如一个人)的快乐是其主观感受中感觉为好的或正面的感受(positive affective feelings),包括肉体上的快感与精神上的欣慰。快乐的反面是痛苦,也是包括肉体与精神上的。(所谓肉体上的快感或痛苦,实际上最终也是精神上或主观意识的感受。强调快乐包括肉体与精神上的,主要是避免被误会为只包括纯粹肉体上的感受)净快乐是快乐减去痛苦。
在任何一个时点,一个人的快乐的强度(intensity)可大可小,可正(快乐时)可负(痛苦时),多数时间可能等于或接近于零。一个人大部分时间没有快乐的感受,也没有痛苦的感受,快乐值等于零或很接近于零。当他生病、受到伤害(肉体上或是感情上)或忧伤时,他的快乐就是负值。当他有感官上或是心灵上的享受时,他的快乐就是正的,而快乐或痛苦有不同的强度。在任何时段,净快乐量是这快乐强度在这时段中的积分。如图1所示,用横轴代表时间,正纵轴代表正快乐的强度,负纵轴代表痛苦的强度,则快乐强度可以用一条曲线来代表。净快乐量是通过原点(或零点)的横轴以上的面积(等于正快乐量)减去以下的面积(等于负快乐或痛苦量)。于是,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快乐方式,总的快乐却是一维的。
对于下图,笔者需要做几点说明:第一,快乐只包括正的或好的(快乐)与负的或不好的(痛苦)感受,不包括中性的、没有苦乐的感受,或把这种中性的感受算为零。例如,我现在可以看到墙壁是米色的,如果我对这个视觉没有正的或好的,也没有负的或不好的感受,而且此外没有其他感受,则此时的快乐量为零。
第二,快乐包括所有正的或好的与负的或不好的感受,不论是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不论是高级的或低级的,如果可以分高低的话。其实快乐本身,除了不同的强度,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在一些另外的意义上,才有高低之分。例如,某种快乐感受,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或训练,才能感受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比较高级的。
第三,快乐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为什么有些快乐或享乐方式被认为是好的,有些被认为是不好的呢?这是因为有些享乐方式会直接或间接地(例如通过对知识或健康的影响)增加将来或他者的快乐,有些会减少将来或他者的快乐。如果没有影响,或有同样的影响,则不同的快乐只有强度的不同,没有好坏的不同。
当然,不同的快乐感受有性质上的不同。欣赏音乐的快乐感受与吃冰淇淋的快乐感受,即使在时间与强度等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主观感受上的性质上的差异,即哲学家所讲的不同的qualia。然而,不论是音乐还是冰淇淋,如果给予感受者同样程度的快乐,又没有对将来或他者的快乐有不同的影响,虽然感受不同的qualia,其快乐量是一样的。人们一般会褒欣赏诗词与古典音乐或阅读的快乐感受,而贬吃冰淇淋的快乐感受,有一些原因:首先,前者一般可以通过陶冶性情或增加知识而增加将来或他者的快乐,而后者一般会通过增加体重而减少将来的快乐。其次,吃冰淇淋的快乐感受不需要通过培养,人人知道,而欣赏诗词或阅读的快乐感受需要培养,很多人对此重视不够。然而,除了对他者与对将来的快乐的影响,这些不同却没有影响快乐的总量。许多哲学家对这简单的道理依然有很大的迷惑,正像他们对快乐是唯一有终极价值的东西依然有很大的迷惑一样。(详见黄有光,2011,附录G)
为什么偏好使用“快乐”?
如果说快乐、幸福与福祉都是一样的概念,为什么笔者偏好使用“快乐”?如果严格根据笔者所使用的意义,则使用任何三者之一都无所谓,因为它们是完全一样的(在给定同样的时段)。然而,其他人对这三个概念的领会是有所不同的。笔者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或定义是纯粹主观感受的,客观因素只能通过对人们(包括现在与将来;为了叙述方便,“人们”可以包括动物)的主观感受来影响快乐,不能够直接影响快乐。这是(包括动物的)人本主义或福祉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多数人会接受“快乐”是这种纯粹主观感受的概念。然而,很多人认为“幸福”与“福祉”含有或应该含有一些比较客观的东西,例如上述对于道德方面的要求。
在此举例说明:如果张三身体健康,收入丰厚,妻子美丽贤惠,孩子听话上进等,有人就认为他是幸福的。笔者认为,这些客观因素,只是在许多情形下,有助于使此人幸福。张三是否是幸福的,要看他是否真的能够在其主观感受上有高度的快乐感受。如果他天生是悲观的,不知足的,或是后天受到某些心理伤害,使他在多数时间是痛苦的,则即使具备能够使大多数人得到快乐的客观条件,他却是不快乐的,因而也是不幸福的。
由于上述对快乐与幸福(或福祉)在主观与客观要素上的理解可能有差异,因此,使用“快乐”可以避免人们受错误的客观主义的影响,避免人们在应该针对主观感受时,不适当地混杂一些客观的因素。这些客观因素并不是不重要,而是在定义快乐或幸福时,是无关的。
其次,由于类似的原因,强调快乐可以避免一些滥用权力者使用像幸福或福祉的美丽概念,去进行一些表面上宏伟的措施,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提高人们的快乐。被误导的人们,可能还接受自己是“幸福”的,虽然并不快乐。实际上,如果不快乐,绝对不能够是幸福的!
为什么许多人偏好使用“幸福”?
中国有许多优良传统,笔者非常支持恢复或加强对这些传统的重视。当然,传统中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其中一项是禁欲主义倾向。在人口密度高而文化教育与法治水平不够高的情形下,某种程度的禁欲主义,可能对于维持社会安定有一些贡献。这也可能是禁欲主义倾向传统形成的一个原因。然而,从人民快乐的观点出发,尤其是到了现在,与其依靠禁欲,不如用加强法治、提高收入分配平等与提高教育水平等方法来维持社会安定。(详见Ng,2002)
由于禁欲主义倾向的传统,人们还有贬遏享乐的思想,把享乐主义当成洪水猛兽。其实,享乐本身是好的,应该被批判的是损人利己。鼓励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最终而言,并不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孙中山语)。“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是以服务为最终目的,而是要使人民快乐。如果服务是最终目的,则类似文革的情形,人人都痛苦地为人民服务,不就是一个理想社会了吗?经历了文革的洗礼的中国人民,更应该认识到这个谬误。
由于禁欲主义倾向的传统,人们对“快乐”还有所保留,因而偏好使用“幸福”。如果使用“幸福”比较容易被受传统影响的人们所接受,未必不是一个好策略。目标针对幸福,总比针对GDP(产量)要好得多。不过,即使使用“幸福”,应该认识到“幸福”就是长期快乐,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于2010年9月17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中,问:“什么是好的生活?”笔者的答案很简单,终极而言,好的生活就是能够达致长期高度快乐(包括自己、他人、甚至动物的快乐)的生活。然而,怎样的生活能够达致长期高度快乐呢?这就需要很多跨学科的学者进行长期的研究,以及各界人士的讨论。
快乐还是幸福?与徐景安教授的讨论
笔者有幸于2011年10月参加了讨论幸福问题的威海峰会。这个峰会主要是中国幸福管理研究院院长徐景安教授主导的。徐老不但在主办讨论幸福的会议、倡议《21世纪幸福宣言》等理论层次上致力工作,而且通过提供咨询,在实际改善许多机构与企业员工的快乐上,也有很大的贡献。徐老与笔者在关于快乐或幸福问题上有大致共同的看法,但观点也有重要的不同。
笔者认为幸福与快乐是一样的。徐老认为幸福与快乐不同,幸福是比较高级的快乐,只有人能够感受幸福,动物只能够感受快乐。以笔者的定义,一只狗可能比一个人更加幸福,但徐老认为狗完全不能够有幸福感。我们在会议上讨论,彼此没有说服对方。
人类肯定能够有比动物更加复杂与比较高层次的精神上的快乐与痛苦。(关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濠梁之辩,见黄有光2011,附录F)比较低级或简单的物种,多数完全不能够有精神上的苦乐,只有肉体上的苦乐;更低级的物种,多数连肉体上的苦乐也没有。(详见Ng,1995或黄有光,2010,关于福祉生物学一文的论述)笔者认为黑猩猩与狗等物种,应该能够有某些精神上的苦乐。为了给徐老比较大的空间,让我们排除能够有精神上的苦乐的动物,假定只有人能够有精神上的苦乐。
如果徐老定义幸福是精神上的快乐,或是某种(本节下文略去这条件)精神上的快乐,则根据这个(与笔者的不同的)定义,不能够感受精神上的苦乐的动物,当然不能够有幸福感可言。因此,根据徐老对幸福的定义,他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根据笔者的定义,笔者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如果只是定义上的差异,不必讨论,但是还有一个重大问题。
为了讨论上的方便,本节下文采用徐老的定义。根据此定义,幸福与快乐是不同的。幸福是快乐的一种,是精神上的快乐,不包括肉体上的快乐。吃冰激凌的快乐,不是幸福;性爱的快乐,也不是幸福。这类快乐,动物也有。你晚上回想这一天(或一生),认为成就(不论是在享受、事业、家庭、社会贡献等方面)很大,感到欣慰,这是幸福。
上述重大问题是,个人以及社会,应该极大化幸福还是包括幸福的快乐?徐老显然认为应该极大化幸福。笔者认为应该极大化包括幸福的快乐。
先考虑个人的情形。假定对他者与对将来的快乐没有不同的影响,你选择下述两项中的那一项?
甲:一生极度的肉体上的快乐(例如快乐量为九千万亿个单位)加上高度的精神上的快乐(即幸福,例如幸福量为九万个单位)。
乙:一生极度的肉体上的痛苦(例如痛苦量为九千万亿个单位)加上很高度的精神上的快乐(即幸福,例如幸福量为十万个单位)。
从极大化包括幸福的总(净)快乐量的观点,肯定选择甲,但极大化幸福量要求选择乙。
可能有人认为,在乙的情形,虽然肉体上很痛苦,幸福感依然很高,可见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从社会的观点,乙可能更好。从社会的观点,应该极大化所有人(假定不影响动物的快乐)快乐的总和,则也并不排除选择乙。(详见黄有光,2008年的有关论述)
对于社会的选择,把上述甲与乙维持不变,只加上“社会上每个人都有”,则极大化幸福要求选择乙,而显然地,选择甲才是合理的。若然,应该强调包括幸福的快乐,虽然并不排除对幸福的重视。
如果采用笔者的定义,幸福与快乐是相同的。如果采用徐老的定义,幸福与快乐是不同的;但终极而言,我们应该极大化包括幸福的快乐,而不是排除快乐,只极大化幸福。
不久前读了徐景安于2011年11月14日对“以幸福为核心理念:推进中国新文化建设”问题的答记者问。徐景安说:“人怎么会产生幸福感?它会无缘无故产生吗?不会。这是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当饿的时候,有馒头吃是重要需求的满足。对三餐无忧的人,吃馒头就不是重要需求了。幸福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
上述对幸福的讨论显然在幸福中包括肉体上的快乐,也显示动物能够有幸福感。狗饿的时候,有肉骨头吃是重要需求的满足,会有幸福感。
徐景安也说:“幸福来源于物质幸福、情感幸福、精神幸福,鼓励人们在追求物质幸福的同时,重视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
既然幸福包括物质幸福,当然包括肚饿吃东西的肉体上的快乐,狗等动物当然也有这种幸福感。
其实,“重要需求获得满足”,只是通常能够产生愉悦感的有利条件,不是愉悦感、快乐、或幸福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当你肚子很饿时,填饱肚子是重要需求。不过,如果我只让你吃非常苦涩腥的食物,你为了不饿死,勉强吃了,但感受很不好,苦涩腥的负感受超额抵消吃饱的正感受,没有正的净愉悦感。因此,重要需求获得满足不是快乐的充分条件。假设有位学者,自认为并没有达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水平,对诺贝尔奖没有需求。然而,如果她意外获得诺贝尔奖,还是会有很大的幸福感的。因此,重要需求获得满足不是快乐或幸福的必要条件。
还有,幸福感不会无缘无故产生吗?很多人认为黄有光经常会无缘无故忽然大笑。(虽然这是真的,但也是半开玩笑的)
快乐研究的一些政策涵义
本节着重谈对公共政策的涵义,关于快乐研究对个人快乐的涵义(个人如何增加快乐),及科技发展如何能百倍地提高我们的快乐水平等问题。
快乐研究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是,在达到小康水平之后,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并不能增加快乐。对个人而言,比较有钱的人的平均快乐水平,比一般的与比较穷的人略为高一些,但有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因素。(详见Diener等,2010)然而,对全社会而言,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倍增加,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快乐。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温饱之后,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快乐水平的是相对收入或消费。有钱的人比较快乐,因为他们的收入比其他人高。然而,当全社会的收入水平随经济增长而增加时,不但你自己的收入增加了,其他人的收入也增加了。因此,快乐水平没有显著增加。由于相对收入效应,一个人(尤其是富人)的收入或消费的增加,减低其他人的快乐,可以说有外部成本,应该征税。传统经济学分析强调税收的反激励效应(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认为税收有扭曲作用或超额负担。其实,一般的收入税或消费税,即使单单从效率上而言,而不考虑平等,实际上有纠正作用,超额负担是负数(小于零)。
涵义一:由于相对收入效应,征收收入或消费税,尤其是对富人有纠正作用。
第二,对人们生存环境的破坏,随着生产与消费之增长而增加。这在中国的情形,尤其明显。世界银行的Easterly(1999)曾经分析得出,随着经济增长,约有比50%多一些的生活质量指标上升,但也约有比50%少一些的生活质量指标下降。这也部分解释为何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增加快乐。另一方面,随着时间与科技的进展,多数生活质量指标明显上升。
涵义二:由于对环境的破坏,征收收入或消费税,有纠正作用。
第三,像松鼠与老鼠等动物一样,人类也有累积的本能。加上人际竞争与无所不在的商业广告的影响,人们牺牲对健康、快乐、甚至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拼命赚钱。这对竞争性极强、物质主义横行的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更加明显。像茅于轼所说,“用危害道德的方式赚钱,用危害健康的方式花钱”,长期快乐如何能明显增加呢?
根据Gruber&Mullainathan(2005)的研究,对香烟征税,增加抽烟者的快乐,因为少抽烟实际上对他们好。这也和传统经济学分析背道而驰。(也参见Lucas,2012的反面论述)
涵义三:由于过度的物质主义,征收收入或消费税,有纠正作用。
在大多数国家,上述三项,每项都应该征收至少20%的税。合起来,征收40%~50%的税,都还是属于纠正性范围,根本不须要担心税收的超额负担。可能有人认为笔者估计太高。其实,根据Blanchflower&Oswald(2004)的研究,人们认为相对收入至少有绝对收入一半的重要性。因此,单单根据相对收入作用,就应该征收约33%的税。
当然,税收的收入应该用在对人民的长期快乐有利的方面,包括环保、科技、教育、公共卫生、广义的基础设施等,而不是被贪污与浪费,才能够真正有效率。但这些问题超越本文的讨论范围。(详见Ng,2003或黄有光,2008)
近年的研究显示,相对收入对快乐的影响,不但对有钱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甚至对相对贫穷的中国与印度乡村农民,也比绝对收入更加重要(Luttmer2005,Knight等2009,Knight&Gunatilaka2010,Linssen等2011, Guillen-Royo 2011,Fontaine & Yamada 2012)。有些数据甚至显示,“所有作用都是相对收入作用”(Layard等于2010年所做的结论)。古人说,不患贫而患不均,至少是在温饱之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关于环境破坏的严重性,更加明显。很多环境科学家认为人类只剩下二三十年的时间来避免因环境破坏而灭亡。单单温室效应或全球暖化这一问题,若没有及时处理,就可能要人类的命。
2006年前,不但英国皇家学会宣称,人类经济活动造成全球暖化已经是和地心吸力与进化论同样肯定的事实,连商界名人也出来强调环保的重要。那些到现在还不承认空气污染、全球暖化等环保问题的严重性的经济学者,不是躲在象牙塔,就是被其极端右翼的、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意识形态所迷惑。(详见黄有光,2007)
其实,有效率地处理污染问题,对其征收等于污染的边际危害的税,并不会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只是工厂甲必须付污染税,则其负担很重,可能必须关门。如果只是中国必须减少污染,其成本也可能很大。不过,如果全世界各国对所有造成大量污染的生产与消费,都必须付污染税,则市场会通过价格的调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调整,使绝大多数工厂还能继续生产,而且污染税的收入,可以用来进行环保投资,人们可以换去做环保的工作。
有人认为根据污染的边际危害的税应该是多少,很难估计。笔者(Ng,2004)论证,至少应该征收等于减少污染的边际成本的税,而这比较容易估计。
当你在挨饿时,可能会说宁愿毒死,不愿饿死。已经温饱了,应该更加重视,就长期与全社会而言,对快乐更加重要的是环保、科技、卫生保健、教育等问题。
正像我们现在的人均实际收入是一百年前的七、八倍,如果地球的生态环境没有被我们过度破坏,一百年后,我们的子孙的人均实际收入,也会是我们现在的五、六倍(如果以环保负责的速度发展)或七、八倍(如果以环保不负责的速度发展,而假定没有中途灭亡或至少发展停顿)。在此笔者提出一个问题:读者们,你们是愿意子孙们有安全健康的生存环境,但是只有我们五、六倍的人均实际收入,还是会选择达到七、八倍的收入,而冒着使人类灭亡,子孙们根本没有机会出生的危险呢?
轻度的家长主义(Soft paternalism)
如果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简单分析,人们是有充分理性的,也具有有关的知识,所做出的选择,是在有关约束条件下,把其效用极大化的。除非有像垄断力量、外部成本(如污染)等造成市场失误的因素,市场的自动调节,“如水之向下”,自然会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除非让一些人的情况变坏,不能让任何人的情况变好的效率最高的情形)。因此,除了可能需要适当的财富重分配,政府完全不需要干预人们的选择。
不过,根据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人们的决策既受信息不充分的影响,又有很大的不理性的成分。(详见Kahneman,2011)若然,是否应该让政府来实行中央计划,才能够达到最优呢?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已经证实这多数会更加糟糕。市场有失误,中央计划未必更好。我们应该避免传说中类似于罗马皇帝的失误。这个传说中的罗马皇帝,要选出全国最好的歌手,在全国比赛,得出最后两个最好的歌手后,要通过殿试,由皇帝亲自御定哪一位应该获奖。皇帝听完第一位歌手唱完后,马上把奖牌赐给还没有试唱的第二位歌手。怎么知道第二位歌手(中央计划/政府干预)不是更加糟糕呢?
像世界上许多事情一样,在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选择,最好的不是全黑,也不是全白,而是适度的黑白相间,中庸之道。市场调节能够大致有效,没有重大失误的地方(多数情形),由市场调节;市场有重大失误的地方,例如环境的严重破坏,食品安全问题等,必须由政府补充。政府如果还是做得不好,则必须设法改进,总不能够等死!除了极端右翼的无政府主义者,绝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会同意这种中庸之道。然而,对于一些理性不足的选择,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则还没有很一致的看法。笔者的看法依然是中庸之道。
首先,政府在这方面的干预,不能够太细,不可以对人们指手画脚。这不但会增加行政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影响人们的自由。自由对快乐有很大的正作用。即使人们的决策是错的,政府的决策是对的,政府也不可以在私人决策范围取代私人。即使短期看来是改进的,对自由的影响,长期而言,多数会是灾难性的。经过反右、大跃进与文化革命这三大灾难洗礼的中国人民,对自由的重要性应该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当人们的决策有相当程度的失误,后果又相当严重时,政府虽然还是应该避免使用粗暴的手,但却可以考虑采取“轻推”(nudge)的方法。Thaler & Sunstein于2008/2009年发表的书,就以Nudge为名,论述如何用轻度的家长主义或符合自由的家长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方法,鼓励人们作出更加适合的决策。其中一项建议是要求厂商给消费者的合同必须简单与容易理解。现在的绝大多数合同,不但长篇细字,内容也很难读通,使多数消费者(包括笔者在内)连看也不看。(参见Sunstein,2011)
一项在西方国家很成功的轻推政策,在中国可能不需要,但可以参考其原则,用在其他方面。多数西方国家,人民的储蓄率很低,多数国家实行以低税率鼓励(甚至用强制要求)人们在养老金账户存钱的政策。美国国会的极右的保守派与左倾的自由派(liberals)联手通过“明天储蓄多一些”(save more tomorrow)的轻推政策。这方案不要求人们马上增加储蓄,因为这样人们比较难接受。它要求当将来薪水增加时,自动开始增加储蓄。由于不需要马上减少消费,人们比较能够接受。
除了美国,包括英国与南韩在内的一些国家都接受了轻度家长主义的政策。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小组,应用行为科学来帮助政府。这小组的正式名称是“行为洞见队”,但人们称其“轻推队”。Richard Thaler教授是这“轻推队”的顾问。
许多国家让人们在驾车执照上选择关于意外死亡时人体器官的捐赠。有些国家是采用“选择参加”的方式,一个人只有签名填写愿意捐赠,意外死亡后才可以采用其器官;有些国家是采用“选择不参加”的方式,一个人如果没有签名填写不愿意捐赠,意外死亡后就可以采用其器官。换句话说,有些国家的默认选项是不捐赠;有些国家的默认选项是捐赠。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然而,绝大多数人是根据默认选项,很少人选择填写与默认选项相反的选择。因此,类似文化的国家,由于默认选项的不同,愿意捐赠的百分比差别很大,例如在瑞典是86%,奥地利是接近100%,而在德国是12%,丹麦是4%。(详见Johnson&Goldstein,2003)
绝大多数人并不强烈反对捐赠,但也很少人强烈要求捐赠。因此就随默认选项,没有采取填写与默认选项不同的选择。不过,所有国家都很缺乏可以救人命的器官。因此,绝对应该把默认选项定为捐赠,以增加人体器官的供应。为何很多国家还没有这么做,这是笔者很不理解的。只要有足够的保障,不让人还没有死,就盗取器官,捐赠肯定是正确的选项。既然已经死了,能够救活他人,不是很好吗?在澳大利亚并没有在驾车执照上让人们选择,而其默认选项是不捐赠。笔者虽然强烈支持捐赠,但由于时间、拖延等原因,也等到约十多年前才做了器官捐赠注册。其实,不必在驾车执照上填写,所有国家应该采用所有人的默认选项都是捐赠。你不愿意,可以填写选择退出或不捐赠。你没有填写,就假定同意。这肯定是正确的做法。
不只是在器官的捐赠上,在其他所有选项上,如果有一个是专家与具有相关知识的多数人都同意是正确的选项,都应该在所有情形,尽量让它们成为默认选项。例如,全谷面包比白面包健康,卫生部应该规定,除非条件真的不允许,在公共食堂,尤其是学校食堂,应该供应全谷面包,并且把全谷面包列为默认选项。人们如果只是说要买面包,必须提供全谷面包,明言要白面包,才可以提供白面包。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以对提高人民的快乐的重视,替代对经济方面的数量的重视的时刻。快乐问题牵涉很多因素。笔者提出的“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只是作为国家成功的主要指标。希望中国不但能够继续发展,人民也能够提高快乐水平。关于改革与发展方向与话语的讨论,只是继续向前走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于席正、江莉莉(2012):“试论消费决策与幸福:动机—精神力场—行为假说”,《经济学季刊》,11(3):969-96。
黄有光(2007):“跳下地狱?走上天堂?人类面临灭亡与极乐十字路口”,《经济学家茶座》,元月,第4~7页。
黄有光(2008):《黄有光自选集》,“当代华人经济学家文库”之一,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黄有光(2010):《从综观经济学到生物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黄有光(2011):《宇宙是怎样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黄有光(2012):“道德水平低下的成因与对策”,《经济学家茶座》,第二辑。
黄有光(2013):《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BLANCHFLOWER, David G. & OSWALD, Andrew J.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7-8): 1359-86.
BORGHSI, Simone & VERCELLI, Alessandro (2012),"Happiness and health",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6(2): 203-33.
DIENER, Ed, HELLIWELL, John F. & KAHNEMAN, Daniel, eds. (2010),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ASTERLY, William (1999), "Life during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4(3): 239-276.
FONTAINE, Xavier & YAMADA,Katsunori (2012), Economic Comparison and Group Identity: Lessons from India, hal-00711212, version 2.
GRUBER, J. & MULLAINATHAN, S. (2005), "Do Cigarette Taxes Make Smokers Happier?", Adv. Econ. Anal. Policy, 5:1-43.
GUILLEN-ROYO, Monica (2011), "Reference group consumption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poor in Peru",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59-272.
JOHNSON, E. & GOLDSTEIN, D. (2003), "Do defaults save lives? ", Science, 302:1338-9.
KAHNEMAN, Daniel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KNIGHT, John, SONG, Lina & GUNATILAKA, Ramani (2009),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4): 635-49.
LAYARD, Richard, MAYRAZ, G. & NICKELL, S. (2010), "Does Relative Income Matter? Are the Critics Right?", In Diener, et al. 2010, pp.166-216.
Rik, Luuk&Gerbert(2011),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India: The Curs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1(1): 57-72.
LUCAS, Gary, Jr. (2012), "Saving smokers from themselves: The paternalistic use of cigarette taxes",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Vol. 80.
LUTTMER, Erzo F. P. (2005), "Neighbors as negatives: 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3):963-1002.
NG, Yew-Kwang (1995), "Towards welfare biolog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of animal consciousness and suffering", Biology & Philosophy, 10(3):255-285.
NG, Yew-Kwang (2002), "The East-Asian happiness gap",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7(1):51-63.
NG, Yew-Kwang (2003), "From preference to happiness: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307-50.
NG,Yew-Kwang (2004), "Optimal environmental charges/taxes: Easy to estimate and surplus-yielding",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8(4):395-408.
NG,Yew-Kwang(2008),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8, 85:425-446.
OISHI,Shigehiro (2010)," Culture and well-being: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Diener, et al.(2010).
SUNSTEIN, Cass B. (2011)," Empirically informed regul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8(4): 1349-1429.
THALER, Richard H. & SUNSTEIN, Cass R.(2009)(updated editio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York: Penguin.
VEENHOVEN,R.(1996),"Happy life-expectancy: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of-life in Natio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39,1-58.
VEENHOVEN, R. (2005), "Apparent quality-of-life in nations: how long and happy people l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1-3),61-86.
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