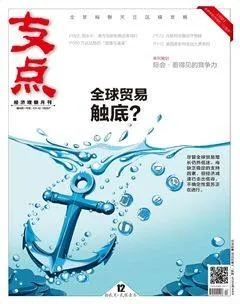城镇化是发展结果而非动力
2013-12-29陈志武
城镇化可以由政策驱动,也可以由市场驱动,而这两种驱动方式,会对地区城镇化发展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
以新德里为例,它的主要街道都十分宽阔、建筑十分宏伟,这是在权力主导下发展出的城市特征。但这对于商业而言,不一定是多好的选择,因为这种形式的城镇化带来的交易成本太高,不利于市场化发展。
另一类是市场交易催生出的比较符合商业形态的城镇化,就像苏州,哪怕是最大的街道也不一定有多宽,建筑物之间也相对比较紧密,这种形态下,商业成本相对较低。佛罗伦萨、威尼斯的发展模式正是如此,这些城市的市场交易都十分发达。
当我们在重新讨论,是否应该将新的城镇化发展作为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时,必须要思考,城镇化究竟是结果还是起因?答案可想而知,城镇化必然是发展的结果,而并非经济发展的源动力。那么,如果一味的通过权力、政策主导来推动城镇化发展,虽然短期结果很好看、很宏伟,但是长久而言,我们恐怕会看到更多的鄂尔多斯“鬼城”,会看到更多的发展弊端。
这也可以通过农村的发展形态来诠释这种观点。农村最自然的形态,是分散的住房遍布在各个农田边上,因为农民的居所与农田挨得很近,他们每天早上一出门便可以下地干活,运肥料也不需要走很远,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劳动时间和成本。
但是,一旦这种自然形态遭到破坏,最低交易成本被打破,将农民聚集到一起,安排他们整齐划一的居住和生活,最终的结果将是,农民不仅需要为居住的房子缴纳租金甚至购置房产,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会像他们一样,每天下地劳作都需要多走几公里,生产成本提高,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城市病的“农村化”。
这种城镇化的形态与交易成本的降低是相悖的,也是我们在长久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不能为了短暂的GDP增长而强迫农民放弃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
这样的例子还有户籍制度。当时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加强社会管理以及其他的经济目的而推出户籍制度,但现在来看,户籍制度导致政策层面的选择空间越来越窄,给整个社会带来诸多不平等,特别让农民及其后代遭受着方方面面权利和机会的不均等,不利于长远发展。所以,在定义城镇化以及其他一些政策的时候,应该听取不同的意见,要把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以及各个方面的后果和代价都考虑进来。
从操作上来讲,把农民都从自己的宅基地上迁出来,一旦这种模式出现问题,再想回到过去会变得异常困难。所以,中国自上而下推动的城镇化,在运用政策时应该稍微谨慎一些,对行政权力的运用也应该更慎重,否则不光是城镇化会走弯路,环境危机、污染危机、经济结构危机也将很难避免。
现阶段与城镇化相关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更多制约,把权力更好地关进笼子,虽然依然会产生观念上、生活方式上的城镇化问题,但并不会那么难处理。当把中国公民的权利和机会都变得平等,而不是走独木桥的时候,城镇化便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