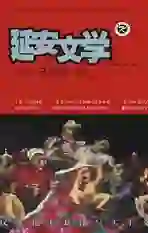戏说“小人图”
2013-12-29吕向阳
吕向阳,陕西岐山人。陕西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解放军文艺》《西北军事文学》《延河》等。
引 言
凤翔木版年画,是民间艺人酿出的一坛陈年美酒,品读它就像触摸一轴地道的关中民俗画。民间艺人虽然身份卑微,但将根须扎在最基层,从而把对生活的只光片羽、对人世间的眉高眼低描绘得极为传神。这些民间艺人是真正的丹青妙手、艺术大师,其捕捉美的能力如狮子捕捉黄羊一样敏捷有力。近日,我无意中发现了其中的“异类”——八幅“小人图”,颇为有趣,且讽刺意味甚浓。于是,用手中的拙笔,为“小人图”作出粗浅的诠释。
一、扶上杆儿抽梯子
木版年画的本色是质朴简洁,晓畅明快。民间艺人往往直奔主题,无须拐弯抹角。你看,杆上人的眼神露出丝丝可怜的哀求,而抽梯子的人却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画面直白地告诉人们,“小人会置你于困境,要睁大眼睛认人哩!”
人生在世,困厄重重。谁没有七灾八难?谁没有雾失楼台?谁没有败走麦城?这个时候,就巴望着有人指点迷津,或是雪中送炭,或是扶危济困。古道热肠者送衣送粮,慈眉善眼者嘘寒问暖,豪士侠义者拔刀相助,见多识广者献计献策。但其中也不乏这样的人:描绘前景天花乱坠,指拨得你能摘下天上星星。等你一旦入套,悲剧就来了。
扶上杆儿抽梯子,这种小人的心态就是给陷阱盖上鲜花,将自己打扮成善人或智者,却把你陷到坑里去。小人的精明就在于热情,在于主动,在于伪装。赤裸裸地害人会露馅,于是变着法子用谋略当毒箭,用忍耐当匕首,不择手段,达到目的。
我们总是警惕手执战刀、明目张胆的敌人,却总因喜戴高帽子被敌人暗算。我们总是不喜欢说真话的朋友,而喜欢说恭维话的小人。于是小人活得很吃香,朋友活得很吃力。直到抽梯子的那天,才认清了人,已为时晚矣。小人的梯子上不得!一个人在世上活得不容易,遭小人暗算可叹可悲,这就是这幅版画的张扬力和说服力!
二、得风扬碌碡
碌碡是农具中的实力派,早在秦朝就替代了石柱、木棒那些效率低下的工具,汉唐明清十多个朝代的辉煌,说到底都是从碌碡底下滚过来的,直滚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才被迫让位于农业机械。
昔日没有脱粒机、收割机,可谓碾场靠碌碡,扬场靠木掀。碌碡转一圈,木掀扬半天。要把麦子从堆积如山的麦秆、麦穗、麦衣中分离出来,是一场人与碌碡、木掀、扫帚、簸箕等和自然风的协同作战。于是,在碌碡完成了碾压使命后,借风扬场就成了农人最迫切最焦心的期待——望风的手搭凉棚,唤风的打起口哨,等风的恨天咒地,而老天偏偏紧扎着风口袋与人作难。微风整日不吹,好风三日不来。某日老天终于发了脾气,一场狂风,差点把碌碡吹了起来——这就是“得风扬碌碡”这句话最初的出处。久而久之,得风扬碌碡,就成了天大的笑话,就成了讥讽信口雌黄、异想天开的口头语。
这张版画上,一个壮汉喜滋滋地招呼着风神,果然要风得风,好风下凡,缕缕清风顿时被驯服得如绽放的朵朵牡丹。兴奋之余得意忘形,竟自不量力把木掀塞在了碌碡下面,神气十足地盘算着“得风扬碌碡”。
“得风扬碌碡”者,不分青红皂白去跟风,不管东西南北风,什么风他都敢跟。农村人将这种人讥为跟屁虫。别人说风他就下雨,别人说雨他就响雷。
“得风扬碌碡”者,多为“长舌妇”、“公道男”,时常嚷嚷着:“人都是这么说呢,岂能有假?”总是嘟囔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谁敢给人铁板上钉钉子?”直到有一天事情真相大白,“得风扬碌碡”者脸红得像猴屁股,见了人像做贼似的。扬碌碡扬没了脸面,扬没了人格。虽然起初很起劲很风光,但到最后却落得个“尻子客”、“转轴门”、“阴阳人”、“醋溜神”的下场。
碌碡滚了几千年,已经滚乏了滚累了,没了用场,但演化出的“得风扬碌碡”的故事还在上演,还要在关中人的口中流传一代又一代,因为再没有什么语言比这句俚语更能鲜活地将这些小人丑脸描绘得如此入木三分了。
三、见了旋风竟作揖
在沙漠、在草原、在关中农村,受暖热气流和地形影响,常见粗如碌碡、形若魔柱的旋风忽隐忽现,有的在旷野疯癫狂奔,有的在坟头腾挪旋转。旋风作怪时沙起柴飞,鸟恐兽惊,行人眯了眼窝抓了脸,猪狗挣脱链子钻进窝,农村人像碰见了凶神恶煞似地提心吊胆,把此唤作旋风,骂作妖风。旋风乍起,大胆者快步追击,胆小者吐唾沫压胜,但怕事者却被其狰狞面目吓得魂不附体,晕头转向间竟对其作揖叩头,于是凤翔木版年画传神写照,给世人留下了一副令人忍俊不禁的小人图。
我细细琢磨着这幅版画,画面上的人物不是普通农人的装扮,更像清末民国间的书呆子。他眼里倾泻着恐惧和游移,毕恭毕敬间若有所失,诚心诚意后若有所求,而那股受到膜拜的旋风得意忘形,像无数长蛇缠绕扭曲在一起,时而奔时而停,时而盛时而竭,像魔鬼一样示威,像疯狗一样狂吠。
今天的年轻人,看了这幅版画都会发出一串讥笑和嘲讽。可是,放在解放前看这幅版画,你就觉得它并无怪异之状,也无荒诞之处,而是广大百姓可怜可悲可叹的生存现状的真实镌刻。
旋风是何时成为鬼神的,不得而知,但鬼的幽灵在乡间徘徊了几千年却是事实。旧中国有许多愚根,缺医少药是其一。医疗卫生的落后,使好端端的人一会儿就闭了眼,于是人们常常怕鬼恨鬼怨鬼直到驱鬼,于是农民发明了三件法宝——血溅之、火映之、桃木钉之……文化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少文人不是传播先进文化而是故弄玄虚,传播《易经》大义的人少,算卦问卜的人多;用科学解释自然现象的人少,用鬼神吓唬人的人多。
如今,在科技昌明的大环境下,农民已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了!见官不用躲,生病有医保,受灾能救济,有疑问科学,对旋风一类的“鬼”更是见怪不怪了。但是,见了旋风就作揖的后人并未绝迹——见恶人低头哈腰,见权贵趋炎附势,见穷困事不关己,见危难袖手旁观。
四、爱钱钻钱眼
凤翔木版画“爱钱钻钱眼”,亦庄亦谐地勾画出了两个“孔方兄”无往不利的百般俗态——“光绪通宝”的麻钱被幻化成碾盘状,一人很吃力地扶着麻钱,一人正削尖脑瓜欲钻钱眼,而硕大的脑瓜怎么也钻不进去。这情景,就像牵着骆驼穿针眼,就像赶着大象穿窗户!
古人说,致富没有常业,财货没有常主。“爱钱钻钱眼”,实际上被关中人骂作“要钱不要脸!”钻,是挖空心思,不择手段;钻,是投机钻营,不顾脸面。钻钱眼者,往往会耍出坑蒙拐骗六亲不认的伎俩,会使出贪得无厌谋财害命的绝招。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富起来了,洋起来了,美起来了。市场经济让百业兴旺,让能人受宠,让富人扎堆,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之风却也愈演愈烈,于是有了“笑贫不笑娼”的恶俗,钻钱眼者如过江之鲫。
吕思勉先生在《窖藏与古物》一文中尖刻指出:“珠玉金银,或出深渊,或在穷谷,其取之也,不知靡人力几何?既得之而又埋之,置无用之地。既而又靡人力以掘之,而又不可必得。其所费者,或自暇以领略人生真趣之时日也,岂不哀哉?”
“夫事莫善于公,而万恶皆起于自私。”进取与致富是世间的常理,知趣与知足是人生的真谛,而营私与贪婪却往往是祸端的渊薮。在财富面前,分清公与私、善解名与利、辨别人与物、判明国与家,无疑是走好今生、光照后人的大是大非。
五、白地捏骨角
关中人把耕耘待种的田地称白地,把羊角、牛角、鹿角称孤角、骨角。骨角本是长出来的,是草木血肉之精灵,是山川雪雨之化身,但厚重豁达、幽默好古的关中人,却时常用白地捏骨角,揭示世间的云谲波诡,痛责笑骂乡村那些无中生有的小人。本来,白地是准备播种庄稼的,却被好事之徒凭着想象捏出了牛角羊角一类的骨角,岂非咄咄怪事?你看,画面上的小人眉毛倒挂,眼珠露白,胡须下撇,明显包藏着杀机,闪现着狡诈,释放着歹毒,一边手忙脚乱地捏出了一堆堆骨角状的东西,一边像做贼似的生怕别人窥见,随时准备拔腿就跑。而他身后退一步就是危崖深沟!这幅版画构图简洁生动,刀法娴熟,传神逼真,寓意深长,堪称“小人图”中的扛鼎之作。
在社会生活中,白地捏骨角的并非都是坏人坏事,比如灵感触发创造,幻想催生发明。假如没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男儿奇志,怎能揣着梦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可见,无中生有无疑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宝中之宝。但是,如果把无中生有的本领错用在日常生活中,那就大错特错了。君不见,擅长唆使弄非者被骂作“日弄山”,习惯栽赃陷害者被骂作“尻子客”,惯用离间伎俩者被骂作“搅屎棍”。
白地捏骨角者有四个特征:一是造谣中伤,二是栽赃陷害,三是装神弄鬼,四是吹胀捏塌。如果说有什么预防和医治此类顽疾的灵丹妙药,那不妨用“近君子,远小人”作为自卫、自省的武器。
六、用钱买上皂角树
皂角是肥皂、洗衣粉、清洗剂的祖先。旧时没有肥皂,洗衣洗头,全凭这牛角状的宝贝。这也是人们爱栽皂角树的由来。而要从密密麻麻的毒刺间举起竹竿打下皂角,更像打星星一样吃力。这时,晃荡在皂角刺间的竹竿,被硬刺划拉得浑身震颤,偶尔一个毒刺掉在谁的脖子、脚面,或被恶作剧者耍弄,谁便像一尾蝎子钻进了被窝,慌作一团吱哩哇啦。于是,敢不敢精脚爬上皂角树,就成了农村人最头疼的赌场。
有了赌场,就有行话,就有了千百年来一句俗语:“有钱能买精脚上皂角树”,由此也生出了“有钱能买鬼推磨”的俚语。这幅版画上,一个穿戴整齐的阔人,一本正经地将一串货真价实的麻钱,展示在一位可怜巴巴的穷汉面前:“看吧!只要精脚片子爬上树,这就归你!”而愁眉苦脸的穷汉双手紧搂着蟒蛇一样的树干,眼里充满着恐惧,他不是怀疑这串钱的真假,而是早在这棵皂角树上领教了无数次鲜血淋淋、脚肿手胀的苦楚:“钱是真的,皂角刺也是真的!”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勤劳致富是千百年来人的梦想。钱是驶向幸福港湾的舟楫,钱是通向富裕天地的快车,但钱也是双刃剑。钱是丰衣足食、勤劳致富的神驹良骥,钱也是杀人越货、一夜暴富的饿狼猛虎。钱,在我们每个人使用它时,分明在用无声的语言提醒着我们,拷问着我们:只有关闭心中那扇兽的大门,才能关闭钱的那扇兽的大门!
这幅“用钱买上皂角树”的版画作者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却给世人留下了一面铜镜和无声的警示:钱,有多有少;家,有富有穷;官,有大有小,但只要正路挣钱、量入为出,钱就是泉,越疏浚越旺盛;若是邪路捞钱、财大气粗,钱就是催命的鬼、败家的神。
七、吹涨又捏塌
乡间远离闹市物资匮乏,最引人眼球的是货郎担,孩子每每见到挑着两竹筐、腰如一张弓、手持拨浪鼓的老者,就兴奋不已,那花花绿绿的气球,把孩子们惹得手脚痒痒团团转。农村人把这气球吹气口加上小竹管叫“吹涨捏塌”,尽管这个吹泡泡、听哨哨的玩具实在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但却令成长中的孩子心驰神往、乐此不疲。而长辈们听多了、听烦了,总是嗔怪地说:“长大了别做吹涨捏塌的事!”
昔日曾经风行一时的“吹涨捏塌”,这阵从儿童玩具行列中已经消失,但“吹涨捏塌”这个口头禅,却在乡间人的语言中依旧闪光。近日我在翻拣凤翔木版年画8幅小人图时,像发现了久违的一件宝物,突然眼前豁然一亮:原来,一个极不起眼的“吹涨捏塌”,早就由孩童的玩具走进社会舞台并定格在版画上,看来耿直倔强的关中人,对种种“吹涨捏塌”的货色深恶痛绝,不是没有来由的。
在这幅版画上,两个老兄闲来无事,相互较着劲吹猪尿泡、羊尿泡,一个头戴元宝帽子,半蹴在地上,吹得眼珠子白多黑少,吹得脚尖快要离地,吹得肚子胀成青蛙。旁边站着的人,手里也拿起“吹涨捏塌”准备使劲吹哩!想必两个人想比赛一下看谁吹得最凶,看谁能吹破天!这幅版画创作于清末民初,那时还没有气球飘动在中国,而猪羊尿泡肯定比气球难吹,不把自己腮帮吹得像猪羊尿泡,当然是吹不起来的。
乡间是一个大社会,各种人物都聚集了,有正面角色,有反面角色,有吹胡子瞪眼的,也有甩袖抡刀的。庄稼人把搬弄是非、挑起事端、从中渔利的人骂作“吹涨捏塌”。起事者是他,息事者也是他;兴事者是他,灭事者也是他。
小人与君子,如同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炉。君子无论如何艰难也要守住底线,而小人为了达到目的总是指桑骂槐,偷梁换柱,含沙射影,不择手段。正如鲁迅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一样,“吹涨捏塌”者纵然有36计、72变,但最终无一不是“反误了卿卿性命”,把自己“吹”死“塌”死,从古到今,无一例外!
八、东吃羊头西吃猪
多年前,经济困难,百样短缺,不要说吃肉,就是高粱搅团包谷糁、萝卜缨子蔓菁根,也要省着捏着,生怕有了这顿没下顿。于是,谁家年关能扛回一个猪头,就像今天中了千万大奖一样神气,肯定惹得四邻八家垂涎三尺,翻肠倒肚。在凭粮票布票肉票购买东西的年代,猪头也是关系户、走后门的代名词。每到年关,一向红火的生猪收购站更是热闹而神秘,屠夫的白刀子与管屠夫的纸包子,绝对都要耍弄猪头、猪肝、猪心、猪板油、猪下水甚至猪尾巴的把戏,特别是按官职发猪头,就是一条铁规。收购站生怕混淆了“肉头”“瘦头”,忙中出错,便给猪头贴上“朱县长”“杨局长”“牛主任”之类的标签,于是闹出了笑话。
吃猪头难,吃羊头更难。先人造字,将“鱼”与“羊”拼在一起为“鲜”,羊大为“美”。于是,一个勾魂摄魄的“鲜”字,一个心花怒放的“美”字,凡人听了就手脚绵软、胃口大开!而那个年代普通人吃不起羊肉,偶尔步行几十里在县城吸溜一碗羊肉泡解馋,就觉得风光得好像吃了八套席,回到村上半个月还飘散着膻气。
我手头的凤翔木版画小人图,压轴之作竟是让人满口生津的“东吃羊头西吃猪”。画面上,一位眼珠泛白、穿戴阔绰、满面春风的“公子哥”,一手捧着猪头,一手捧着羊头,把头拧得像拨浪鼓,顾了左顾不了右,生怕脱毛的猪头羊头从手里挣脱。他蹴在地上翻着白眼,猪头也翻着白眼,羊头也翻着白眼,六只白眼构成了这幅图的轴心,三颗头定格了公子哥的贪婪与张狂。“东吃羊头西吃猪”,这句民谚究竟流传了多久,已无法考证。今天的汉语词典把那些八面玲珑的人描摹成“左右逢源”,夸张为“两全其美”,简洁则有之,但远远没有了“东吃羊头西吃猪”的鲜活韵味了。今天所说的“一个萝卜两头切”“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等俗语,实际上都是从“东吃羊头西吃猪”这句口头禅的缝隙中长出来的连理枝。
关中人常说:“东吃羊头西吃猪头,就是没有自己的头!”这话说得好,说出了真理揭开了根底。吃了猪头吃羊头,吃得脑满肠肥,吃得八面风光,但吃到最后会磕掉牙,直到撑死胀死。天下没有白吃的羊头和猪头。传说中的饕餮胃口大得能吞下一切,但这个“有首无身、食人未咽”的家伙最终也是“害及其身”。今天的人们,还是要管住自己嘴,管住自己手,要管住这一切,归根到底在于管住自己的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如果常常这样提醒自己,嘴就不会胡吃,手就不会胡伸,人才能知足常乐,平安无虞!
责任编辑:侯波 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