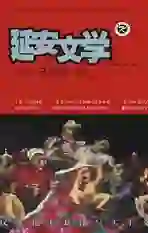尖叫的石头
2013-12-29高宏
高宏,陕西横山人。2002至200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2003至2005年在清华美院做访问学者。现居北京宋庄画家村。
对着天叫一声,说,开始思考。
站在泥土里,想起在志丹的路上诗人阎安对我随意说的一句话:“这里是上帝的地方,在上帝的地方人要生活其意义是深刻的。”这是对大地生命进行过无数次思考后的随意,发人深思。
在冬天荒凉的高地上开始追问此行的目的,头脑是空白的,一个悬着的疑问叩击疑虑,在山沟里转悠。对大地我不止一次行走过,丰盈着羽翼,撞击着心灵。
印象中的志丹是闲散的,简单直接的一个概念。刘志丹是志丹人心中的永恒坐标,原因单一的不再单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陕北出了个刘志丹。”通过对周河、洛河、杏子河的寻走,对志丹有了畏怯。一个封存了自己而失落的文化背景,在遗忘的伤痕里打上了悲怆的疼痛。失怯的破坏里看到的是在时间里的损耗,人在利益的熏心下作恶,大地让人感到忧心忡忡。
石 头
夜的黑暗中,急速的脚步磨擦土地,发出的声音带有惊悸的力量使人缺乏自制力,想摆脱心中的不快情绪,却听到诡秘惆怅的疑问。
伴随升起的太阳,高原的整体在下降、上升、遥望、沉思里交递着晨或暮的企盼,感受着红石头的遗憾。那质感、量感、光感用血红碳素的色彩使人的肉身陷入在山地,灵魂在渴望的阻滞与沉重里向高处盘升,沉重的压力凝固着狭窄的空间,在时间与生命的年轮里暴露着生命的痕迹。仰望岩壁上空,紫褚褐红与湛蓝之间夹着苍白略带划时代的疑问。这黄白位居山顶,给予人决定性的启示。遥望山头之间这片沉浮于大地间光与影的辉映,无不显露着神迹。
高渺的蓝天在峡谷低处暗示着莫名的力量撕裂着上升的欲望。那广袤的大地上,从山顶到低凹处横陈着古城的躯体,残垣的历史步履在大地上返回,战争的遗存历经风雨,土地是人的苦难铸造而成。所有的死都有灵魂潜埋在残垣中,到处都是无处不在的安息和不安息的灵魂。驻足在残垣土地上的生命是如此的复杂,听到驱赶绞杀的震颤。生存的磨难从深谷中涌出,清澈见底的震颤,显示着忍受生存重负时体现出的伟大,具有高度的忍耐力。憋屈坚强的灵魂从河水里攀附着石头的力量浸入在土层的苦难里,显示着疮裂而崛起的气势。
没有生命的红石头,摧毁着人的精神防线,对生存有了胆怯。不论如何充满信心都无法走向生的希望,只有亲近的权力,没有超载的力量,在精神的史话里千百年一个一个英雄的墓园,把期盼与希望在这里凝固,遗憾的深度让人命断在红石头上,留下体验的遗憾。
土地上的寨子、崖窑是志丹红石头上的遗存,挖掘者的目的是人的原始情感,是逃跑者与征服者的深厚的力度。在历史的时间进程中浸透着人类的反思,反观着人对大地的生命体验。在沟谷里行走,抬头望去每每有种感动心弦的呼吸。小河的静流在沉默的无声中细说古老的故事,那沟谷与沟谷之间,土壑与土壑之间有言说不尽的关系。志丹的塬峁沟梁是文学的、故事的,端庄平正里暗藏凶险,凝重端庄的姿态与古朴平正的气魄相吻合。秦砖、汉狮上遗留着英雄追悔和自责,投射着人类精神的光芒。巨人的面容在红石头上浮雕般地立着,原始灵魂用现代与后现代的姿态发问着上苍。倾注着高原的气派,秦人的遗韵,胡人的残留,宋代的古城,明清的驻脚,中国革命的光辉都在这里的红石头上历历分明,永恒照耀。
石头与泥土的川地是平缓的,山是凹凸的,崖是直立的,展示着一种叙述的强烈对比,断断续续的城垣展示着强大的力度。遥望上苍的天总是如此的蓝。单一的蓝盖在黄白的土地上形成明显的对比,形成的线条让人心颤。问天的沉思冥想中感悟着对生命力的无奈,把人的精神推向更高的精神之境,展示的是灵魂的力量。山是塬的高度,崖石是天的力度,沟是上苍思想的深度。所有的对峙、冲突、平缓、协调都是天宇的精灵,不能生,就是死,所有的艺术都在两极之外。
土地的生态在变,志丹的生态也在变,农耕与后工业化的时代在这片大地上延伸、深入,改变着人的心境。背山者那绛紫的脸,在颤抖中显示着承受力量。磕头机(抽油机)的节奏在伸向地府阎罗的深处思考、寻找着,获得利益的可观。带来的文化缺失是日益严峻的,甚至是一块永恒的硬伤。那痛是在心灵深处隐藏着,需要思考。
后工业时代给这块上帝的土地带来了一点希望,人们登高时迎接着曙曦的微光。如果此刻的陕北大地上不出现一代新的思考者、责任者、良知者,陕北就会陷入茫然。真的是这样,那么这块大地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历史苦味,贯穿于大地的命运感受之中。似乎是永恒的过去、未来,现在的渺茫。一切强烈的体验隐秘在高原遗存的形象中,触摸到彻头彻尾的幻觉里。
土地是一幅历史的沉重的负担,在地壳深层里埋藏着希望的种子。仰望生存神性的光,罩着单纯的力量,灵的躯体在追忆沉淀深思熟虑中显示着深厚坚实。锤炼的激情拓宽生命的河,流淌接收着信息,反复地解构、整合才可得到严整的力量,并发出铿锵的声音。
志丹是一块单纯的蓝,深度的红,疲泛苍劲的白,在相互的吞噬、消解、融合中,规整着粗砺,慢慢地最终聚集了一股深沉浑厚的力道拓展着空间。
站立在大地精神的高地上,精神的力量一定能永存。
两棵土槐
两棵老槐树位于志丹城西郊中央党校旧址旁,一前一后地站着,前边略显粗壮短小,树身的痕迹似银灰的发卷在盘着,展示着无尽岁月的记忆。那密集的皱痕里刻着难忘的苍桑,像苍老的祖父在讲着一部记忆的故事。后面站着的那棵粗壮高大,挺拔威猛,枝繁叶茂,历尽磨难的躯体腐化成空心,用一个姿态仰望着四方的阳光,打碎禁锢的蓝色,显示着一副生机盎然的绿意,在时间空间的生命流动中得到了重生的魅力。
老槐树遒劲固执地撑着蓝色的虚无,经历着岁月,见证着村子的同时也承载着历史,用枝杆护着大地,拿崇高与骄傲驱逐着恶劣和卑下。老槐树是大地上生命的根,静静地站着,扛着。投射到大地上的影子是夕阳下槐树对泥土的祈盼与落泪,映照毛泽东在树下讲课的声音。这是生命之根上发出的对漫漫前程抱有一份热情的希望,用奇迹不断地破灭阻碍前进的航标,这一过程已经证明了,转变为历史,保留在生命之根永远的身后。
老槐树的生命之根,枝节未满,身形在泥土中站立,使人体味到温情与美好。弥漫着时间记忆,那份淡淡忧伤的历史语调,深思中发出对时间偏执的追问。试探着天究竟有多高,地究竟有多深,将欲望扬在空中,把仇恨掩埋在泥土中,经受着风雨考证,一岁一枯荣地活着,用千疮百孔展示着坚韧,对天做着虔敬。
老槐树记录着思绪和遐想,几百年来,几千年里,慢慢地走着,走在一辈辈人的记忆中,沉默里绽放着飘忽的思绪。谁也记不清掉过多少次叶子,死过多少根枝杆,在活着的过程中把一切写进梦中。
老槐树的生命之根有一种宿命,暗藏着人的无知和麻木,从来没有看到过生活中的苦难与不公,一切在黑暗中认命、承受。是土地的座右铭,也是胎记。所有的酸楚在黑暗里被掩埋,酝酿着不平,发出对上苍诅咒的恨意。生命不在此处,却在彼处,越是走近越是无法认识。
两棵老槐佝偻着,直不起腰身地站着,只知道不卑不亢的活着。夕阳西沉。仰望天空,没有任何指路的星。未来是疑问,是钉入地壳中的长叹。听,受苦人在地里刨哇刨哇的节奏声,单一的寂寞惨淡只有上帝知道。晨光里,老槐树的姿态意犹未尽,迎着光在微笑,枝与叶结成生活的网。群鸦落下吵闹声里把起点与归宿织在网中。看见黑暗的灵魂,将抹灭的心灯重新点亮。黑是生命的幽灵,在生与死的两极里思考着艺术人生。
在生命的根系里探寻心灵,是孤寂的心在朦胧的睡意里梳理着纷乱的思绪。真实的怕,真实的只能叫人珍藏。怅然的感觉就如同洛河上的那座贞洁牌坊一样深刻,孤独。红石牌坊那四个形似女人臀部的石桩在大地上打洞,沉沉地思考着大地,破碎的斑迹檐头寻访着浩渺的天空。苦是思念丈夫无助的生理悲痛。整个川道如同一个美少妇睡着的心神,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的顾影自怜。准备在无人的时候,悄悄地推开心扉的门,在忍受苦难中成就着人生崇高的大道,做出摧残自身生命而换来对生命的虔敬。
直面两棵老槐树的生命之根,影子下的心境在孤寂中的天然宿命,真的使人无意中想到志丹县城的东山上那座为男人建造的石塔矗立在天地间的阳物。对着蓝天,向着太阳打洞,具有和尚用心看破尘世的无能,有什么资格在那里指手划脚?忘记了思考,忘记了疾苦中挣扎的众生,单一念头就想走进天堂,是在做白日梦。面对和尚山有说不尽的贬义,在和尚对天感叹号上划上句号。
残阳里,两棵老槐的生命之根忧伤着,村民立着香案供奉着,表达着一种美好愿望,动作与姿态足以表明心的虔诚。他们残缺的心灵表达出的超现实的思考是有意思的。对根我是无法言语的,只能从浅薄的记忆里感悟良多。心中燃烧着火球在喷嗤激烈的情感,茫然得不知所措,感觉到有清风急促地掠过,一个人误读着生命中的泥沼,根的生命站立于根的土地升向爱的天空。
一个村子
不知如何去理解刘志丹,不想过多的纠缠这个问题。刘志丹只是志丹人心灵中的光,是灵魂对整个世界感受的象征。
漫游刘志丹的出生地金鼎楼子村,会被根本就不存在的力量吸引。认识是想象的,根本就没有专注激奋!
刘志丹的出生地与所有陕北人的出生地大同小异。村子在卑微中存在这淳朴的生命,门前的洛河言说着生命的长久。四周被山围着,面山当地人叫龙山,座山是虎山,看上去有些破碎。是当地人心中高贵永恒的情怀,不需要解释就能表明意图。一个永不停息的生命图腾,神秘的蓝色中挂着月光皎洁的夜,灵驻留在穷乡僻壤,看着一堵残破的破矮墙上留下柔和推移的光,遗弃的红石窑实在看不到什么突出的地方。但似乎听见了一个生命的呐喊。生命的脚步在夜里走寻。沉思的天空是浸透着的,没有云的遮拦,只有星月映衬着苍茫的群山。山道上默默地留下刘志丹儿时打闹的音容,但夜晚淡幽的月光笼罩在深山里,没有声音的对话,是活着人的情感,是活着的人的叙说。
天空高得着实可怕,星星平放在天上,渐渐高升的月亮,在破墙院子的枣树上挂着。整个村庄、田野、树林、山峦在一片静谧中沉沉睡去。驴的叫声,猪的呼噜声和西墙外新房窑洞内穿出的哼哼声,在村子里穿行,白狗在夜里成了幽灵。刘志丹在这里只是感情,没有改变这个村子什么,相反还给这川道,这片土地增加许多死者,使空守房子的寡妇在夜晚里念着苦经。
夜的静是禅僧。刘志丹的祖辈也是普通百姓,几辈子的学好向善,修桥补路,建寺垒塔,织出、组成了一个英年早逝的刘志丹。用行走登上高山,迎来了霞光,山崮的苏醒发出铿锵声,在沉睡中渐渐地显示出坚实的姿态与和蔼和笑容,永恒的停留在高耸的峁塬上,陡峭的岩壁上。刘志丹带来的思考是丰富、凝重的。英年早逝没有能扯起飞扬的帆,更没能远航。这早逝是陕北的早逝,完成了接纳、奠基、发展、壮大、出发的任务。没有中央红军的到来,即使刘志丹能长寿,也不能夺得天下。这是陕北的宿命,是上帝给这方水土的基因。
迎着微风,望着夜色下的枣树和四周的矮草,听着飒飒的音响,环顾四野,这几孔破旧的窑洞还是比周围的窑洞要强大。此时天空中一只猫头鹰无息地掠过山顶,翱翔在准备的碧空,点燃着心中神秘情思,产生敬畏的心扩展到广阔无垠的苍穹。
刘志丹是大地上生长的荆棘,是洛河腹地里的生命。土地贫瘠命运的刻薄,惊天的聪明与亲切憨厚形成鲜明对比。这精神容量是巨大的,是受苦人在泥土里挖掘出来的,是地里种出的庄稼,是大地上牢固强烈的情感。
看一眼冬天这个裸露着的汉子站在辽阔无际的原野上,是用什么样的心思,目光在时间的过去眺望着远方,定有一番激动人心的情景。这是烙印,是心灵直接归于大地深处的复杂感情。面对楼子沟这个村子,有的是震撼、热爱、眷念、赞美,更多的是悲伤,是恒久价值所在,是最朴素、最直接、最单纯的情感并置。去除所有印象以及似是而非的印痕,楼子沟村最直接的元素就是针对心灵的阻力。
村庄的败落景象,是一个生命衰老的象征,形象也模糊在峁塬顶端,模糊在连绵的群山周围。那几孔伴随刘志丹长大的窑洞只能是他曾经生命的见证,眺望窑洞本身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任何企图陶醉都略带梦的感觉,这短暂的生命里充满诗意节奏。命运并不悲惨,悲伤的是抚养生命的土地,是母亲唠叨一生的磨难,父亲的沉默,子女的哭泣,妻子眼睑的红肿,嘴角中发不出声音的呜咽。无尽的悲怨随着暮色晚风向蓝黑色的天宇尽端逝去,留在褚褐殷红色的红石头里。
刘志丹的死是天对陕北人的呵斥,是上帝对土地最纯朴厚道情感的处罚。死是拯救天下苍生必然要去的地方,拓荒者的可怜被一个念头死死地缠着生者的生痛。人人都是革命的过客,只有死才会生长出更强盛的生命。
刘志丹的死在当时并没有多少色彩,是陕北人素描的疼痛,具有单一深沉的浑厚,对中国革命是重要的,因为刘志丹为革命者落脚奠定了基础。英雄真的死在黄土塬的山脉上,在河流的拥簇下,在天哭地嚎的推动下,深深地打在志丹人的筋脉里。一个精神的行走者,在事业面前昏了头,用意志对土地的眷恋的深情,对革命信念的真切,在生与死中感到了忍受苦难时的庄严伟大。一个引领者的命运是具有灵性的,能使卑微者变为高贵的灯,涌动着阴沉命运的力量,应当以师法心灵的态度当作自我心灵的散步,倾听着内心的信条。
今天,大地上的生态在变化,对凝重沉着的气质有了差异的模糊。单从贯注在土地和生命的情感上认识是不够的。刘志丹无疑是土地上朴实英雄主义的悲剧精神高度。面对英灵只能从形式上去忏悔,以个人的情感对英雄进行无知而可卑的亵渎,是对英雄的强暴。
风清扫着,楼子沟村在寂廖、静穆中叙说着一切。
故 居
走在入冬的土地上,雾气凝成的冷冰粉沫吹指到脸颊上。慑于寒气,我蜷缩着身子,手顺势放入衣袋中,在志丹县城的郊外摇晃着,仿佛要在这雾霭中等到什么。无名的悲壮用忧伤的眼睛逼近着那熟褐焦灼的红石头,脸上由不得扭起了粉红色疙瘩。志丹的革命故居摊放在面前,空空的摆放,样子极度疲劳,加上困乏,在大山的垂直挤压下,保持着难以保持的平衡。想一想当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在这山的狭窄的空隙中,是紧绷的情绪,还是松驰的状态,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疲惫中听到一个小小的哈欠,心里泛起沉默的酸楚。
矮窑中留下的是想走出困境的兴奋,所有的话语在今天人们的耳边絮絮叨叨个没完没了。
凉风飘起,一个人扭动着肩膀,晃着脑袋用眼睛死缠着山下这排庄重的碳血红的石头窑洞。坐在窑里的硬椅子上,两手平铺在八仙桌上,头如同砍掉一般稳放在桌子上,瞪视着窗外,寒气不知何时又悄然浸入了洞内。渐渐地回到了封闭的状态中。缩着身子,朝着一把把椅子用手抚摸去,是无奈的微笑,责难的目光,无数双眼睛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八仙桌上,困惑与羞辱之情使人浑身发热。
窑洞,同样是窑洞,这几孔窑洞就偏偏有了生命。站起身来到院子中,随着一声喊叫就顺势仰天望着,突然间紧咬冻僵的嘴唇,气喘吁吁瞪着上苍发出惊人的一问,那话语又卡在喉咙里竟然说不出话来。双肩被风猛然一拽,眼睛里充满血丝,意识里的眼神就像火花的光芒那般刺人。
院子里的那棵大榆树上的喜鹊在晨光中一声声叫着,弄不清是冲着什么在问,这带着浓重天音的尖叫声是什么含义。使人瞬时默不作声盯着自己的双手,狼狈不堪地强忍着疼痛,体肌内拥有了一种无法挣脱的力量悸动。心脏发疯似的推打着胸膛,头撞着胳膊,仰望被树杈打碎的蓝天。听着墙外的喧闹声,那是生活的刀刃。慢慢直起身子来,面对着外面用变曲的胳膊擦着脸颊的憔悴,神色紧张地默默地注视着外边。心在一遍一遍地不知重复着什么。耳朵里听到的是狂躁激愤的声音,只能摇一摇心,用清晰的声音重复着苦经,语句里骤然生起恐怖令人魂不守舍。顺着思绪随口说一句粗话冲淡了一个人的气氛。脏话中将头扭过来看了一眼故居,恢复了精神,表情里摆出威胁的架势,像一个纵情任性的孩子在嚷嚷。在一个人的不知所措中感到恐怖在消失,但还是弄不懂故居的心思。视线在避开故居的脸面,心想这是不是一个恶意的玩笑,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至少可以感到对人没有什么危险。望着阳光下红色的石头思量着,只有这样看着,站着不动才能得到点什么。
直面故居在屈服的狂热中离去,用沉默不语掸着衣服上的尘土,神经质地默不作声地呆坐了一会儿,闭起了眼睛,内心的深处屈辱好似凝成了一块石头,像一个血红绛紫的猪心,对现实的仇恨仿佛毒液似地开始一个劲地往外涌动,不再与任何景物打交搭腔。
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吭声是惭愧的,脸色一定是青色里耍弄着舌头的嘴唇,愤愤不平地一言一语地教训着,默许地数落着灵魂,琢磨着忍气吞声的暴光。用不语低垂着脑袋,全然是一个人的架势,哑巴似的不能作声。发干的憋屈如同生铁一般压在心上,英雄在时间的记忆里清楚地消散着,灵魂的强大只能使人不吭一声地用观望的态度敬畏着英雄。
带着凝望的眼神走出了旧居的大门,把压力和损害团结到一起,一脸的茫然收回了昂扬的情绪,急剧地冷却下来。
志丹的县城不大,高楼耸立。现代化是标尺,金钱是志丹干部的标准,瞅一眼干部的慢动作的工作作风,只能用怜悯打量着心。一个人在慢条斯理的掸掉身上的泥土,为怅悯低贱的情感而羞愧,觉察着内心深处的默然,回头望着远处的故居是如此地透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威严。
历史在今天忍气吞声,声调缓慢而凝重的表情里似乎隐藏着一团将要升腾起的烈火,是安抚,更是强制。摇一摇头,双手抱紧了胸前的衣襟,走在犹豫不决的路上,迈着步子几乎是风在拽着往前走,满肚子的愿意,满脑子的不愿意。是逃走的神态,是施暴,是收获,只能用逼问的眼睛扫视着远处英烈们的故居。寻找那外表上被打伤和砍伤的痕迹,刻印在内心深处慎重地触摸。
冻僵的眼睛站在远方对着太阳望着故居,一束虚晃的光在防范着视线。这虚光里有伟大灵魂接见斯诺时留下的音容笑貌,是肯定,鼓励的眼光在风雨中是那样的一声不吭。伟大灵魂是一颗颗勇敢的心脏,在征服着天宇。笑貌中那雄辩的语调,清晰的嗓音里作着沉默忘我的回答,用决心承担着不可越过的障碍,扛着前进。
湿漉着的早晨在发沉。风是冰凉冰凉的,发颤的浑身默不作声地走着,一样的姿态走了好长时间。寒流在抽击着腿脚肚子抽筋,痛这一念头猛然间升腾,难以自持的一股力量缠得人没完没了,心中充满焦虑和悲哀,使尽全力挣脱这种力量,也不知如何去掩饰失败和悲哀的情感,只能一声不吭瞪视着远方,那充满怒气的眼里突然溢出了泪水,只能以羞愧的无地自容的姿态去面对一切。
秦直道
秦直道,终于见到了秦直道。没有想象的那样伟岸、宏大,也不是那种根本的不起眼。直道上没有任何古老的烟尘,被掩埋在荆草和丛林中,单一地平躺着,踉跄中行走着。假如不知道,这就是直道,一定会认为是一条乡村宽广的土公路。知道了就不同,是一定会猜想蒙恬、扶苏在直道上的英姿雄壮。传说中秦始皇归西的灵柩碾过历史记忆,在人的心中有种宗教的精神高度。
对秦直道不能用今天的技术去追问历史。这条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还是能看到忧郁深思的眼神,对人性惩罚的极限,能寻找到秩序、法度下的残酷。事实上人的伟岸都是以人性的残酷折磨熔铸而成的,文明的历史标志在形成民族精神坐标中,永恒是用孤独铸造而成。
秦直道是通过对人性罪孽处罚的遗存。直道变为一个孤单的老人,留下的是一个失落的背景,单一的无以言表,立在荒芜的高地,敬畏警示着利欲的人。
道 士
马头山,是道家之地,历史悠久。道家择地都在高、险、奇上做文章。我对此产生过质疑,难道只有如此这般的形式才是仙境吗?
正午的马头山坍塌在大山的深处,被山风托起。生命在飞逝,没有炫耀的朱红,只有高墙的坍陷,松林苍幽,野草茂盛坦荡。横放遍地的残瓦里躺着一根根白骨的木头在失魂落魄的诉说着沉静,迷迷糊糊中能听到唉声叹息。唉叹声让人睁开眼睛,给生者一个安慰的眼神。
一个人穿梭在丛林中的马头山上,才能使人醒悟。没有当地人说的那样神奇,地方上的人总是对自己的生命图腾给别人夸耀,美好的愿望中加进了故事性。说马头山是西北的道教圣地,佳县的白云山道观都是从此地传过去的。历史无存考证,美好的假说实在是让人可爱的可笑。
蓝天下的禁锢,林影的罗网下看着残碑。昔日香火的景象,晾动着四方的人,所有延伸隐没的命运在马头山上构成。那个时代神灵是存在的,今有枯杆作证。历史的遗作看不到哭泣的悲伤,更多的是沉默的空虚。
看破红尘的马头山肉身道士,在时间的彻夜不眠中坐化了,双目凹陷的眼睛不知疲倦地瞪视山谷,探寻着天高,呆滞的深情永远是惊讶的木然。假如山腰的那间破旧石屋会做梦的话,灵魂飞离红尘黄土的躯体,一定感受到的是冬天狂啸的风,对境界发出幽然的感叹。看到住在山里的这个灵魂的罪孽深重,深重的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那永久誓言背后做着没有任何意义的自行等待的毁灭。山上修长的钟声,是从历史纵深处传来的一串串无尽的钟声,钟声与山谷默默地对视着,声音使我对坐化的道士有某种奇怪的感觉,诞生出无言的刻薄。
窥视神灵是有罪的。马头山更像是一个藏在无尽岁月里的故事。我没有找到刻在难忘岁月里的沧桑,因为走进肉身道士就能讲一个凄美而娓娓动听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就在双目疲乏的眼神上。愿人真的能平步青云为神仙,可是要小心,天堂的路是拥挤的,抛下身后,一切是永远的不可能。整个世界空无一人,纠缠盘结徘徊心头的闹剧,在心的深处有锁链牢笼,用极端缩短着自己的生命。站在精神的高度上看,留下个肉身泥胎就让人感动,太过简单,这个灵魂,不能为今世的人苟同。
遗 痕
洛河、周河、杏子河如同三条红色的劲龙,不汹涌,但有力量。
河谷山峁深处寺庙塔群林立,古寨拔地,遗墙古城,古墓石碑矗立。自然奇观更是百兽奔跑,丰富得让志丹不再是个概念。
在冬天的荒芜里,这些看上去对生活并不重要的事都长久地扎根在记忆里,镶嵌在石缝里,影留在脑子中。拂去尘埃的往事在竭力挣扎着虔诚的心灵,为了实现崇高完美的灵魂,红石头发出祈祷的呼声。在时间的体验中走过苍老遗存的生命,是古人给的遗嘱。那龙泉寺的石塔,永宁山深处的砖塔,城台寺内的残毁石雕等。记不清楚太多太多,今日无从考证得道高僧的功德有多高,也无需谈论他们的对与错。文明让人在短时间内读不懂,在陕北还是第一次过目了这么多的砖塔、石塔群,站在下面不信佛的人也会相信佛的境界也博大。
今天,钱是第一生产劳动力。陕北大地正以后工业时代的飞快速度进化着,改变着,发展着。佛陀倒下了,佛头砍去了,塔群在坍陷消失,横七竖八地残躯睡在荒芜中。能走到今天无不让人对敬畏产生了置疑。石墓被盗,白骨是祖宗,留下深深的黑洞是大地的疼痛。留着空空的墓道,将高耸的碑头伸置在虚无的蓝空。下半身入地祈祷,上半身吟天长啸,永远不能面对子孙的审问。
文明古迹的现身,神话世界可敬。在无数次的战争中,在今天的毁灭下,文明被失去文明敬畏的心葬送着。
真的不想谈论永宁山古寨、金鼎古寨、旦八古寨有多么雄伟,古基石宏伟吓人,寺庙里石雕丰富得让人震惊。城廓的遗址等还有多少不被人知道,叫什么名称不重要。古迹在惆怅着,盗走毁灭的不是文物,而是对这方水土的注解,是对文明的湮灭。没有文化、文明的土地就是概念的黄土。
志丹的遗存非常复杂,多少个民族在这方水土上进行过注解,强悍的战争中不知有多少观念在此地失落后又重新建立新的概念。走到今天是不易的,艰难的让人不敢去多想。
阳光下,西风凛冽,破落的古址更显悲凉。心灵在畏畏缩缩地亲近着。也难怪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祁玉江在谈到要打造文化大县时是那样的坚定、直爽、自信。希望成功,不要搞成文化美容,过去搞的三台山文化景观就是例证。
对望着红石崖单一、单纯的力量,内心是复杂的、多变的,一方面惊喜,另一方面是担忧,更多的时候是伤心的悲哀。突然夜色下永宁山的砖塔在将要坠落时回头揪心,等待着帮助、搀扶的修缮。龙泉寺石塔的祖物有两座不知去向。城台寺的万佛洞内的石头在滴血中呻吟着,古墓的白骨在阳光下咆哮着,城廓在蓟草的埋掩中哀思。作为人只能想。
过去的已成过去,历史的已成为历史,一切都在沉默着,什么也没有说。人类在历史的前进中丢弃了朴素、厚实,丢掉了老祖宗留给我们对神灵的敬畏。对视的眼睛停驻在想象的荒地里,一个动作攀上山岩,立在山顶,爬过阻隔的心,走近、离开、抬头长久地仰望留在心上的痛。
惊喜的是仅有的遗痕在不声不响地撑开、托起志丹的概念,使人睁开眼睛。顶着虚妄的蓝,托着浓烈的太阳,做着问天问地的祷告。志丹的大地上形成永久的简单,永久的粗砺,在雄壮、坚韧里展示着硬度、力度。三条弯曲的河流永久地弯曲着想不到的憨直。历史在接受着风沙的掩埋,几千年来都有漠然无声,一言不发。
背靠永恒的红色石头,久远的黄土。这里是一个谜,一个愿,一个誓言,在沉默的睡意里竟让人惊奇。从痉挛的疼痛里读到磁石的魔法和符咒中走到今日,艰难不幸中带着悲怆的记忆,耸立于衰草残阳,被风清扫着,夜染着,星星伴着,在情景中畏怯。一个平庸的流浪者,能为你讲一些什么,一切归于无声。
责任编辑:魏建国 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