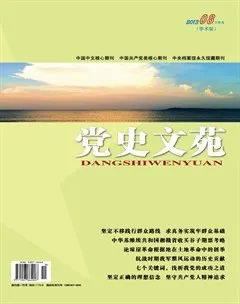改造袁、王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践
2013-12-29张丽君徐光兵
[摘 要] 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就是一条以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为主体的,联合知识分子、绿林武装和小资产阶级为辅助的一种统一战线。对袁、王的成功改造,正是毛泽东把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最早运用到对待农民武装这一问题的成功实践。其意义是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最大程度地壮大自己。
[关键词] 毛泽东 袁文才 王佐 统一战线
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就是一条以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为主体的,联合知识分子、绿林武装和小资产阶级为辅助的统一战线。他们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与广大农民结成同盟军,使得井冈山斗争体现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农民阶级为基本力量的十分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有效地开展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同时,为了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革命斗争,毛泽东在实践中还尝试了很多好的做法,如与绿林武装结成统一战线,为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打开了胜利的通道。这些历史经验,都是十分宝贵的。有人以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是党员来否定党的统一战线,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袁文才入党并不能说明他懂得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入党主要还是因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是利益的诉求促使他加入共产党,而并非他的个人信仰使然,所以说这个党员身份可谓是空有其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证:
一、从袁文才的入党背景及其与党组织的关系看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开始。随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共派遣大批党团员回家乡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进行打土豪分田地,使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此大背景下,1925年7月,宁冈籍在南昌读书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龙超清、刘辉霄、刘克犹等利用暑假回到宁冈开展争取武装力量的活动。面对风云变幻的社会形势,遁迹山林的袁文才也在深切地关注着形势变化,顺应形势不停地伸缩自己的触角,是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明证。1925年9月,龙超清等人上山招安袁文才出任宁冈县府保安团,县府接受了袁文才提出的要求,同意为袁文才的“马刀队”提供粮饷并帮助他扩大队伍,精明的袁文才很快率队下山赴宁冈县城就职。1926年9月,北伐雄师抵达江西,当时局势已经非常明朗,北洋政府兵败如山倒。于是“袁文才率领保卫团举行起义,在龙超清等发动的全县工农暴动的紧密配合下,……驱逐了北洋军阀县知事沈清源出境,推翻了宁冈县政府,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为委员,主管军事工作,宁冈县保卫团也改编为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指挥”[1]P451。其后,袁文才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凭借手中的枪杆子,击毙或驱走了三任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宁冈县长。是年11月底,中共宁冈党支部在龙江书院成立,龙超清为书记。袁文才在龙超清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被党组织派往吉安参加农民运动训练班。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袁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山大王”生活。1927年五六月间,为保存实力,袁文才接受国民党右派宁冈县长张开阳的安抚,出任宁冈县保卫团团总,直到7月底,因袁文才参加攻打国民党控制的永新县城后,才彻底与国民党决裂。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袁文才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保全或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入党的动机亦如此,是袁文才在大革命失败后别无选择的一个无奈之举。所以说“自身利益诉求是袁、王走向革命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一味拔高他们的革命理想动机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2]P137。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和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战事频繁、联络不畅、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党组织的上下级根本无法保持联系。袁文才本来受党的教育就比较少,再加之他长年住在深山里,有关党的理论、政策的书刊很难见到,对党的认识了解比较肤浅,虽然在贺敏学、龙超清等的劝说下入了党,但他的脑子里装的主要还是农民的平均主义和侠客的劫富济贫思想。他对人对事,往往只重感情,讲义气,爱憎多从个人恩怨出发。正因为如此,他的队伍虽然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旗号,反抗旧势力,但这支武装阶级观念模糊,带有非常浓厚的绿林习气,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崇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绿林作风;没有现代建军思想,部队的领导全靠对首领的个人信仰;没有正规军事建制,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只靠江湖义气约束。
二、从表五对毛泽东引兵上井冈的态度看
当时毛泽东既是受中央指派领导秋收暴动的前委书记,又是中央委员,率兵上井冈山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无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毛泽东深知袁文才部队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就是我们党掌握的地方武装,但对袁、王部队性质的认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客观分析,从阶级本质和部队组成成分来看,袁、王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武装,成员多是本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有反对地主豪绅阶级的强烈愿望。虽然他们长期以来打家劫舍,沾染上土匪习气,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从本质上看,二者并无根本矛盾,相反,却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阶级利益。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于工农革命军在边界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都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于是,部队一到三湾,他立即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自浏阳抵临永新之三湾,拟不日转驻贵邑,此后在湘赣边陲诸县开展武装割据,立农工政权,实施土地革命。此计划不知当否?希能共同议之。[3]p158并连夜派人送给袁文才,以争取他对引兵井冈山的支持。然而,袁文才果断地用书信委婉拒绝了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想法,他是这样写的:“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江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4]P169从这封信我们不难看出,袁文才根本就不欢迎毛泽东率军上井冈山,他怕毛泽东鸠占鹊巢,同时也可以佐证袁的党员身份其实就是徒有虚名。一旦牵扯到自身利益时,他早已把党员这一身份抛之脑后,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的“山大王”能否保住。
三、从毛泽东团结袁、王的方式及其对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起的关键作用看
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儿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毛泽东说道:“他们是绿林军,我们是草头王,大家可以合为一家嘛!有机会我要去拜拜山。”古城会议最后确立了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古城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选择位于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与袁文才见面,毛泽东通过赠枪之举让袁文才认识到,毛泽东的到来非但不是吞并自己,反而帮助自己发展。于是袁文才当即表示包下工农革命军的粮饷供应,并赠给银元1000块。正是由于袁文才的帮助,王佐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一起帮助工农革命军在攀龙书院建立了医院,在象山庵建立了后方留守处,伤病员和辎重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自卫军有革命的一面,由于缺乏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也存在着一些绿林的坏习气,但他们毕竟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同志。毛泽东果断地作出对袁、王部队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决定。他派何长工和宋任穷等到王佐部队担任党代表和连指导员,派游雪程、徐彦刚等到袁文才部队担任军事教官,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质。1928年的大陇升编,标志着前委对袁、王队伍的团结改造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也标志着这两支井冈山的“末代绿林”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从此在共产党的引导下,踏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部队和袁、王部队统一战线关系的建立,不仅使秋收起义部队在起义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中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隐蔽处,得以休养生息,而且使周边革命力量找到了一个新的集结地和出发地,将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插上了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打开井冈山寨门的革命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在1929年3月的一份“会剿”报告中写道:“湘赣不靖也,推原始袁文才不能勾引毛泽东,无毛泽东焉能结合朱德?”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把两支游民为主体的绿林武装改造成受命于共产党的工农红军,正是毛泽东把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最早运用到对待农民武装这一问题的成功实践。也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用人艺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最大的胜利。其意义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抗大时所说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也就是说,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最大程度地壮大自己。由于党内外的复杂因素,袁文才、王佐后来被错杀,错杀袁、王,实际上削弱了自己。错杀袁、王,“也就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井冈山长期被敌人占领,直到1949年江西全境解放时才得到解放”[5]P25。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改造袁、王武装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对袁、王实行统一战线的方式方法,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总结。○
参考文献:
[1]周谷生.吉安英烈[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2]汤红兵.井冈山时期的人物群体研究(1927-1930)[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3]匡胜,刘晓农.井冈双雄——袁文才、王佐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