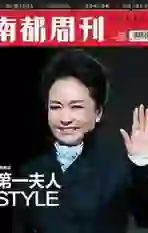反贪,靠尖端技术还是靠基本权利
2013-12-29刘远举
在当下中国,廉政是公众对新十年的一个重要企盼,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个技术性的保障,近日再次被提上议程,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陈利浩提出了一种思路,即效仿证券市场防范内幕交易的机制,对公职人员登记的本人及家属财产在信息系统中实施“名单管理”,定期报送清单、如遇异常的情况,状态系统自动报警,同时修订法律法规、消除“代持”;对于基本透明后的存量财产,按照黑、白、灰分色处置。这种思路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高科技,在体制内加强对官员财产的透明力度,本质上属于自纠自查。
这种方法要求一个较完善的身份识别系统来作为整个制度的技术基础。这似乎也符合相关职能部门的思路。据参加多次中纪委座谈会的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财产申报制度大概明年就能出台,因为“现行身份证在市场上非常混乱,很难做到认真核查,中纪委一直在等待二代身份证完全更换,预计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就会出来。”
应该说,粗略看来,事实的确如此。在房姐有几个身份证、几个户口时,这种利用高科技在体制内监管官员财产,从执行层面上来看,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只有漏洞更少的二代身份证系统,才可使新的监管制度更牢靠。
不过,仔细分析,却会发现更多的问题。指望用新的身份证技术来作为财产申报制度的保障,其本质是指望用机器来管住人,但是,不管再尖端的技术,再精密的机器,总是由人操作的,人总能控制机器、绕过机器——房姐的几个身份证虽然可以归咎于一代身份证的技术缺陷,但是,即使如此,多个身份证、多个户口却肯定需要公安系统内部人的协助。所以,指望用机器来管住人的想法,是幼稚的,如果把它当做一个可靠的监督制度基础,那么,就如同把大厦建立在沙滩上。从这个意义上看,二代身份证制度,不是财产申报的充分条件,即,有了二代身份证系统,并不一定能有高效的体制内监控。
另一种思路是变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财产公示制度。与申报不同,公示是向公众宣示,本质是利用群众的监督来完成前一种思路中赋予机器的任务。这两种思路的另一个差异是,财产申报制度是中央集中式的控制,希望用新技术来克服中央集权所必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与管理层级问题;而财产公示制度则截然相反,是依靠分散的、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群众力量来完成监督,可谓无远弗届。
不过,所谓公示并不是简单的公开,而是需要公众的讨论、交换意见、质疑,所以自由的舆论是公示的一个必不可缺的环节。这也就是说,有效果的财产公示及其监督,本质上必然是法治保障下的群众舆论监督。在这样的监督体系之下,即使没有完善的身份制度,但广大群众的期望、愤怒,以及国家对腐败的惩治决心,都会通过资本驱动、利益驱动的方式,促使媒体、记者去报道、去深挖。有趣的是,房姐四个户口的例子,再次从另一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在现在有着种种弊端的身份证系统中,媒体也仍能把她找出来、曝光在公众的视野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二代身份证制度,也不是财产公示的必要条件,即,高效的财产公示制度,并不必须要高科技的二代身份制度。群众、舆论、媒体自会完成所有一切的工作。
对贪腐官员的监督必然来源于制度,不过,制度虽然重要,但制度却不是凭空而来,更重要的是制度要接地气。也就是说,制度要在人民手中,人民要能对制度发表意见,舆论和权力之间必须有衔接环节——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只能是自由言论构成的栏杆。个体掌握的能级稍有增加,就直接改变了社会统治形态。同样,言论作为一个基础性权利,作为政治生态、社会意识中个体的基础参数,对社会改变的作用是巨大的。
没有接地气的制度保障,即使有锦衣卫式的机构,全国统一的信用网络,最终也难免异化,更何况小小的二代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