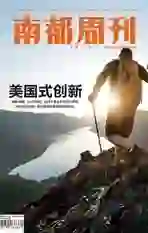我们的税负高不高
2013-12-29任晓兰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如何使国富民强,孔子的回答是:“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听了此言,哀公沮丧地说,“若是,则寡人贫。”对此,孔子睿智地答道:“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如此,孔子在论证君主财富与民间财富的辩证关系时,也引出了如何理解税收的作用以及如何看待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的话题。
宏观税负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期间内,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前些时候,福布斯杂志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显示,中国的指数为159,高居全球第二位。对此,我国马上有学者回应说,西方很多高福利国家的税负水平远高于中国,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么,我国的税负到底重还是不重呢?
税收可以看作是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不是按照血缘关系而是按照地域来划分居民、出现了特殊的公共权力、而且为了维护国家机构的运转而向居民征税的时候,国家便出现了。如果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那么,税收便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国家必须采用征税的办法来筹集国务活动的经费,否则便无法正常运转。
在这个意义上,古代“轻徭薄赋”的民本思想,乃是处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关系最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古代帝王也懂得,百姓为租税所困,官府如果不知体恤,致使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统治者轻则失去税源,重则还会遭遇反抗。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先秦思想家似乎在告诫我们,减轻税负,给予公众更多的生存空间,扶植自主创业、尊重企业家精神,才能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国富民强。
在现代国家,民众纳税是为了交换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征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和提高国民福利,公众所承担的税负应该与他们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相匹配。在这个意义上,高福利国家的高税收政策,是逻辑自洽的。
也正因为如此,判断税负是否偏高,至少要从社会福利的改善状况、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及政府用于自身的行政性开支是否合理等方面进行考察。不仅如此,税负水平是否影响到了民间企业的投资发展创新能力,政府增加税收是否影响到了公众的购买力水平,也都是必须要关照到的方面。不得不承认,近些年,中国一直选择的是通过政府直接扩大投资,追求高投资、高增长和高税费征收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税收的连续高增长,又极大地刺激了政府扩大支出的欲望,财政支出规模追逐着税收规模而迅速膨胀,推动着政府的职能和规模的急遽扩张。
事实上,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在经济衰退和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不应该依靠增加纳税人负担来解决财政需要,国家在制定税率、税目和税种的选择,应当比较中性和轻型。一个成熟的税收政策,不是消极地消减高收入者的所得,而是设法积极地增加低收入者的所得。也就是说,虽然有时候需要适当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负,通过转移支付来支援低收入者,但只有必要的时候才这样做。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尝试着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留在民间,焕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之后,我们需要给经济运行一个自我休整和恢复的机会。适当的减税政策,对于拉动消费内需、培育中产阶层、冲抵不良预期,以支撑实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更何况,根据拉弗曲线的原理,税率高到一定程度,税收反而会减少,而如果能适当降低税率,税收还能增多。从长远来说,一旦减税效应发挥出来,带动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和企业的发展,未来的税收总量必然会持续增长,从而形成一个积极的、良性的循环过程。
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为增税而促进经济繁荣的案例,也找不出一个因减税而导致政府贫穷的案例。当务之急,是切实提高我国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削减政府用于自身消费的支出和资本性投资的支出,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一方面为我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留下可操作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构建政府与纳税大众之间的良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