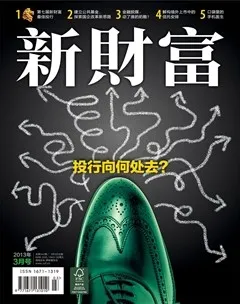金融脱媒:动了谁的奶酪?
2013-12-29丁安华宋敏
从中国过去10年的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看,金融脱媒正在逐步深化,其对货币政策指标的冲击尤为明显。单纯锚定货币供应量指标,难以起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央行采取以市场利率为锚的公开市场操作,将会日渐重要。
传统上,金融市场是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银行作为资金的供应方(通常是储户)与资金的需求方(通常是借款人)之间的媒介,从而实现社会闲散资金向实体经济的转移,而银行本身就是依靠存贷利差而生存。所谓金融脱媒(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就是指资金的供应方,不再通过银行中介,而是通过金融市场直接为资金需求方提供资金。金融脱媒,导致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角色和盈利模式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交易对手转变为经纪人,从利差收入(Interest Spread Income)转变成收费收入(Fee-based Income)。
美国圣路易斯联储局于1979年1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是早期研究金融脱媒的文献之一。据该文记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货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美国的短期国债的收益率一旦高于银行的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时,银行机构的存款资金就会大量流向货币市场工具。随着货币市场的发展以及各类资本市场工具的创新,银行的存款大量流失,出现了所谓“脱媒”的现象。
可见,金融脱媒的出现是与货币市场相伴而生的。而30多年来,金融脱媒成为全球性的现象,更是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根本而言,所谓金融脱媒,是指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取代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实质上是体现了从银行主导的经济(Bank-led Economy)向市场主导的经济(Market-led Economy)的转型。
金融脱媒带来社会融资结构变局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金融脱媒对社会融资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化。一方面,社会的融资体系趋向市场化,也就是说非金融企业越来越多地依赖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另一方面,居民户的金融资产构成中,传统的银行存款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而持有的资本市场工具越来越多。
以加拿大为例,来观察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加拿大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外部融资构成中,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60%,下降至目前的40%左右;债券融资的比重从15%上升至25%;权益融资从25%上升至35%。再以美国为例,来观察居民户的金融资产构成变化:存款占住户部门金融资产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25%下降至15%左右,而权益资产(股票和基金)和保险资产(含养老金资产)在家庭户部门金融资产中占比大幅上升。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从30年的时间轴观察,可以确认金融脱媒的趋势性变化,但各项比率的此消彼长并不是直线式的。一般来说,当经济陷入衰退、股票市场下跌、通货紧缩出现时,企业无法在资本市场融资,银行贷款占比就会反弹;同样,居民户的资产构成中,银行存款占比也会上升;反之亦然。
中国的金融脱媒呈加快之势
中国金融脱媒的程度,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尽管如此,过去10年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脱媒现象已呈加快之势。从社会融资结构看,人民币贷款占比大幅回落。2002-2011年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由2万亿元扩大到12.83万亿元,年均增长22.9%。而这期间,间接融资(人民币贷款)占比从91.9%下降至58.2%;直接融资发展迅速,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从4.9%上升至14%。
从家庭户金融资产的构成看,银行存款占比下降,而居民在股票、基金、保险、理财产品上的投资占比进一步增加,逐渐形成了银行负债端的金融脱媒。据统计,2010 年末,中国住户部门金融资产达到49.5万亿元。其中,存款占比63.8%,较2004年末下降8个百分点;而证券、基金占比14.4%,较2004年末上升4.2个百分点。
根据《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在社会融资规模保持适度增长的同时,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要提高至15%以上。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进取的目标,仍然具有浓厚的银行贷款主导社会融资的色彩。我相信直接融资的比重将达到20%的水平,银行、证券、保险等主要金融行业的构成将更趋合理。
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冲击明显
现代货币政策理论,受弗里德曼的影响颇深。简单而言,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的根基,是建立在货币流通速度(V=GDP/M2)的稳定和可预测性基础上,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主张。
然而,金融脱媒与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脱媒和金融创新使得各国对广义货币(特别是M2)的相关定义和统计口径变得混乱不堪,货币供应量的准确计量变得几乎不可能。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金融脱媒使得基于银行存款的货币存在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银行“脱媒”出来的资金以全新的面目出现,超出了传统货币指标(特别是M2)的统计范围。正因为如此,近来一些国内学者总是拿中国的M2与美国的M2进行比较,其荒谬无异于“关公战秦琼”!
金融脱媒的结果是,货币供应量指标无法得到准确计量,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再稳定,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不确定。弗里德曼提出的“单一货币规则”失去了神奇的效力。1993年7月22日,美联储宣布放弃货币供应量这一中间货币政策目标,转而根据利率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表明金融深化过程中金融脱媒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带来重大的挑战。尤其是金融产品的创新,使得资金在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突破了原有的限制,削弱了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加大了政策调控的难度。从全球趋势看,随着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推进,各国的货币政策将逐渐从数量型(货币供应量)调控向价格型(利率水平)调控转型。
从中国过去10年的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看,金融脱媒正在逐步深化,其对货币政策指标的冲击尤为明显。2001-2010年,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2、新增人民币贷款)的实际值在绝大多数年份均超过年度目标值,且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的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关系基本趋同。但情况在2011年发生了变化,该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47万亿元,超过年初7万亿元的年度目标值;然而,同期M2实际增速为13.6%,低于年初16%的年度目标值。央行在2011年10月调整扩大了M2的统计口径,使得M2增速得以小幅提升。M2增长放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脱媒使得银行存款增速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可以预见央行的政策工具将会更加注重公开市场操作。一方面,公开市场操作可以精准且迅速调整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公开市场操作可以实现对市场利率的调控。数量与价格效用可谓兼而有之。近来,中国央行一直在加大逆回购投放操作,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央行在快速的金融脱媒进程中,适时地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意图。
丁安华先生的观点紧扣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的脉搏及货币政策的新动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关于“金融脱媒”问题,总体上我很认同丁安华先生的观点,并就以下两个问题简要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个是金融脱媒的中美比较。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金融脱媒”主要受内外两方面因素驱动:从内因,也就是资金的供给方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1933年美国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的“Q规则”(Regulation Q),标志着进入利率管制时期,限制了存款利率的上限。但其后由于60年代中期美国执行廉价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刺激通货膨胀率从1965年的2.3%急升到1969年的6.1%,7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形成滞胀,进一步加剧了负利率,使得银行存款对储户逐渐失去吸引力,资金有内在的外流压力。从外因,即资金的需求方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了多样化的替代选择,诱使存款资金从银行体系大量流出,涌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寻求更高投资回报。
从这方面看,中美“金融脱媒”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现阶段的“金融脱媒”也有其重要的特殊性。
首先,“金融脱媒”造成的结果与美国不完全一样。在当时的美国,传统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空间几近饱和,货币与资本市场反而日趋成熟,资金有多样化的投资选择,“金融脱媒”促进了美国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的发展和融资效率的提升。而现时的中国,一方面货币和资本市场还没有发展成熟,资金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由于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不高,从银行体系流出的资金大多追逐短期高回报,而没有投向有利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银行在传统的信贷领域也仍有相当大的业务拓展空间,例如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银行存款的流失还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
其次,美国的存款搬家主要流向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彻底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中国的存款搬家相当一部分通过银行理财产品的方式间接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信托等高风险领域,虽然作为影子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暂时转移到表外,但银行依然承担相当大的连带违约风险,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第二个是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在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时代,传统货币政策主要关注广义货币供应M2。实际上政策的着眼点在于控制银行的信贷增长,而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影响比较小。随着“金融脱媒”逐步深化,再单纯控制M2增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大打折扣。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不得不相应地转向兼顾对包括直接融资在内的社会融资总额的管控。以美国为例,上世纪70年代之前其货币操作受凯恩斯主义影响,主要目标是压低国债利率刺激投资,到了70年代,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在滞胀的环境下渐成主流,1979年保罗·沃尔克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后,制定了严格的货币数量目标,并以此成功控制住失控的物价。但由于货币供应量目标被引入后货币流通速度就很快且大幅度偏离原有趋势,1987年美联储不得不宣布放弃M1目标,1993年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不再将包括M2在内的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数量目标彻底退出舞台。实际上,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一种绕开银行体系,直接购买国债、MBS等资产,向资本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压低市场利率的非传统货币政策。
对比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以往一直锚定货币供应量,操作中除了要面对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这些传统难题,更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金融脱媒”这一趋势的影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创新政策工具,提升货币政策的效果。近来央行探索采取的一系列新的货币政策举措,已经凸显了这一新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