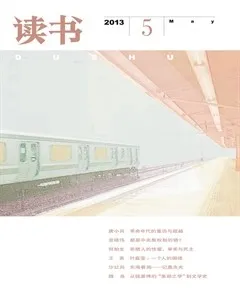舒卷的粉墙
2013-12-29姜勇
近年来,西方艺术史家已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对艺术品价值功能的理解和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图像、风格之类的作品内部的艺术性问题,还应拓展到作品的物质性和存在方式,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学层面(《美术史十议》,巫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零八年版,12—13页)。这种研究侧重的转向,也为中国艺术史的重理提供了诸多可贵的启示。例如,中国书画在今天与古时最重要的区别,也许不仅是作品内部语言的差异,还涉及观看方式的变迁。作品从古典时代浓厚的私密色彩,走向现代的公共性;从个体的书斋案头,跨入敞阔的展厅乃至漫无边际的外部空间。从表面上看,它们作为艺术从来都诉诸视觉实现自身——都是用于“看”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展示的场合、方式、范围,甚至对观看者的选择。这些外在的行为方式不仅影响到感受模式的改变,也决定了“观看”的性质。而观看的方式和性质,又常常是文化精神的某种映射。
如果对中国传统书画和西画进行装池上的比较,问题就会逐步显露出来。油画,可以说从它架上创作的开始——对绷紧了的画布施以油彩——到完成后嵌入硬质四边画框,都意味着一种强制性的展开,以及单一、静态的空间占有意识。而中国书画所采用的那种折页或卷轴装,则顺理成章地引出一个“敛合”的动作。它清楚地表明“收敛”而不是展示,才是作品产生后要经历的常态。收敛意味着对空间的尽可能放弃或不甚感兴趣,但同时,它却隐含了自身的时间性要求,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其一,卷轴不仅保障了舒卷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在长幅横式的手卷作品中,舒卷过程本身就是观看活动的一个介入因素:它对观看的范围进行必要的控制,使之纳入一个历时性的过程,而拒绝对全幅做同时性的呈现。具体而言,手卷的展示过程,是随着“看”的进行,作品左侧的部分被陆续打开,随之右侧部分被不断地收敛,视野所及范围因此有如摄像机的镜头,它要通过舒卷所能呈现的自然范围(约为一个手臂的长度)来展现连续构图中的段落感。巫鸿和吕胜中都对《韩熙载夜宴图》这一最为典型的作品内在观看方式做出仔细的分析(《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巫鸿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46—51页;《造型原本·讲卷》,吕胜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零二年版,81页),而实际上,凡此“狭长视象”的绘画与书法作品,都有展示过程中的段落要求,以使观者视野中的图式保持一个自足而又不重复的节奏空间。这样的节奏空间由于是逐步呈现和不断变换的,因此意味着时间统领和支配下的空间。这是手卷与静态展示的立式挂轴、册页或镜心等小幅作品的重要不同之处。当艺术家和欣赏者进入这种心照不宣下共谋的视觉结构之时,“看”的过程也由此被称为“读”。与“看”相比,“读”所强调的正是时间意义上的行进过程。
其二,卷轴和折页所提供的“敛合”形制,意味着中国人对艺术品存在方式的要求并非单一展示性的,而是允许或强制它进行“闭藏”——拒绝展示。甚至我们应该说,敛合是作品的常态,而展示才仿佛是偶然的事件。至于类似手卷那种狭长的作品体制,更排除了壁上展示的可能性,仅限于案头的临时赏玩。西方油画当然也不是以展示为经常性的,但它在装池上却未能有效地体现“敛合”的要求。通过敛合,我们会进而考虑到收藏的行为,因为敛合也正是收藏所基于的一个动作。“藏”是中国人处理“既往”事物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周易·系辞》所谓“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说的就是将所藏者纳入到“过去”的时间历程中。过去是不断消逝着的现在和未来,收藏之藏的行为是使所藏之物尽可能地延伸到未来,把无尽的“未来”变为它曾经存在的“过去”。在这样的意义上,它要求所藏之物具有物质和精神价值上双重的耐久性,而传统书画作品整套的装裱程序和技术,如其防腐、防湿、防蛀、防折损,也都暗示出一种对时间要求的尽力满足。尤其是卷轴或折页所支持的敛合形态,可使作品避免因长期暴露于空气和光线而带来的损伤。
当一个物件经由收藏而变为“古物”,让人得以对其“彼时彼地”的种种情事进行回顾和玩味之时,就自然产生一种时间深度上的“追远”效应。这是一种在政治、宗教和其他价值观念领域都被运用过的“时间的力量”。在艺术品方面,它会对人们感受作品的整个态度和体验产生影响,因而成为作品价值建构系统中的重要因素。
可是,敛合的意义并不止于此,进一步的辨认会让我们领悟到,它还可能是对观看者进行拣选的隐喻。折页和卷轴的形制所隐含的既不是无条件的展示,也不是全然不允许看。确切地说,它指示出古典士大夫艺术活动中的那种“限制性”的看。宋人孙少述的诗句对理解这个问题或有帮助,道是:“更起粉墙高百尺,莫令门外俗人看。”(《诗话总龟》卷六)该诗的题目是《栽竹》,考虑到竹子清幽、绝俗的文化品性及其与文人墨客的种种精神关联,这样的诗句完全可以视为古人艺术观念的一种借喻。“粉墙”象征着艺术家与世俗阶层的文化和趣味隔阂,通过它来圈筑庭园,就等于塑造了趣味的共同体,其功能恰如布迪厄所说:“趣味是分等级的,它会区分出不同级别的群体。被分成不同等级的社会主体,通过自身制造的区隔,会在美与丑、杰出与庸俗之间区分自己。在客观的分层中,他们的立场得到表达或揭露。”(《艺术与社会理论——美学中的社会学论争》,奥斯丁·哈灵顿著,周计武、周雪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91页)
既然这样的粉墙是由栽竹人有意构筑起来的,而且不厌其高,于是墙内的景观也成为一种阶层身份和权力的表征。粉墙既强化了它里面的群体身份,也向外发挥着拒斥的功能——使那些不具备艺术修养的人无由仰望或参与其事,不得其门而入。因此,对于卷轴或折页式的作品而言,它的展示是有条件的。当作品舒展开来的时候,它面对的不可能是公众,相反,其展示常常带有隐秘的色彩和私人性。这就是为什么文籍书画的弆藏之所被称为“秘阁”或“秘府”,而艺术藏品本身被称作“秘有”、“珍秘”及“秘玩”。通过古代大量的笔记、书信、日记等文献或图像资料可以知道,艺术品的展示通常是在一个称作“雅集”的小型私人聚会中进行的,被邀请的“观看者”则是与藏主既已建立起私谊的文艺名士。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具体作品而言,展示就仿佛期待中的“节日”,尤其对那些传世珍品和富有的藏家而言,就更是如此。将一件重要的作品长时段地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是不可想象之事,不仅远非慷慨之举,反倒可能被视为不谙风雅的蠢行。在这个意义上,作品就像传统家庭中的女眷,愈是高门贵第之家,就愈谨于抛头露面。
为了强调“连续构图”的特征,巫鸿对手卷做了严格的限定。他利用米芾在十一世纪所做出的“横卷”和“横挂”的区分,将不足三尺长度的后者排除出“逐渐打开”式的作品之外,“虽然当一幅横挂在获得愈来愈多的题跋时也能潜在地‘变’为一幅横卷,但其最初是作为单一画面的绘画来创作的,而不是具有多个画面的手卷”。毋庸置疑,这样的区分是颇具说服力的,但我更愿从功能构成的立场上,对卷后题跋的意义做进一步的阐释。
对书画藏品进行题跋,是古代艺术活动中十分普遍的行为。不断累积起来的卷后题跋凝聚了诸如美学品评、人物交游、流传线索、艺术生态、历史考据、辞章风雅等多方面的价值感。但从结构功能学的角度考虑,这些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此时此地”的见证人,跋主们为原作勾勒出一个相对生动、真切、饱满而又独一无二的历史轨迹。虽然拒绝展示性的收藏限制了作品的展示机会,但另一方面,藏主还是渴望找到有社会威望的人士为其藏品题跋。所谓“题赏增重”,其意义在于为作品的存在找到最有分量的见证人,以构成其被看的历史。
在一个完整的附跋手卷中,排在最前面的一般就是藏品原作,随后的题跋按照与原作的时间间隔依次排列。于是,作品的展开是以最早产生的,也就是时间上距我们最远的原作最先出现,而距我们时代愈近的题跋就愈在卷轴的最后。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空间对时间的“倒装”,但在我看来,如此这般的“倒装”形式恰好印证了本雅明所谓的“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本雅明著,许绮玲、林志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64—65页)。也就是说,卷尾题跋是烘托原作“权威性”的最有力的“灵光”,这道灵光把原作从历史深处推到我们的眼前——它们强化了原作独有的“此时此地”感。
在这样的意义上,附跋手卷代表了对现代艺术品“机械复制”的顽强抵抗。那些题跋反复提示着原作“独一无二”的存在和它一再被亲历和见证的历史。只要愿意展开它,你就被迎入到一个具体而自足的传统中。如果说,现代机械复制技术使得艺术品泛滥成“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成为视与听的对象”,挣脱传统而获得无所不在的“现时性”(《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前揭,63页),那么,卷尾题跋的形制仿佛早已预见到这一趋势,并以其促成原作独一无二的“历时感”的方式对之进行抵御。当然,现代复制并不会因此罢休,在为公众临摹消费的大量印刷品中,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孤立出来的卷首原作,大量的卷尾题跋则被弃而不用——无论由于它们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抑或因为成本的限制阻挠了复制的范围。总之,手卷遭到了强行的割裂,历时感被现时性取代。当原作包容在历史中的整个关系网络被斩断之后,本雅明所说的“独一性”也就不复存在,于是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复制品!
卷后题跋提醒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手卷,并不属于“当代”,因为“当代”是一个对时间深度否定性的概念。手卷只能是那种随着时间的向后展开,通过不断地题跋进行历史刻度确认,才逐步“成为”手卷的东西。换句话说,手卷是过去之物,它既是我们“在看”的东西,更应该是别人曾经“看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