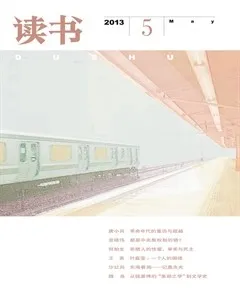读舒芜先生的《红楼说梦》
2013-12-29方竹
一
舒芜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中包括《红楼梦》研究,文章先以随笔的形式连载在《文汇月刊》上,后于一九八二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说梦录》。二零零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更名《红楼说梦》。
一百多年来,无数专家学者为《红楼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无可讳言,有些研究是与小说的本质相违背的。舒芜则明确表示自己只是普通读者,只关心普通读者关心的现实内容,这部《红楼说梦》的意义首先在此。他的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研究小说本身,首先专注于故事的悲欢离合,人物的喜怒哀乐。所谓“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这里的泯灭是怕闺阁中人泯灭,而不是怕宫廷秘闻档案泯灭。但他的研究又寄寓了很深的人文关怀,他认为:不是只关心了人物命运就理解了《红楼梦》,那还只是最基本的欣赏;从文学反映世道人心的观点看,它不是一部普通小说,而是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小说。舒芜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过:
我对《红楼梦》有个基本看法,认为它是中国古典文学最富于人性的一部书,就像聂绀弩讲的,是一部真正“写人的书”。如果要讲“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红楼梦》的伟大,主要在它的人文内涵。中国古典文学,包括文言的、白话的、正统的、非正统的,在人文主义价值方面,没有超过《红楼梦》的。这就是我《说梦录》那部书的基本观点。
这又是从思想上阐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正因为充分论述了人文主义价值,《红楼说梦》才完全区别于流行的“红学”(舒芜极怕被人称为红学家)。它是一部细致地分析思想、分析情节、分析人物的专著,关注点在小说本身,这方面大有可谈。
二
《红楼说梦》分前编、本编、后编三部分。前编是三篇较长的思想论文。本编在篇幅上是书的主体,共六十篇文章,详细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场景、情节,稍列几个题目就可明了:《黛玉骂的是谁?》、《宝钗的学识》、《袭人回家与元妃省亲》、《平儿与凤姐》、《丰富的半天》、《歌颂爱情的合奏》等等。题目写实,内容则趣味横生。文章或长或短,人物主次皆有,重在精准的分析。后编是四篇文章,分析王国维的悲观主义,谈《红楼梦》故事环境的安排、穿插及《红楼梦》的媵妾制度等。
本文只谈前编的三篇长文,它们包括了舒芜对《红楼梦》的根本看法。第一篇《谁解其中味》,是对话体,开篇即提出《红楼梦》到底写的什么。
以往常说的,写阶级斗争、反封建、四大家族兴亡,显然都太政治化了(实际上也只写了贾家一大家族)。但是,说它写了宝、黛、钗的爱情故事,爱情悲剧,对不对呢?舒芜的意见,大致如下:
这么说当然是对的,但如果说,它只写了或主要写了宝黛钗这个中心,就不对了。除了宝黛钗,作者还写了其他许多女孩子,对她们“无论着墨多少,都是一笔不苟地写出了她作为‘人’的价值”。
可是,这些具有人的价值的美丽女孩子,最后都以悲剧告终。曹雪芹(贾宝玉)十分悲痛、深为不平。如果缺少了对她们的关注,去掉了她们的悲剧,不仅无法构成“千红”,《红楼梦》的气象、其伟大意义,也缩小了一半,这就是越剧《红楼梦》令人感到单薄不过瘾的原因,它没有反映出“千红、万艳”悲剧的深广厚重。
因此,舒芜认为,《红楼梦》其实写的是——那个社会青年女性的普遍悲剧,她们既是青春欢乐又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主角,而不仅仅是宝、黛、钗的悲剧。
这是悲剧的第二层次。然而这还不是终极答案。
有人将宋朝的晏几道比作早生了几百年的曹雪芹,他的《小山词》,也写了许多可爱女孩子,小晏与她们平等相处。但舒芜认为,一部《小山词》不等于《红楼梦》,关键是没有写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而谁又能保证她们中没有悲剧?
元妃省亲本是贾府第一等大事,以前的文学作品若写这一幕,可以想象会怎样欢天喜地,感恩戴德。但是,在曹雪芹的笔下,一切都截然不同。修建大观园时的欢乐在元妃到来后荡然无存,从头至尾都是凄凄惨惨生离死别的哭声,这是历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所以舒芜说“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悲剧,仅仅是曹雪芹(贾宝玉)眼中的悲剧,在任何人眼里都不是悲剧,甚至那些女孩子们,对“自己的悲剧的意义与意味,也绝没有曹雪芹(贾宝玉)所见所感的那么深,那么重,那么无边无际,那么永劫不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早已说过: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唯宝玉而已。
宝玉亦渐长,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
以前也有评论者注意到这段话,但都没舒芜这么重视:“真是说得太好了,加上一个‘敬’字,这就是大大的不同,根本的不同。”
就因为宝玉的世界观里,充满了对女子的“敬”和“爱”,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命、是“咎由自取”,到了宝玉这里,就是无限的痛惜,感同身受。爱和敬有多深,悲痛就有多深。所以舒芜说:“《红楼梦》与其说是写青春女性的大悲剧,还不如说整个就是写的贾宝玉的大悲剧。”
这是悲剧的第三层次,已跳出女性的范围,是一个男性感到的苦难。然而思索还没止步,悲剧还有更深的含义:
宝玉的“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很不爱听,恐怕只把它当作爱情的誓言,却不理解宝玉是把她自己当作人世最高价值的体现,她的死对宝玉不仅是爱情的毁灭,而且是人世最高价值的毁灭。
这是从更高的人的角度阐明悲剧的意义,用人道主义思想照射出誓言背后深重的思想底色,将誓言从男女之爱中升华出来。舒芜指出:
贾宝玉对自己的否定,也是从人的价值来否定。有趣的是,不是觉醒过来看到自己是个人,倒是看到自己是人当中的“渣滓浊沫”。贾琏、贾环、薛蟠之流,倒不会把自己看作“渣滓浊沫”,正因为他们才真正是“渣滓浊沫”。
所有这些议论,都围绕人的价值。
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贾宝玉所有的爱,都是对人的爱,舒芜才做了这样高度的评价:
(贾宝玉)由爱慕而尊敬,由同情而抱不平,这就足够使他把一切青年女性尽量美化了……他所美化的女性的形象,其实就是他所理想的完美的“人”穿着女装的形象。他对女性的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人的尊重。
“完美的‘人’穿着女装的形象”,这个归纳深具思想力度,是近百年来对著名的“女清男浊”思想的意义明确、纲举目张的定位,令曹雪芹的困惑、忧伤、痛苦迸射出神圣的光芒。这一思想从始至终闪烁在《红楼梦》的青年女性形象中,应该是《红楼梦》的主题曲,认识到它,才是真正读懂了《红楼梦》,才能深解“其中味”。
我们由此看到舒芜先生一条清晰的思路:宝黛钗的悲剧——扩大到女孩子们的悲剧——深刻到贾宝玉的悲剧——最终是人的价值毁灭的大悲剧,并且是从宝玉眼中才能看到的人的价值毁灭的大悲剧!
三
《谁解其中味》着重从思想上分析《红楼梦》,但舒芜认为,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能闪闪发光,令人喜爱,却主要不是靠思想,而是靠性格。
《新人宝玉新在哪》一文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
一、如果单论抽象的思想,《红楼梦》远远不是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水平,与曹雪芹同时的戴震,才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的代表者,何况黄宗羲等又比他早多了。曹雪芹的思想比起他们,甚至是倒退了,所以说,贾宝玉形象的深入人心,主要靠性格。
二、虽然分析人物都必须分析他们的思想,分析他们之间的思想矛盾和斗争,否则就容易陷于“两峰双水”、“钗黛合一”,但是,又绝不能停留在思想的层面上。
黛玉、宝玉、宝钗、湘云、探春等感动读者的,也是他们崭新美好的性格,普通读者,谁会去注意他们是不是反封建?
这样的分析摆正了思想与性格在文学中的关系,即:作品的伟大靠思想,人物的成功靠性格,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必两美齐备,缺一不可。
舒芜认为,贾宝玉的性格“是以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在《红楼梦》以前,中国文学作品里从没有贾宝玉这样与环境不相协调的人。过去的文学作品里,也有忠良被谗,英雄失路,才人不遇,公子落难,佳人薄命等等。但是,他们同所属的环境是协调的,就是说,同当时的社会政治道德观念,同当时真善美的标准,是完全协调的。他们不管遭遇到什么不幸,总归代表着当时舆论公认的正义和美好的力量,在作品里总能得到当时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的了解、同情、赞助和支持。而迫害他们的人,不管怎样嚣张,总归为当时的清议所不容,公认为奸邪和丑恶的力量。只有贾宝玉,以他的整个性格,同他的社会相矛盾。除了林黛玉以同一类型的性格成为他唯一的知己而外,书中没有一个人了解他”。
这一大段话内容十分丰富,从是否与社会伦理观念相容来评价和回顾众多中国古典文学的典型,这就把宝玉的性格特点说得十分有意义了——他的不幸是人人都不理解,他的美好也恰恰是人人都不理解。尤其他一人担起全体女性悲苦的重量,却不被认为是正义美好的。他的言行完全超出固有的社会价值判断,表明一个新的真善美的标准的诞生,毫不夸大地说:这是预示封建社会灭亡的征兆。
这样的分析不是抽象地拔高,为完成一个大的思想命题而进行的空洞的推理,而是从作品的思想、细节出发,源于具体情节的推理。使读者不仅从性格上认识到贵公子贾宝玉平民化的伟大人格,而且认识到他的孤独所具有的深远的社会意义。从这样的角度看,贾宝玉的形象就不仅仅是可爱,他所有小儿女式的举动都闪现出人性的光芒,这个形象承载了曹雪芹的全部欢乐与痛苦。贾宝玉“带着光辉和芳泽出现在中国文学里”,中国文学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四
《红楼说梦》第三个要讲的,是如何看待众说纷纭的后四十回。这主要写在《冲破瞒和骗的罗网》一篇中。
面对无数对后四十回的否定,舒芜先生与许多肯定后四十回的评论者一样,坚定地认为,后四十回正确地传达了曹雪芹的原意,符合作者的初衷。
他将后四十回一分为二,首先——
整个宝黛故事,整个大观园故事,整个《红楼梦》故事,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悲剧结局,正是要由这个结局来回顾整个故事,才会显出它是一首凄厉的长诗,一阕悲怆的交响乐。否则,如果像专家所论证的,说曹雪芹原意只是要写黛玉因病早死,宝钗于是自然而然与宝玉结了婚,如果结局真是这样,读起来真不知道整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干什么要写这一大篇故事了。
这是点出后四十回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保留了黛玉抱恨而亡的悲剧大结局,宝钗在瞒和骗中与宝玉成婚,她也是极其不幸的。
但是,后四十回艺术的贫瘠也是极明显的。它文笔枯窘,所有在前八十回已深入人心的人物,进入后四十回,言谈忽然都失去灵气,变得淡而无味。贾府也明显失去大家气派,森严的贾府变得随便什么人只要有个由头,就能轻易地登堂入室,与原来高高在上的贾政老爷随意攀谈,轻易就能面见清高的林妹妹,这是在前八十回绝不可能出现的。
可是同时,后四十回又有一些篇章,艺术感染力明显超出其他文章,风格与前八十回一致。因此,舒芜同意这样的判断——
高鹗据曹雪芹残稿续完《红楼梦》,好的篇章大致可断为曹原稿,譬如:抄家和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两章,非大家曹雪芹写不出。而那些艺术差、贵族气象小些的则为高鹗所补。
可是,尽管艺术不足,后四十回在展开矛盾、深化矛盾方面显然比前八十回更尖锐、更积极,而恰恰思想的深化与艺术功力的不足又使小说浅白直露,失去含蓄之美。
但是归根结底,尽管后四十回有种种不足,它毕竟保留了悲剧大结局,尊重了曹雪芹的原意,使《红楼梦》区别于所有才子佳人的小说。他认为,仅凭此一点,后四十回就足以不朽:
中国有那么多瞒和骗的文艺作品,有那么多“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只有一部《红楼梦》,只有《红楼梦》后四十回,写出了一个伟大的悲剧结局,总算把瞒和骗的罗网冲破小小的一角。
后四十回保证了《红楼梦》思想上的前后统一,正如聂绀弩所说:“对于《红楼梦》说,对于曹雪芹说,甚至对于《红楼梦》的读者说,高鹗‘功不在禹下’。”(《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辨伪存真》)
这样的分析,依然是将《红楼梦》放在大的、恰当的文学背景中去评价。背景是沉重的、铜墙铁壁混沌一片的,而《红楼梦》的丰姿超尘拔俗,划开铜墙铁壁,惊艳绝世地凸显于混沌之上,我们欣喜地发现,背景越深阔,它的光芒越强烈,它的不同凡响和伟大越夺目,这真是伟大作品的特点!
不过,据周绍良考证,历史上的高鹗不仅热衷功名利禄,而且不尊重女性,以他的思想,断写不出后四十回。很可能后四十回基本上是曹雪芹原稿,许多更只是框架,未及修改润色曹雪芹便过世,高鹗只起个将稿子连缀小修小补的作用。
但不管是谁写的,后四十回的悲剧大结局总是必须肯定的。
五
妇女问题是舒芜终其一生念兹在兹的大问题,他在《哀妇人·病后小札》中说:
曹雪芹(贾宝玉)就是最伟大的“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者。他能够充分理解尊重女性,是一方面的原因;他又熟知并且痛恨国贼禄蠹峨冠博带之流如何从骨子里贱视女性,则是另一方面的原因。《红楼梦》在妇女问题思想史上最独特最伟大最无可替代的作用,就在于此。
纵观以上所述,舒芜是将《红楼梦》研究纳入自己的大的思想体系中,纳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中。他的思想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传统,与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正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评价《红楼梦》,才能深刻体会出曹雪芹刻骨铭心的对女性苦难命运的哀痛。
聂绀弩在看过《说梦录》后,做出热烈的响应:
今又看《说梦录》,觉甲乙对话一篇真好,恰有马二,说人的觉醒要通过妇女觉醒;恰有鲁公说宝公身担一切女性觉醒重量,及昵而敬之等等。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你发现了这些议论,竟成伯乐。这是红学的最大空前突破,强于胡文。(一九八三年致舒芜信)
我钦佩《红楼》妇女要通过宝玉之目一一过去之说,前谈人物时,也说到某某是宝玉凭吊人物而未悟及一切妇女一切人一切世界无不如此,则胸中大亮矣。(一九八三年信)
这些话,还有那句已被人多次引用过的诗“舒公即宝公”,都有助于我们以更大的兴致阅读《红楼说梦》。
《红楼说梦》既是亲切、朴实的读后感,又是专门的小说分析,是一个学者从普通读者立场出发所做的思想、艺术的分析,它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富于人性的一部书”这个大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