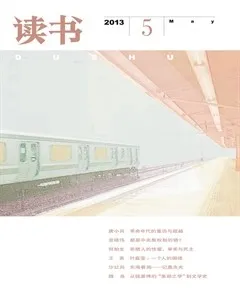奥克肖特眼中的政治思想史
2013-12-29宋澄宇
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政治情势的演变,学界对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兴趣日见浓厚,很多西方政治哲学家的著作受到追捧。麦克尔·奥克肖特《政治思想史》的翻译出版,可谓躬逢其盛。
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堪称二十世纪最有特色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怀疑论者和自由至上论者,也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代表。奥克肖特的论著不仅思想深邃,而且文笔优美,可能是二十世纪英语世界中文采最好的哲学家。
《政治思想史》是一部匠心独运之作,源自奥克肖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授课的讲稿。奥克肖特生前曾准备将其出版,但后来放弃了这一计划。在他去世后,这本书作为《麦克尔·奥克肖特选集》的第二卷,由纳尔丁(Terry Nardin)和奥沙利文(Luke O’Sullivan)编辑出版。
对奥克肖特来说,政治就是决定政府形式和政府事务的活动。因而,政治思想有两个对应的主题:政府权威的来源和构成,以及政府的职能。奥克肖特同时强调,政治经验与政治理论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区别。不应当把对实际的政治信仰的论证与对政治活动的解释(历史的或哲学的)混为一谈。他清楚地表明,他的目的不在于探讨更有效的政治行动的理论,而在于对政治活动给出历史和哲学的解释。
奥克肖特把历史研究描述为一种思考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对事件、人类行为、信仰、观念的解释,必须与它们赖以出现的条件或具体语境联系起来。《政治思想史》展现的就是跟四个相对独立自足的语境相关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研究。具体来说,它是对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中世纪欧洲人和现代欧洲人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思想的探究。
奥克肖特认为,只是到了大约三千年前,“在相当程度上为政治活动提供了条件的群落”才得以在希腊产生。但是他警告说,不要试图发现任何像“三千年连续不断的欧洲政治史”之类的东西。奥克肖特质疑这样的信念:历史必定沿着某个方向移动,或者说,政治思想史中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前进”方向。他认为,历史关系所承载的,是相互蕴含,而非绝对的必然。因此,奥克肖特所愿意提供的,并不是一部“科学地”想象出来的“因”和“果”的历史。比如他认为,古希腊的地理条件,或奴隶制,或他们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导致希腊人必然以他们那种方式来思考政治。
关于希腊人的政治经验,奥克肖特认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希腊城邦的出现标志着政治共同体的诞生。这不仅因为部落的一切特征(包括习俗、神、首领或统治者等)都被城邦彻底改变了,而且因为城邦提供保护、祭祀和法制,尤其是提供“言说的生活”。在奥克肖特看来,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因为“以说服来统治”的概念由此得以产生,这便是“政治”的起点。虽然在集会地(agora)发言的只是少数有公民身份的人,但是,去到公民会议上“听取政策商议和法律裁决”的听众,那些等待被说服的人,也可以说是参与者。
关于希腊人的政治思想,奥克肖特十分推崇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确立了“人类活动的等级版图”,“后来的思想家只在上面做过很少的改动”,这幅版图提供了“两千年来一切欧洲政治思想的语境”。与一般思想史著作迥异,奥克肖特将亚里士多德放在柏拉图之前加以介绍。奥克肖特对此给出的理由是,在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经验所激起的智性回应中,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试图分类和合理化)比柏拉图更接近希腊政治经验的主流。
亚里士多德把“公民”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友谊”,即一种平等关系,产生和维护城邦中这种人为的平等,凭借的是对话、说服而非武力。奥克肖特认为,正是这种通过讨论达到互谅互让的过程成就了希腊人的“政治”。当然,希腊的政治是很不稳固的,它经常要面临奥克肖特所称的“口舌之争”与“兵戎相见”之间的严峻抉择。但是,奥克肖特认为,希腊政治的存在至少显示了和平对话的一次胜利。尤其是雅典城邦出现的民主政体,使最初的公民会议“转变成了统治权威”。
奥克肖特认为,在大多数方面,罗马人的政治经验完全不同于古希腊人的政治经验。因此,用“古代世界”这个断语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归并到一起,“是有史以来最具误导性的归纳之一”。奥克肖特对罗马人的政治经验大加赞赏:“说罗马人是唯一展示了真正的治国天才和政治天才的欧洲民族,并非夸大其词。”他把罗马人描述为“一个非常有能力从经验中学习的保守民族”,并声称,应当把在欧洲人心目中播种“法律”观念的功劳归于罗马人。
奥克肖特指出,对家族的强调是罗马人的显著特征;使罗马这个大家族联合起来的原则,不是像希腊的政治共同体那样基于“参与一项共同的事业”,而是“对古老习俗(mos maiorum)的尊重,对法律的尊重”。这一原则的力量主要源自它的宗教特征,奥克肖特认为,“罗马人民就是一个由宗教团体组成的宗教社会”,罗马政治“始终都有宗教仪式的成分”。
这跟奥克肖特十分关注“法律”(lex)这一关键术语是吻合的。根据他的考察,lex概念出自更古老的fas(宗教责任所强加的法律)和jus(作为一种道德法则的法律)。lex的意义在于,它使“制定法”、“主权权威”等希腊人不熟悉的概念得以产生。奥克肖特认为,罗马本质上不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更是一个民事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它把“法定权力”的概念融入了“权威”的概念。命令或统治所需要的法定权力,不是作为武力(potentia)的权力,而是在不同政府官员中分配的“做某些事情的权利和义务”。民事共同体的观念在雅典表现得不像在罗马那么清晰。
奥克肖特认为,基督教的出现让罗马人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对支撑原有政治经验的基本“神话”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在他看来,随着罗马公民身份普及到整个帝国,罗马衰落进入了重要阶段。因为个人与罗马城邦“神话”之间的联系越小,他就越难体验到它是一种行为的激励。换句话说,罗马世界走向终结是由于其居民丧失了捍卫它的意愿。
奥克肖特的政治哲学基于一个基本的判断:“政治思想的一切区别中,最根本的区别是‘武力’或‘暴力’与‘权威’之间的区别,是武力(potentia,它是物理的)与法定权力(potestas)或权威(auctoritas,它是精神的)之间的区别,是‘力量’与‘权利’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政治与纯粹的暴力是两码事,而且暴力常常可以摧毁政治;政治权威或者来自法定权力,或者来自别的方面,但很少是暴力。
在《政治思想史》的最后几讲中,奥克肖特致力于辨析两种关于政府职责的信念的差别,即他所说的“目的统治”(telocracy)与“法治”(nomocracy)之间的差异。所谓“目的统治”的信念,即认为“政府的恰当职责就是组织其国民追求一个单一的、预先谋划好的‘目的’或‘目标’”;而“法治”的信念则认为,政府的职责应当限于“为国民追求各自选择的不同目的创造条件”。奥克肖特对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统治观念的分析是发人深省的。尤其是他对目的统治信念不同版本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模式”的政治特质。
在奥克肖特看来,政治是对暴力的否定。但是,从《政治思想史》勾勒的欧洲政治图景来看,从古代到现代,政治权威和权力的构造日益壮大,到了现代时期,目的统治乃至极权政府无论在经验还是在理念层面均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趋势。虽然奥克肖特看到,“现代政府异乎寻常的巨大权力更多要归因于战争,而不是任何别的环境”,但他仍然不愿意承认,暴力是政治权威的天然构成要素(这让他对政治权威的解释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虽然他也看到,目的统治与“民主制度”的结合产生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统治方式(这与他的法治信念背道而驰),他却没有认识到,“必要的恶”必然有自我膨胀的趋势,最终会成为掌控一切的“全能的恶”。难道“恶”真的必要吗?难道“恶”真的能够成为“善”的黏合剂乃至守护神?在超国家生活日益成为常态的今天,也许我们应当从道德哲学的角度(阿克顿勋爵认为,政治学是道德哲学的应用科学)而非政治权威的实证分析的角度,寻找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