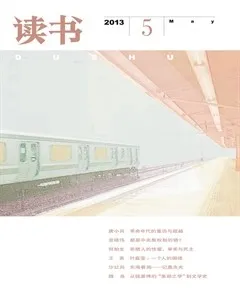查士丁尼与人性的幽暗面
2013-12-29肖洪泳
公元五世纪,当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汹涌人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的时候,定都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仍然顽强地挺立下来,并且在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大帝统治的数十年间,一度取得了伟大的军功。查士丁尼不仅重新从汪达尔人手中收复了非洲省,从哥特人手中征服了意大利的大部分,也恢复了东罗马帝国在西班牙南部的统治,地中海几乎再次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不仅如此,查士丁尼还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宏伟而美丽的圣索菲亚教堂,创立了一所大学,并且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还组织法学家对大量纷繁复杂的罗马法律以及法律学说进行梳理,着手《罗马法大全》这一伟大的法典编纂事业。由《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学说汇纂》、《查士丁尼法学阶梯》和《查士丁尼新律》四部罗马法巨著组成的“国法大全”或“民法大全”,不仅代表了罗马法发展过程中的最高水准,而且为西欧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准备了充分的历史养料,为资本主义两大法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根基。
出于这样的文治武功,查士丁尼不仅生前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死后亦受到历史学家无尽的褒扬,即使二十世纪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韦尔斯,也称誉其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富于组织能力的人”。事实上,与查士丁尼同时代并且曾经担任过东罗马帝国要职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就在《战史》一书中记述了查士丁尼为恢复昔日伟大的罗马帝国疆域而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并在《建筑》中极力讴歌甚至吹捧查士丁尼在帝国各地进行的建筑活动。其优美典雅的文笔所树立起来的查士丁尼形象,不仅高大伟岸,而且栩栩如生,颇为动人,一直成为后世研究查士丁尼及其时代矢志不渝的信念。然而延至十七世纪,也正是东罗马帝国这一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其一部从未公开面世、记录查士丁尼劣迹的历史手稿顿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在这部发黄的希腊文手抄本中,普罗柯比一改《战史》与《建筑》两书中赞美甚至谄媚查士丁尼的写作风格,以极其犀利甚至污秽的语言大肆辱骂查士丁尼及其皇后塞奥多拉。最初发现该书手迹的教廷图书馆管理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至于一度精神紧张而神经兮兮。
在这部被后世称之为《秘史》的历史著作里,普罗柯比极尽批评或谩骂之能事,那个在《战史》、《建筑》等书中曾被誉为“伟大的立法者”、“伟大罗马帝国的保护者”的查士丁尼,几乎成为“蠢驴”、“白痴”、“野兽”、“低能儿”、“人形恶魔”、“杀人魔王”、“披着人皮的魔鬼”之类的代名词。面对如此天翻地覆的形象反差,不要说当初的教廷图书馆管理员瞠目结舌,即使今天我们这些稍有罗马法常识的法科习学者亦惊讶莫名。难道这是一部托名普罗柯比的伪书?然而经过长时期的历史争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秘史》一书与《战史》、《建筑》在写作风格上的一致性,并且其所记述的事件亦大多可为六世纪东罗马作家的作品所证实。
看来,普罗柯比写作《秘史》是有深思熟虑的,这就是他开篇就指出的:“当某些人在世时,按照历史家本应做的那样去记载其真实言行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他们的间谍就会发现,并且置我于最悲惨的境地……这就是我为何在前几部著作中被迫矫饰历史并隐瞒自己真实观点的原因。”如果这不是普罗柯比别有用心的一种矫情,那么《秘史》一书中所暴露出来的查士丁尼形象,恐怕恰恰印证了西方世界一直以来对于人性幽暗面的一种警惕。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曾用“人们睡眠时活跃起来的欲望”指称这一人性的幽暗面,并认为这一可怕的非法的欲望事实上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即使在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心里都有。《旧约》中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更是深刻揭示了人性幽暗面的存在: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一种趋向上帝的一点“灵明”,但是由于人对上帝的叛离,遂致“灵明”汩没,黑暗势力遂在人世间得以伸展,从而造成人性与人世的堕落。张灏先生正是从这里发现了西方世界对于人性正负两面的“双面性”了解,即一方面承认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有灵魂,都有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人又具有与生俱来的一种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所以,人可以得救,也可以不断向上,但却永远不能变得像神那样完美无缺,相反,人的堕落性却是无限的,随时可能的。张灏先生从而提炼出“幽暗意识”一词,专门用以指称人类对自身幽暗面的一种认识,并将这一认识与西方世界的民主传统和自由传统联结起来,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
的确,一种深入人心的幽暗意识可以随时提醒我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从不因地位的高低或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换句话说,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没有谁比谁更高尚。阿克顿勋爵进而认为,要了解人世的黑暗和人类的堕落性,最值得重视的因素就是权力,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阿克顿甚至斩钉截铁地断言:“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从这样的幽暗意识出发,要使拥有权位的人得到约束,就不能单纯幻想道德的力量,而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西方世界“权力分立制衡”的宪政基石,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幽暗意识这一人性警惕。
相反,幽暗意识的阙如或隐而不彰,人们就易于对人性抱持一种乐观精神。中国古代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正是从正面肯定人性成德的可能性。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坚定信念,恰恰来自于人性成德的期待。所以孔子所理解的政治,无非就是一个“正”字而已,即圣王率先“正身”而后“正人”,从而达到秩序井然、天下大治的崇高理想。出于这种人性成德的乐观精神,儒家虽然也意识到现实具体的个人是容易堕落的,但仍深深笃信通过修身养性的“内圣”功夫,足可以达到成德、成圣甚至成佛的目的。而一旦一个人因修德而成圣人,理所当然便应该成为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或成为不良之恶政的批判者。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批判者,其依据都来源于成德或成圣这一期待。这样,儒家就不只是将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几乎就是将政治完全等同于道德。这一唱高调的姿态不仅消解了法律制度存在的正当性根基,同时也由于对最高统治者的美化,丧失了抵抗最高权力的内在意识或有效途径。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一方面充满温馨的道德柔情,另一方面却又是饱受肆意的君主专制这一内在困境的深刻根源。
当然,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但肯定人性堕落的幽暗意识,至少可以迫使我们勇敢面对复杂的人性,同时也仍然为道德情操留下了期待的余地。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普罗柯比当初抱着什么样的目的非得一改《战史》、《建筑》中对查士丁尼的誉美而为《秘史》中的谴责,都可以引发我们对于人性两面性的深深思考。其实就是作者普罗柯比本人,其对查士丁尼前恭后倨的矛盾心态,本身就是人性两面性的一面镜子。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一种阅读历史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