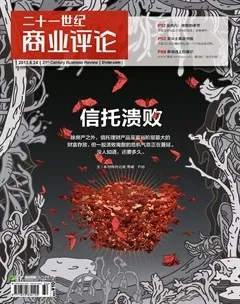刘氏孤儿
2013-12-29刘黎平
汉文帝刘恒被认为是汉高祖刘邦最完美的继承人,刘恒完美地继承了刘邦的休养生息政策。然而,若认真审视,就会发现,这是一对没有良好交集的父子,父亲刘邦并没有留给儿子刘恒多少良好的政治遗产,儿子刘恒也一直未能顺利收割父亲刘邦种植的政治作物。
从家庭空间来看,刘恒的母亲薄氏在刘邦的女人当中,是属于边缘地带的一个,刘邦也将他们母子边缘化。在公元前196年,刘恒和母亲被分配到远远的北方,刘恒被分封为代王。刘邦对儿子刘恒的态度就是:安置而已,没有把他当成可能的继承人之一。刘邦这样做并没有错,但他没有预料到,历史这匹马的缰绳有一天居然会转到刘恒手里。
公元前179年,刘恒作为老功臣们第二阶梯的人选进入长安。两代人亲情上缺乏互信导致政治上缺乏互信,一下子面对父亲这么庞大的政治遗产,刘恒表现出来的不是兴奋和激动,而是恐惧和犹豫。在动身前,刘恒要通过打卦来打消自己的疑虑,接近长安时,他还是不相信自己能接手那位陌生的父亲的遗产,于是先在郊区住宿,打听动静,“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以至于到了长安城城门口,面对父亲遗留下来的政治班子周勃陈平等人,他战战兢兢,太尉周勃希望能和他建立私交:“愿请间言”,即借一步说话,刘恒的谋士宋昌用“王者不受私”拒绝,其实正好证明了刘恒缺乏与父亲的政治班子进行亲密接触的信心。父亲刘邦没有给这个边缘化儿子的接班做任何铺垫。从政治角度而言,刘恒是个孤儿。
刘恒一直未能很好地消化父亲留下来的政治班子,他和这帮政治老人所追求的不是磨合,而是相安无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如此描述汉文帝刘恒上台时期的政治姿态:“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谦让都还来不及,哪里还来得及有所拓展和施展?这种谦让其实是对父亲政治遗留势力的谦让,再直白一点,就是对父亲的谦让。

例如,有一回,刘恒似乎想改变汉初时期那种“萧规曹随”的因循管理方式,他问内阁总理周勃,大汉帝国一年的司法案件有多少,生产总值有多少,已经习惯含糊管理的周勃“惶愧,汗出沾背”,这次谈话似乎是刘恒要改变工作风格的一个信号。刘邦政治班子的重要成员陈平喝止了这种倾向,他教训年轻的管理者刘恒说:具体的工作业绩,你去问具体的部门,作为汉帝国内阁总理,只抽象地负责“理阴阳,附百姓”。刘恒在父亲遗留的政治班子面前投降了,其实也是向父亲的行政风格投降。
刘恒也一直未能很好地打理修改父亲刘邦的政治架构。刘邦留将军功分封制的帝国修改成刘姓分封制的帝国,不管是异姓分封还是宗族分封,这对帝国的统一都是一个威胁,刘恒最大的政治操作空间就在这上面,他想打造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而代表他心声的人物出现了——贾谊。
在贾谊的参谋下,刘恒着手修改父亲留下的帝国架构,打造自己的政治班子,改变一些初期的法律条文,尤其是将集中在京城的诸侯遣散到地方安置。
然而,其父亲刘邦的政治班子还很健康,很强壮,刘恒的则还处于偷偷成长的空间。一班政治上的老前辈再次让刘恒屈服,贾谊被排挤在政治核心势力之外,被赶到了地方“卑湿”的长沙。
在此期间,刘恒一直想与新生政治班子保持接触,他屡次召回贾谊面谈,然而却只敢和贾谊谈鬼神,李商隐感叹“不问苍生问鬼神”。在那个转型政治未成熟的时代,不谈鬼神又能谈什么呢?
可以说,汉文帝这位千古传诵的优秀管理者,其实也一直处于其父亲刘邦政治遗产的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