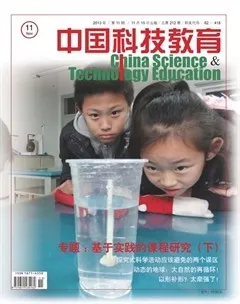科学人文是一种精神
2013-12-29马丽华
一百多年前,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Richthofen,1833—1905)在他的中国之行后如此论断: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学科或可有所成就,唯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
这番话,最早由杨钟健先生转述给他的学生刘东生,刘先生又告知更多弟子和大众,以此为警示,激励后来人。好在经过近百年数代人努力,情形大为改观,李氏所言显然过时,中国的自然科学长足发展,其中黄土研究和第四纪研究跻身于国际地学前沿,像刘东生先生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已不仅仅是中国地学界的泰山北斗,在全世界,已然实至名归的里程碑人物。
借用这一典故,是为反观相应的科普写作。同样是白手起家,只是起步更晚,半个多世纪里固然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就个人经验,还记得少年时捧读《十万个为什么》时的心情;及至成年,从大众媒介、出版物中接触到科学人文和生态环保一类现代理念;就近的例子,也可列举当下的科学普及出版社:该社正在推出的“院士传记”和“科学·文化与人经典文丛”两套丛书,从中可见辛勤努力。然而就总体而言,相比我们一线的科研已经起飞,虽距科学大国尚有不近的里程,毕竟有了高度和速度,而应当紧随其后的科学普及工作——这里专指文学形式的传播而言——不能不说滞后,还在地面滑翔:总量稀少、精品稀缺、人才稀见,处于中国当代文学边缘,还有足够长的路要走。
在此聊可一辩的是,比之纯文学,科学人文的原创在文科人士那里,由于“科学”要求增加了特别的难度,不是想写就能驾驭得了的;对于理科人士,由于原因种种,也许更属意于涉笔论文。就这一意义来说,金涛先生的创作实践难能可贵,恰好是文理兼备:既有地质学出身的专业训练,旁及天文地理;又有记者生涯的历练,行万里路的博闻广见;还曾从业出版,具有出版家的宏观视野和职业敏感。所以他的科学散文耐读,文笔精到、文采斐然自不必说,难得的是字里行间闪烁的知性光芒——古今中外,钩沉索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会贯通,常识的传播是信手拈来的,其中不乏多学科进展中的新知,不乏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跟随他的游记篇什,不啻一次知性之旅。
在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人类文明正在接受考验和挑战。这样的命题过于宏大,我们能做的仅仅是那么一点点。就如今天的研讨会,不限于对个人作品和某套丛书的宣传促销,作为科普出版机构,潜台词应当是“我们在努力,在呼唤”,在标举一面旗帜——努力尽职,呼唤更多更好的科学人文原创之作。毕竟,科学是一种精神,人文是一种情怀,需要修为和建树,是一份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