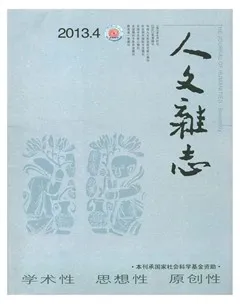苏格拉底“舍生取义”之处境
2013-12-29赵卫国
内容提要 苏格拉底因虔敬而决断,毕生践行神的使命,以讨论知识为手段,旨在验证神的谶语,由于实践或行为的必然性与知识或逻辑的必然性相冲突,他背离了公众意见或知识所建构的规范,因而陷入孤独而赤贫的处境之中,而公共知识强大而隐蔽的力量注定了苏格拉底必死的命运,苏格拉底对于死的泰然任之并非功利或价值选择意义上的“舍生取义”,而是虔敬处境中对神旨的遵从,对于我们现代人有意义的,是其对人的有限性的透彻领会。
关键词 处境 决断 公众意见 虔敬
〔中图分类号〕B50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014-07
苏格拉底事件通常被描画为“舍生取义”的典范,据称他曾得罪过民主派和寡头,更重要的是,他为了追求“美德”、“正义”、“勇敢”等“定义”而与众人辩论,因树敌甚众最终被判以死刑。按照传统哲学史的一般描画,他对定义的追求在柏拉图那里转化为更加客观化的“理念”或“相”,到了中世纪和近代又被转化为对更一般化的“共相”、“类”,最终直至“规律”、“普遍性质”等知识的诉求。因此,苏格拉底追求定义就是近代追求普遍知识、寻求确定性之肇始。比如尼采抨击现代性而提到苏格拉底时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才有他所谓的“偶像的黄昏”。在知识论背景下理解,苏格拉底事件起因于追求真理,而真理本身到了近代同样被知识化,“科学”的形式是本来就客观存在着的真实,“哲学”思辨的形式是人类无穷建构并接近着的理想,苏格拉底就是为了弘扬正义或追求这样的真理而丧命。同样的解释我们也给予布鲁诺,说他为近代科学而献身。然而,这是否只是“我们”的“事后”解释,而一切科学研究都只能是密西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决定苏格拉底之死是否还有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不是事后知识性分析和解释所完全能够涵括,但又具有其非逻辑、非知识的、当下的某种必然性,就像古希腊人所惧6bb3f9718accee3e2b81a1185d930bc5怕或崇拜的命运。列奥斯特劳斯曾说“任何一部柏拉图对话中的讨论,都只是对话的一部分。讨论、言语、logos(逻各斯),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ergon(行)、行为、行动、对话中所发生的、角色在对话中所做的和所遭受的。logos可以结束于沉默,而行动则可以揭示言语所遮蔽者”。①我们根据通常排在柏拉图对话最前面的《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三篇,被认为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紧扣文本,进入苏格拉底在事件中的当下“处境”,或许能够发现更多。
一、苏格拉底的孤独处境
《申辩》篇的第一句话,甚至第一个词,就为我们暗示出一种孤独无助的处境。“雅典人啊,你们如何受我的原告们的影响,我不得而知;至于我,也几乎自忘其为我,他们的话说得娓娓动听,只是没有一句真话”。②③⑤⑥[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1、67、67、68、58页。第一个词是用希腊语的呼格表达的:“雅典人啊”。这样的一呼,势必产生一问,苏格拉底本人是谁?他不是雅典人吗?后面他也紧接着说:“至于我,也几乎自忘其为我”。由此可见,此时要对雅典人申辩的苏格拉底,已经超离于雅典人之外,而雅典人是一个政治概念,这就意味着,他本人已不再是雅典城邦公民了。我们知道,西语“政治”一词就来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原本就是指城邦中的公民参与统治、管理、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总和,简而言之,与大家一起生活,作为公民而不仅仅是个人。在这种共同生活中,人们建构各种狭义的政治制度、伦理规范、知识体系等公共的框架。而这种知识化建构一旦形成,各种具体事件、情况或对象只有在符合建制的情况下,才可以得到解释和把握。传统哲学作为存在论,只不过更上一层,从所建构的知识整体体系出发解释具体事物之存在。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就是说,人首先是城邦的动物,符合公民标准,比如到一定的年龄,认同并遵守城邦的伦理、法律、政治规范和宗教信仰等,广而言之,被公共知识所规范者,我们将其认定为人。这就是人的社会化,同时也可以说是知识化的认定。
申辩的苏格拉底既然自绝于城邦,那么他是谁呢?他自称是马虻,与雅典人对立的人,“象马虻粘在身上,良种马因肥大而懒惰迟钝,需要马虻刺激”。②然而,这个令人讨厌,不合规范的马虻,与雅典城邦和雅典人对立,却是为了让整个城邦警醒而不至昏睡,“你们如果杀了我,不易另找如我之与本邦解不解之缘的人”。③但如果谁要与城邦、与公众保持这种若即若离、藕断丝连的微妙关系,他所面临的一定是与众人对立的孤独,以及与财产无缘的贫穷。如果我们联想一下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样的人无非就是类似于逃出洞穴的自由人,或者说,哲人。这里要注意的是,哲人切不可理解为我们现代人脑海中分工了的专业哲学家。哲人“单独”走出洞穴看到了真理,他的处境是孤独的,但是幸福的,他本不愿意回到洞穴中与阴影或只识阴影之人为伍。而如果他突然又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毅然返回洞穴试图解救囚徒时,就必然遭受囚徒们的怀恨和敌意。《理想国》中描述到:“要是把那个打算释放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上面去的人逮住杀掉是可以的话,他们不会杀掉他吗?”——“他们是一定会的”。[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5-276页。脱离了众人的孤独者还必然要与贫穷相伴,因为社会关系本身就包含着与物的各种法权关系,脱离社会关系同时就意味着不得不与物、与财产无缘,沦为真正的孤独,绝对的赤贫。柏拉图《理想国》里面所对哲人王的要求,就是缺衣少食,没有财产,甚至无妻无子的绝对孤独者,据传,与苏格拉底的实际生活所不同的,无非就是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因此,当他为自己被诬陷与智者辩护时,苏格拉底说“告我的人……说我索要报酬。我想,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我说实话,那就是我的贫穷”。⑤那么,苏格拉底处境为什么如此孤独呢?因为他背离了城邦和大众,不顾家庭、城邦等公共性的义务而进行了一种本真的决断,“为了这宗事业,我不暇顾及国事、家事;因为神服务,我竟至于一贫如洗”。⑥这就和柏拉图所描写的最终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深明“大义”而返回洞穴,“试图”或“为了”解救囚徒的哲人王略有不同。而苏格拉底以独特方式所践行的、直至为之献出生命的所谓“事业”,以广义知识眼光看,恰恰可能是不务正业,那就是:敬神,以实际行为去侍神。
二、虔敬所导致的被动决断
苏格拉底受审前,在王宫前廊遇到了游叙弗伦,据说是一个经常被人讥笑的占卜者,《游叙弗伦》篇就是向此人讨教“虔敬”,因为苏格拉底被指控的首要罪名就是慢神。按照通常的说法,本篇中苏格拉底是在追求虔敬的“定义”或知识,并且和其他对话一样无结果。但实际上我们认真阅读就不难发现,对话中恰恰处处表明,虔敬根本就不是知识,虽说其中也谈到:“虔敬是事神之术”,⑧[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31页。“我懂得,似乎是指对神的侍应”。⑧但本篇主要传达的是一种神人感应的关系,以及人在这种关系中虽有主动,但主要是被动的处境。游叙弗伦对苏格拉底何为“虔敬”的第一次回答丝毫不假思索,斩钉截铁:“我说虔敬就是做我方才所做的事”。②③[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13、15页。也就是,此时此地,当下所做之事,用不着思考,无需逻辑。遗憾的是:按通常传统的知识性理解,苏格拉底对话最初的答案往往最不具“真理”性,就像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个概念“存在”是最抽象、最贫乏的。可是在《游叙弗伦》篇里,讨论“虔敬”最关键的部分,则首先引用“携者与被携者,引者与被引者”之间的关系,意在表明携着与引着,较被携着和被引着的优先关系,由此引申神人感应关系中神人的不同角色。神在这种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动地位,这表现为“见喜于神者”先于“神所喜者”,意思是:神所喜爱的东西,不是因为那东西本身,或其某种性质、功能而招神的喜爱,这样,神的意愿将被外物所牵而处于被动,而是反过来,只因其被神所喜爱,所以那个东西才是招神喜爱的,或者说,那事才是好的、善的等等,这样,神具有完全的主动性。这里和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思路一致,并非某事物因本身之善恶而决定意愿,相反,是理性决定了意志之所指是善还是恶。于是,人的虔敬是否被神所喜爱,人自身毫无决定权,人只能以虔敬的实际行动,消极地承受神之喜爱,在这方面,人完全处于被动。但对话中同时,甚至更早地也强调了另一方面,当下的“虔敬”先于“见喜于神者”,这就把人的主动性彰显出来了,就是说,人,不因神喜,或首先不考虑“为了”见喜于神而虔敬,我直接就“能”以实际行动而虔敬,这是“见喜于神”的前提,而不用挖空“心思”、动用“理性”去讨好神。但这种主动无疑是以前面提到的被动为前提的,换句话说,我也“只能”主动地虔敬,是否最终真的“见喜于神”,则丝毫不取决于自己。
除被动特性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神人感应关系里面,从神的角度看,神所喜欢的东西没有道理可讲,严格说来,不是因为……而喜欢,而是无缘无故,那东西被神喜欢,同时就“是”其所喜欢的东西,这里虽然也可以、甚至通常用“因为……所以……”这样的关联来“表述”,但并不是严格的逻辑的、知识性的推论,正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样。另一方面,人的虔敬本身就具有独立价值,并不是考虑“因为”虔敬是神所喜者,“所以”我虔敬,那样就成了康德所谓的“伪侍奉”。虔敬就是无因果的虔敬行为本身,人切身地、直接地、当下地“进入”或“处于”这种处境之中,不做功利的、价值的、伦理的,一句话,知识性的考虑,先思考、后行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喜见于神。进入或处于这种处境,对于人来说就是一种决断,而且是“被动的主动”决断,尽管决断本身从人本身“下决心”方面意味着主动,但比起人的日常知识性主动建构来,决断更多的是被动的、虔敬的,是实际的被动―主动的“辩证”行为本身,而个体的实际行为有时与公共性的理论思考或规范相悖,显得不近常理或不合逻辑。
三、背离大众知识与知识的隐蔽力量
全部这三篇苏格拉底对话中,或许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大众的意见”,从公众意见中抽离出来,就意味着反常,而抽离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恰恰就是决断,这种决断在苏格拉底那里由虔敬所引导。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的囚徒们讥笑返回洞穴的自由人,说他弄瞎了眼睛,看不见“最真实”的东西——阴影,判断不出最通常的规律。《游叙弗伦》中也描述到:“我了解了,苏格拉底;因为你说神时常降临告诫于你,他便指控你革新神道,到法庭诬告你一番,他晓得这一类诬告易入大众之耳。我呢,当我在公庭上说些有关神的话,或预言未来的事,他们便讥笑我,说我发疯了”。②“发疯了”就意味着不近常理、反常;“在公庭上说”就意味着常理是公共性的、大众的,因此“易入大众之耳”,宣称“神时常降临”就意味着“神”道道的。按照《游叙弗伦》篇中的描写,当苏格拉底得知游叙弗伦控告其老父时,就连他这个不近常理者也惊叹到:“你的父亲,你这个好家伙”!——“海辣克类士!确实大多数人不知义理何在;我想此事常人不能做的恰如其分,唯有大智高识的人才能”。③这段对话背景是,游叙弗伦的父亲将一个醉酒杀人的凶犯绑起来投入沟中,并及时差人去上报,请示上方如何处置,结果凶犯意外死亡,而游叙弗伦却因此“大义灭亲”,控父杀人,这完全违背希腊伦理甚至我们现代人的一般常理和知识。于是,爱“智慧”的苏格拉底才认为游叙弗伦一定有过人之处,认为他虔敬的无以复加,缠着他追问何为虔敬,“你对虔敬与亵慢如没有真知灼见,就不至于为一个庸奴,控告老父杀人”。[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页。他认为,游叙弗伦既然切实地做出为子讼父这种不可思议、知识和逻辑无法企及的事情或行为,一定是有一种另外的力量,尽管叫做“真知灼见”,但肯定不同于一般知识,是不是对神“虔敬”使然呢,由于他自己被控不敬神,所以希望了解一些与知识不同,但却比知识更真实、更直指人心的某种力量。
决断的力量虽然对于个体真实而有力,但这样的“切身”行为背离了大众所辛苦或苦心建构的知识及其社会规范,相比之下,大众意见力量强大无比,与大众知识对抗将付出惨重代价。《克力同》篇描述苏格拉底入狱并即将行刑前这样说:“但是你瞧,苏格拉底,大众的意见也不得不顾,当前的处境显然证明,他们能为祟,匪小极大,如蒙他们关顾一下”。⑧[古希腊]柏拉图:《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9页。任凭苏格拉底申辩,通过民主表决最终还是消灭了他。除了力量强大之外,公众意见还有隐蔽的身份,这使其更加可怕。《申辩》篇中描述得入木三分,“在你们以前,积年累岁,已有许多对我的原告,说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话。安匿托士等固然可怕,这批人更可怕,我怕他们过于安匿托士等,……请你们记住,如我所说,有两批原告,一批最近的,一批久远的;再请你们了解,我必须先对第一批答辩,因为他们先告我,并且远比第二批强有力”。④⑤⑨⑩[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2、52、52、55、56、68页。第二批是安匿托士等人,那么,第一批究竟是谁呢?他们神秘莫测:“他们单方挂了案,作为原告,从不到案,因为没有被告的另一造出来答辩。最荒唐的是,他们的姓名不可得而知而指,只知其中有一个喜剧家”。④这里深刻地描述了公共状态的奇特状况,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听到一些什么,“大家”都那么说,于是人们纷纷效仿,股票、绿豆、抢盐等等,但当你问究竟谁在说时,只能听到这样的回答,“人们”都那样说。用苏格拉底的话:“既不可能传他们到此地来对质,我又不得不申辩,只是对影申辩,向无人处问话”。⑤但这种“影子”和“无人”丝毫不削减其强大的力量。这里太容易让我们想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描述的常人:“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⑦[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147、149页。在这种共同生活中,我们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比如说苏格拉底慢神、腐化青年,但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每个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人本身。这个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在中又总已经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了”。⑦但“人们”是谁,我们却从不过问。
四、借知识验证神的谶语以自知自己无知
苏格拉底切真地“感受”到了神人感应关系,义无反顾地进入到虔敬之处境中,无视公众意见的强大力量,“万福的克力同,我们何必如此关注大众的意见?”⑧于是,就给自己惹了祸。他坚信神是全知,可是神说“苏格拉底最智”,而“我自信毫无智慧,他说我最有智慧,究竟何?按其本性,神决不会说谎”。⑨为了证明神的谶语,“此后,我——去访,明知会结怨,满腔苦恼、恐惧,可是必须把神的差事放在首要地位”。⑩苏格拉底申辩的主旨,就是“论证”或表白他的所作所为乃服从神的指示,他确实是敬神的,而非被诬告的慢神。但虔敬“感”又非知识所及,只有以实际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虔敬,因此,申辩并不是苏格拉底对于自己的行为事后加以前因后果的逻辑分析,不恰当地说,是对自己实际行为本身的“现象学描述”。可是,事情恰恰又被抛了回来,遵守神的旨意而验证“无人智过于苏格拉底”,却只能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在各阶层人士中,借讨论“正义”、“勇敢”、“节制”等概念或知识进行,于是近代做哲学史的人就说,苏格拉底追求定义或知识。尽管如此,必须指出:知识之讨论,后于虔敬之行为,或者说,只是服务于后者的手段,行为或决断“本身”无可争辩或讨论。《申辩》中明确宣布:“我要向你们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不是空话,是你们所尊重的实际行为”。对于虔敬的苏格拉底而言,相对于实际行为,知识甚至只是些“空话”。
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最终都没有结果。但这种无结果往往被知识化地理解,从哲“学”之超越性角度解读,理想超越现实,理念超越意见,在追求的过程中显现,并在此过程中无穷接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种说法尽管思辨,但仍然持理念优先的思路,最终仍不过乐观地认为,虽然我们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但我们对所要探究的“勇敢”、“正义”、“美德”等知道的更多了,更接近了,知识更丰富了。我们完全不否认这方面的解读及其意义,西方传统的哲学史就是这样解读过来的,但能否换一种思路,或许从中能领会更多的话外之音。其实,我们现代人不妨“头脑简单”一点,苏格拉底的对话没结果,这情况没有那么复杂,只不过表明,作为人,本来就知之甚少。这一点,苏格拉底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由于这样的考察,雅典人啊,许多深仇劲敌指向我对我散布了许多污蔑宣传,于是我冒了智者的不虞之誉。在场的人见我揭穿了他人的愚昧,便以为他人所不知我知之;其实,诸君啊,唯有神真有智慧。神的谶语说的是,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藉我的名字,以我为例,提醒世人,仿佛是说:‘世人啊,你们之中,惟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②③④⑤[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7、70、66、68、71页。很明显,这里的苏格拉底只是“人”的代表,不是苏格拉底比常人意见知道更多,更接近知识,苏格拉底的方法也并非所谓的“真理越辩越明”。这里只要求一种简单而直接的自知之明,要求“人”或我们说“人类”“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由此而进入一种虔敬状态,以便接受另外的“真知灼见”,而“接受”本身就意味着被动,进入一种被动的处境中,警惕日常的、主动的、过分的知识性建构。这里,真正对我们现代人有意义的忠告就出现了,那就是:正视人的有限性。有限性反对人们“接近真理”的知识论想象,哪怕谦虚一点,说“无穷”接近也罢。可见,即便苏格拉底追求定义或知识,也并非其最终目的,他不想知道或接近这些知识本身,对于他来说,更重要的或第一位的,是因真正“侍神”而验证神的谶语,通过其毕生、直至献出生命的行为,或者说,通过他被处死这件事本身,指出或彰显出整体人类知识,或人类本身内在的无知或根本的有限性。只因此,对话对象“无论老少,愿听我谈论并执行使命,我不拒绝,我与人接谈不收费、不取酬、不论贫富,一体效劳”。②
五、处境之必然性
处境中的决断无法知识性地分析和拆解,就如同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实践非知识,理性直接决定意志,无需中间环节,无所谓因果,无以言表。但这并不妨碍决断行为层面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甚至强于逻辑必然性,在苏格拉底那里,特定地表达为受神的引导:“你们要明白,这是神命我做的事,我认为,我为神办此差是本邦向所未有的好事”。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引导理解为“因为”神引导,“所以”我如此这般行为,行为直接受引导,引导直接导致行为,无需思维介入,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讥笑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经常提“神”,“其缘因,你们听我随时随地说过,有神降临于我心,就是迈雷托士在讼词上所讽刺的”。④因为这种不假知识的直接性,从知识角度看就是神秘的,甚至可以诬以“装神弄鬼”。出于同样的原因,后人褒奖苏格拉底时,如果仅从知识角度,赞美他热爱智慧,崇尚理性,这样做,其实和从知识角度对他的讽刺、直至诉讼一样,都没有进入苏格拉底本人接受神旨的处境之中,没有领会苏格拉底处境中的必然决断。“我相信,此事是神之所命,神托梦启示我,用谶语差遣我,以种种神人感应的方式委托我。雅典人啊,此事是真,否则易驳”。⑤苏格拉底用了“相信”一词,以远离“论证”,并直接强调“此事是真”,“否则易驳”。反过来说,如果不“信”此事为“真”,而以知识眼光看,则“易驳”,即有口难言,无以申辩。在克力同最后探监时,苏格拉底说他做了一个梦,“白衣丽人示现于我”,克力同说:“怪梦,苏格拉底。”他坚决地说“不,对我显现明白得很,克力同”。[古希腊]柏拉图:《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9页。因为这种清晰明白,“我们丝毫不必考虑大众怎么质问我们,只要注意那明辨是非邪正的一人和真理本身是怎么说的。……固然可以说,大众能置人于死地”。②⑦[古希腊]柏拉图:《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4、102-103、98页。这充分显示了处境之必然性对抗逻辑必然性的强大力量。“亲爱的朋友克力同,我仿佛真听见这些话,象崇奉渠贝垒女神的人在狂热中如闻笛声;这些语音在我心中不断回响,使我不问其他的话”。②“狂热”中的崇拜者,其信仰的力量远大于逻辑的力量,定会使其“不问其他的话”。
另一方面,从现实的处境来看,苏格拉底也不得不死。控诉他的两项罪名:慢神——引进新神和蛊惑青年——最大的智者,某种意义上讲也没有冤枉他。尽管他极力申辩其敬神,“雅典人啊,我信神非任何告我的人之所能及”,④⑤⑥⑧⑨⑩[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3、70、76、80、65、56、56、67页。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像通常所说的那样,苏格拉底引进什么理性之神,或者基督教意义的上帝,因为上帝恰恰是绝对确定性的符号,但由于其所敬之神并不明确,并且以与人争辩的独特方式表现,不合传统信仰形式。从知识角度而言,处境的神秘性,完全可以任意被解释为引进了另外的信仰。蛊惑青年方面,苏格拉底自己坦言:“如有人,无论老少,愿听我谈论并执行使命,我不拒绝,我与人接谈不收费、不取酬、不论贫富,一体效劳;我发问,愿者答,听我讲。其中有人变好与否,不应要我负责,因为我不曾应许传授甚么东西给任何人”。④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确实将辩论术展示给所有人,而柏拉图后来则极力主张青年人不易过早学习辩证法,因为辩证法和智者的诡辩在形式上一样。“其中有人变好与否,不应要我负责”则表明,确实有他的追随者沦为智者。此外,苏格拉底对话无结论,本来是验证人的智慧有限,但从知识角度看,却和智者们的相对主义、动摇真理结果上一致;就连其证明自己不是智者、不收费而赤贫时的申辩:“可是我没钱,除非你们肯按我的支付能力定罚款的数目。或者我付得起一个命那银币,我自认此数”。⑤也遭到怨恨,被认为蔑视法官,自寻死路。再加上他以实际行动曾得罪了民主派和寡头们,也注定了他必死的命运。
六、处境之中对死的泰然任之
面对必死之命运,苏格拉底自知、认命,并因此表现得无畏。“所以,我的遭遇绝非偶然,这对我明显得很,此刻死去,摆脱俗累,是较好的事”。⑥克力同也赞美到:“我当时感觉你平生尽是乐观,现在愈觉得,当你大祸临头,还是如此宁静,泰然处之”。⑦但如果这种不畏死被解释为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话,就过于片面了。前已表明,苏格拉底与人争辩“正义”并非追求其知识或价值本身,或许后来的柏拉图更偏重于此。舍生取义者往往是以义为先,生为后,“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里明显做了一种价值上的比较,先知而后行,“思考”之后决定以舍生为“代价”而取义,与苟且偷生相比,取义被“公认”为理性的、高尚的决定。但苏格拉底面对死亡这种最不欲的,令人害怕、畏惧的事情的独特态度,不能片面理解为知识、价值层面的高尚选择。他在多处强调,畏死之关键是由于把死当做了知识,而不是切身的事件:“诸位,怕死非他,只是不智自命为智,因其以所不知为知”。⑧对死的知识性无端猜测,使每个人都怕死,即使猜测死后升天,也由于“前途”之不确定而使人恐惧。从知识层面上讲,苏格拉底并非不怕死,虽说“可是必须把神的差事放在首要地位”,⑨但毕竟“此后,我——去访,明知会结怨,满腔苦恼、恐惧”。⑩在《游叙弗伦》中,苏格拉底也表现得和常人一样忐忑:“如果他们认真起来,除非你未卜先知,此案伊于胡底莫能测也”。[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页。作为正常公民,苏格拉底也几乎竭尽全力地进行了申辩,尽管结果不尽人意,因不合知识而适得其反,甚至落得“胡言乱语”意在“舍生取义”以“沽名钓誉”之嫌。“雅典人啊,我此刻的申辩远不是为我自己,如有人之所想,乃是为你们,使你们不至于因处死我而辜负了神所赠的礼物”。类似这样的“逻辑矛盾”申辩中比比皆是。
海德格尔把死称为“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147页。这里所说的不确定,也是指知识层面上死亡事件的不确定性,而“确知”,则只有实际向死的处境中才会昭然若揭。苏格拉底的坦然无畏,就是对于不由知识,而由处境所必然决定的赴死行为而言。但与海德格尔的无神论不同,他的这种无畏还是以敬神的话语表达的。“从幼年起,就有一种声音降临,每临必阻止我想做的事,总是退我,从不进我”。②③④[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8、78、78、78页。在本来就简短的《申辩》篇另外一处又说:“我遇一件灵异的事。经常降临的神的音旨以往每次警告我,甚至极小的事如不应做,都要阻止我做”。②可见,神的意旨更多是消极的阻止和否定,即对一般公众意见说“不”。“你们眼见,当前发生于我的事,可以认为,任何人都认为最凶的”,死被公认为最坏的事,“可是这次,我清晨离家,到法庭来,发言将要有所诉说,神的朕兆全不反对。可是,在其他场合我说话时,往往中途截断我的话。在当前场合,我的语言、行为,概不干涉;我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告诉你们,神暗示所发生的事于我是好事,以死为苦境的人想错了。神已给我强有力的证据,我将要去的若不是好境界,经常暗示于我的朕兆必会阻我”。③这里,“以死为苦境”是以不知为知造成的,而神给予的“证据”并不是逻辑的根据,不保证苏格拉底去“好境界”。 苏格拉底清楚,死:“或是全空,死者毫无知觉;或是如世俗所云,灵魂由此界迁居彼界”。④他肯定不赞成“世俗所云”,那么对于知识而言,死就是全空,是绝对的无,最高的阻止和否定。但这种“无”在行为层面上对每个人都是最真实的,神的暗示通常是阻止,对知识说“不”, 死不从知识角度看,则无所谓苦乐,在苏格拉底的当下处境中,神的旨意无比真实地对他启示:不阻,正是这种真实,海德格尔所言的“确知”,使得他面对死亡“如此宁静,泰然处之”。苏格拉底不是为了正义,故意激怒审判官和陪审团,不是“思虑”长远,为哲“学”之兴盛、为造就柏拉图而献身,泰然任之是行为层面对命运和人之有限性的认可。
总结
苏格拉底的舍生取义不是为了理想或理念,而首先是出于对神的虔敬,因为侍神而决断。而决断必然造就孤独和赤贫,因为孤独的处境背离公共知识,显得古怪而反常,于是申辩本身在知识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为了验证神的谶语,说明人的知识之有限而借助“知识”进行辩论,在后人的知识解释视野中显得是在追求知识或真理,尤其是沿着对柏拉图主流解释的方向,顺理成章是柏拉图的先驱,于是追求普遍性、确定性的殊荣就被加在他头上,以至于被公认为西方的“道德”典范。但通过进入他的切身处境,我们也可以清晰地体会出另外的东西,追求知识只是作为现实可行的手段,服务于他侍神的事业,敬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人的有限性,或者说人的知识建构之有限性的彻查,要求人自知自己无知,苏格拉底以切身行为践行其对神的虔敬,力求“见喜于神”,行为先于知识。这种行为之决断无法真正进行辩解,并且由于履行侍神的义务同时造成了现实的后果,因此苏格拉底之死就成为必然,而他也通过死,完成了他虔敬的一生,直到最后,也是他最后的一句话,他还是坚信:“那么,克力同,就这样罢,就这样办吧,这是神所指引的路”。[古希腊]柏拉图:《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3页。处境所决定了行为之必然性,其强烈程度远大于逻辑所论证的知识之必然性,在苏格拉底的特定处境中,神的指引使他视死如归、安泰恬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张 蓬
* 本文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资助(项目号:NCET-10-0559)。
① 论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施特劳斯,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433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