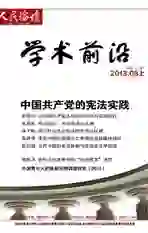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念与实践历程
2013-12-29何勤华
摘要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不仅展示了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卓越能力,而且也具有领导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胸怀和才干。从建党元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届党的领导人,都对宪法的制定和实践给予了高度关注,也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之特色的宪法观念。从中国共产党宪法观念的内涵入手,依次对这种宪法观念与实践的变迁进行了描述、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宪法观念 宪法实践 宪法学 比较法
【作者简介】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导,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研究方向:法律史。
主要著作:《法律文化史论》、《法学史研究Ⅰ·当代日本法学》、《比较犯罪学》、《西方法学家列传》、《西方民法史》等。
在中国,“宪法”一词出现得很早。早在先秦时代的中国古代文献《管子·七法》中,就有宪法的用语:“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另一本古籍《国语·晋语九》中,也有“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的记述。①但此时“宪法”一词的含义,主要是指国家的根本大法,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带有近代宪法的内涵(即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以及为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繁荣确定法律框架等)的宪法的出现,是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宪法观念确立,各国纷纷制定、颁布、实施宪法以后的事情。
与近代宪法的用语是在西方产生的一样,宪法观念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而是在西方伴随着近代立宪主义的勃兴、资产阶级的制宪、行宪实践的展开而形成并逐步传播的。这里,所谓宪法观念,就是指人们,尤其是国家的领导人(统治者),对宪法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看法。其核心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大法,其地位至高、至上;宪法规范国家政权的构造和国家权力的运作,重点在于限制国家公权力的滥用,等等。上述宪法观念,经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洛克(J.Locke,1632年~1704年)、孟德斯鸠(L.Montesquieu,1689年~1755年)、卢梭(J.J.Rousseau,1712年~1778年)等人的倡导、阐述和广泛宣传,成为近代各国立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在近代宪法观念的指导下,美国于1776年推出了《独立宣言》、1787年制定了《联邦宪法》,法国于1789年颁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791年和1793年制定了近代型的宪法,等等。宪法观念和立法实践互相交融,使得欧美在人类历史上,最先确立起了相对于封建专制社会而言平等、民主、进步的法律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项制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法治基础,并进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传播。而中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开始受到其影响。②
在上述近代世界之环境和氛围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非常关注、重视宪法制定和立宪实践。针对北洋军阀提出的立宪主张和立宪框架设计,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宪法观念和立宪诉求,以及他们对宪法观念之内涵的理解。如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明确指出:在西方,是以“法治为本位”,人们对法治的重视,“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盖其国为法治国,其家庭亦不得不为法治家庭。既为法治家庭,则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这是社会文明的表现。而在中国,固有的封建宗法制度给社会带来了四大恶果: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③
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④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人权说”是近世文明的三大特征之一。他认为,在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⑤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此所以欧洲学者或称宪法为国民权利之证券也。”⑥在上述《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引用薛纽伯的话说:“古之法律,贵族的法律也。区别人类以不平等之阶级,使各人固守其分位。然近时之社会,民主的社会也。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不平等者虽非全然消灭,所存者关于财产之私不平等而已,公平等固已成立矣。”⑦在上述《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法律之目的,在强调个人权利自由的同时,就是追求“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⑧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也发表了一系列的宪法政论和时论,如《省制与宪法》(《宪法公言》第4期,1916年11月10日)、《宪法与思想自由》(《宪法公言》第7期,1916年12月)、《孔子与宪法》(《甲寅》日刊,1917年1月30日)等,阐述其宪法观念和宪法主张,分析、比较国外(尤其是苏联)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宪法思想和立宪实践,提出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宪法观念和宪法主张。⑨
只是由于后来(1927年)国共联合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合作破裂,国民党政府大肆屠杀和迫害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利用宪法和法律的手段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的斗争,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只能用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来夺取全国政权,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暂时搁置,仅仅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初步实践,如1931年11月制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1年11月和1942年2月分别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6年4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并对上述西方近代宪法文明成果做出了初步的认可和规定。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移植西方近代宪法观念、宪法文明成果(精华)并将其本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刚建国时对在和平环境下如何领导一个大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项事业,尤其是法治建设还缺少经验,加上党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党的指导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移植西方宪法观念并将其本土化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遭受过许多挫折和磨难,但最终仍然取得了胜利,从而使中国现代的宪法观念和宪法实践跟上了世界宪法发展的步伐,为人类的宪法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本文仅就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和审判独立做些论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确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古代罗马法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
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211年~217年在位)颁布著名的《安敦尼努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包括外邦人)。这样,不同种类的所有权之间的差别就开始消除,罗马人在财产上的法律平等才得以实现,从而带来了所有自由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真正实现。
至近代,洛克、孟德斯鸠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公民在财产权上的平等和政治上的平等进一步做出了系统阐述,并迅速传播至欧美、日本等国家,中国也受到了深刻影响,并为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和司法审判所认可、规定下来。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人类法律文明的精华,是近代宪法的核心价值观,为全世界所有的宪法所认可和规定。我们可以说,在当代,凡是有宪法的国家,必然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的宪法实践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观念(宪法原则)可谓命运多舛,它是经历了众多磨难之后,才被移植进入中国,并扎下根的。
如上所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原则,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曾为党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所大力倡导,也曾为1931年11月7日由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规定。1937年底,毛泽东在因陕甘宁边区发生之“黄克功案件”,而写信给当时此案的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即使是老干部、老党员、老红军,甚至革命功臣,只要犯了罪,也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不能有任何特权,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的思想。这是作为掌握革命政权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观念的认可和强调。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我们党1949年“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指示的落实,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的进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当作“旧法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而受到批判、遭到否定。当时的理论阐述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背离了在阶级社会中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是不能讲平等的基本事实,它是违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敌我不分的为人民的敌人服务的反动谬论。
当然,真理的光辉是掩盖不了的,作为人类法律文明的精华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在1952年遭到否定之后,没过两年,重新又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以及法学界的推崇。在起草、制定和讨论1954年宪法之际,该项原则被人们热烈讨论,最终为我们党和法学界所接受,并在宪法中扎下了根。1954年宪法第85条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然而,中国的政治风云极为多变。1954年宪法所明文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没过三年,到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中,就被当作极右观点而又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再次遭到否定。之后,在20多年时间内,没有人再敢提及这一宪法观念。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1978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李步云的《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重要文章,才明确提出我国公民在法律上平等是必须做到的。该文的观点引起了全体法律人的广泛赞同,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讨论。经过讨论,我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上达成了共识,这一观念才在中国土地上真正扎下了根。1982年制定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虽然1982年宪法之后经历4次重大修改,修改条文达成17处,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项基本原则没有变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核心观念之一。
法治: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法治,是近代西方宪法的又一项核心观念。它最早是由古代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前322年)所提出,他说“法治应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至近代,在西方各国宪法启蒙思想传播之过程中,英国宪法学者提出了“rule of law”(法治)一词;德国宪法学者奥托·迈耶(Otto Mayer,1848年~1924年)等人提出了“Rechtsstaat”(法治国家)的概念;近代日本的宪法学界,则用汉字“法律至上”(发音ほうりつしじょう)对译西语“rule of law”一词,从而导致20世纪初叶日本的“大正宪政民主”运动。
而法国法学界更加进步,在1789年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6条中,明确宣布了“法治”之宪法原则,并强调了“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法”这一宪法观念。在《人权宣言》获得通过后,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10月1日将关于政权组织的条款提交给国王(10月5日获得通过),其中对法治的理念强调得更为明显,即:“在法国,没有任何权力能够高于法律”。这些规定和表述,虽然带有许多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无疑说明:法治这一观念,是近代西方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宪法观念之一。
19世纪末,在世界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如严复(1853年~1921年)、梁启超(1873年~1929年)等人,最早将西方的法治观念引入中国。20世纪初,沈家本(1840年~1913年)在修律变法时,又将法治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移植进入了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之中,同时也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拥护和赞同,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与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对法治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提法。但在1949年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简称“指示”)中,我们对法治等西方法学观实际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指示”强调了必须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的精神来从事法制建设。这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其实也是包括了法治等西方法学观念在内的,因为西方法学观念在当时也被当作“旧法观点”,而“所谓旧法观点,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的法律观点”。在19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中,“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被屡屡点名,指斥为旧法观点,而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并被彻底否定。
受上述历史背景的影响,1954年宪法没有能够直接确立法治的原则。但是,在宪法制定前后全党上下重视法律的整体氛围之下,强调法律至上,得到了宪法起草小组(组长为毛泽东)的肯定。1954年宪法第18条是这么表述法治的精神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这里,宪法使用了“效忠”和“服从”,来表示对民主与法制的尊敬,强调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笔者认为,宪法第18条阐述的就是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原则。
然而,1954年宪法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只过了两年多,就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所否定,并遭受批判。之后,法律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低,法治始终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观而遭受批判和谴责,在20世纪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政法研究》和《法学》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法治”甚至被描述为资产阶级法律“虚伪”、“反动”的特征之一。曾经有学者宣称:“(以‘法治’为核心的)旧法思想中有某些部分,(即使)在发生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在今天已成了不合时宜的文化渣滓。”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以来“左”的路线,实行法治的必要性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1979年12月2日,李步云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一文,正式拉开了“法治与人治”讨论的序幕。讨论的结果,“要法治不要人治”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正是在理论界对“法治”展开讨论,并取得共识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第5条明确宪法的最高权威性。经过30多年的风雨历程,我们党提出的法治观念进一步得到了升华。1999年第三次修改宪法时增加了第5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使法治从一个宪法观念,上升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从审判独立到司法独立
审判独立,在西方一般称为司法独立,是古代希腊留下来的法律文化遗产,其物质形态,就是当时独立于行政机构的法院,如陪审法庭等。此外,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关于政体,关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互相分立、并互相制约的思想,也成为了西方政治法律学界关于“司法独立”的萌芽。至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为了使资产阶级的政权长治久安,开始在理论上提出司法独立的设想。并为各资产阶级国家所欣赏和接受。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顿(Hamilton,1757年~1804年)、麦迪逊(Madison,1751年~1836年)等,就以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为指导,结合美国的革命实践,设计了如何使司法独立有效运作的制度。
在中国古代,既没有司法独立的学说,也没有与行政机关相分离的独立的审判机关。1901年,沈家本受命变法修律,他聘请外国法律专家,翻译外国著名的法典和法学著作,引进外国先进的法律理念和制度,使西方法学观开始在中国传播,而司法独立,就是西方宪法观念中最为重要的内容。1928年民国政府制定六法全书时,也继承了沈家本的立法成果,在法律体系中规定了司法独立的观念和制度。
新中国建立以后,司法独立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观,首先受到了批判和否定。19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其三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批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和司法独立等“旧法观点”。制定1954年宪法时,我们党的领导人对宪法予以关注,开始强调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性,对司法独立这一西方重要的法学观念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了它对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因而将其精神,用中国式的语言,在宪法第78条中作了表述:“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应该说,1954年宪法的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司法独立”,但能够从确保审判独立、强调审判活动只服从法律,以实现司法公正为出发点,做出上述规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非常不容易。
当然,1954年宪法的规定,只能说是“审判独立”,与“司法独立”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一方面,司法独立除了法律意义之外,还具有政治意义,它涉及到了国家政体,而审判独立只是一个宪法观念、法治原则。另一方面,即使在法律意义上,司法独立的内涵也要比审判独立丰富得多。审判独立只解决审判机关不受干预地独立审理案件的问题。但是,法官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之中的,他们也要养家糊口,等等。如何来消解法官的后顾之忧,在心理上和生活上都不受干预地独立审理案件,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就需要有一系列的相应的制度保障。对此,司法独立之宪法观念,设计了各种制度,如法官的高薪、法官的荣誉、法官任职的严格条件、法官就职的庄重程序(如在宪法面前进行宣誓等)和防止法官腐败的监督措施,乃至法官的终身制,等等。
但是,在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为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审判独立的原则,被作为“右派言论”而再次受到批判和否定。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司法独立的原则再也没有人敢提及。期间,1975年的宪法和1978年的宪法,都没有规定审判独立。一直到了1982年宪法,才在第126条再次规定了审判独立的原则:“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982年宪法颁行30年来,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修改,但此条规定一字未改地保留在现行宪法之中。这说明,审判独立也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宪法观念的基础。
虽然,司法独立的原则,至目前还没有被规定进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之中,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有些场合已经提出了“司法独立”的观念。如温家宝于2012年9月1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坚持司法独立和公正,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因此,我理解,作为宪法观念的司法独立,已经得到了我们党的认可。虽然,在法律层面上,从审判独立,到司法独立,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体现了在确保司法公正上的一个飞跃:审判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初级阶段,与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相适应,我们目前也只能以审判独立为目标。等到这个目标实现了,我们再争取早日实现法律层面上司法独立的目标。
宪法观念和宪法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念和宪法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普世价值。一方面,我们党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具有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严谨的学术立场和科学的洞察能力,可以将西方历史上的宪法观念和宪法实践成果移植进入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实践服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执政党之一,90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将其锤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有智慧的、有自信的政党。20世纪30年代,我们党在世界上首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80年代,我们党独创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开放的国策,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西方所有的宪法文明成果移植进来后予以本土化,整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的宪法文明的进步作出我们的贡献。
更进一步言,如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对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行检视、梳理、辨析和改造之后诞生,并得到世界公认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将会对人类所创造的所有宪法文明成果进行检视、梳理、辨析和改造之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予以实践、推进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面前,没有任何理论和学术的禁区,同样道理,在一个成熟的、有理论自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面前,也不会有任何理论或学术上的禁区。因此,不仅以上所述的在西方诞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审判/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等宪法观念,我们党已经将其引入中国,成功完成了其本土化的工作,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深入探讨的宪法观念,如“三权分立”、“宪政”等,我们也应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解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里的问题是,对于在近代西方形成的各项宪法观念,仅仅简单地划定一个禁区,哪些“姓社”,可以研究,哪些“姓资”,不能触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宪法的实施和完善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要走在世界最前沿,必须广泛参考、研究各个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我国宪法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宪法观念,一项宪法原则(如三权分立等),在西方能够实行几百年,虽有小修小补,但大的框架、基本要素没有改变,总有它的道理在内,不能视而不见、轻易否定。
我们对这些宪法观念,必须逐项地进行检视、梳理、辨析,将之与中国当下的国情相结合,做出一个评估:完全适合的,照搬,“拿来主义”;不完全适合的,予以改造,使之适合;完全不适合的,进行分析,阐述清楚其原因,再予以扬弃、超越。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及上面分析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审判/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都是经过这样的过程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扎下根的。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成为人类宪法文明的守护人和传承者,才能通过自己的实践,使人类宪法文明的精华在中国发扬光大,造福于全人类的福祉事业。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度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第16个子课题“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中涉及法语的资料,由华东政法大学马贺博士提供,特此鸣谢。)
注释
何勤华等:《法律名词的起源》(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比如,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美国传教士米怜(W.Milne,1785年~1822年)在其所留下来的中文遗著《大英国人事略说》一书中,就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中国进行了宣传。1833年7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1803年~1851年)在广州创办了中国近代内地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进一步较为详细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的法治、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陪审等宪法观念(参见爱汉者等编、黄时鑑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版)。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
《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
《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详细内容可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在这些宪法性文件中,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发扬民主”、“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保障抗日人民的各项基本人权”、“除司法系统和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等的观念和主张。
皇帝卡拉卡拉的本名,就是安敦尼努(Antoniniana)。
何勤华:“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法学》,2004年第12期。
参见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第8条(“中华民国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第7条(“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2012年,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各国宪法》(全四卷)一书,里面翻译收录了联合国所属193个国家的宪法。从各个国家的宪法规定来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李光灿、李剑飞:“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陈传纲:“反人民的旧法律和人民革命政权绝不相容”,《人民日报》,1952年8月26日;叶澜:“清算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7日。
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全会公报于12月24日发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99页。
Gérard Conac, Marc Debene, Gérard Teboul,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 :histoire, analyse et commentaires, p.150.
李光灿、李剑飞:“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三版。
“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人民日报》,1952年8月17日社论;陈传纲:“反人民的旧法律和人民革命政权绝不相容”,《人民日报》,1952年8月26日第三版;曹杰:“旧法观点危害国家经济建设”,《人民日报》,1952年9月13日第三版;叶澜:“清算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7日第三版;等等。
丘日庆:“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的美国‘法治’”,《法学》,1957年第4期,第22页以下;叶孝信:“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批判”,《法学》,1958年第4期第35页以下;孙国华、郭宇昭、许崇德:“肯尼迪叫卖的‘法治’”,《政法研究》,1962年第2期第1页以下;等等。
刘焕文:“在‘百家争鸣’中谈旧法思想”,《华东政法学报》,1956年第2期。实际上,作者刘焕文本人也是一名在民国时就已经成名的旧法人员,他于1956年写作此文的目的,实际上是想阐述对旧法观点不能全盘否定,应该吸收其中对建设新中国的法制有益的成分。但在当时对旧法观点基本上一边倒地持批判、否定态度的氛围下,即使有一些试图阐述对旧法观点不能全部否定的文章,一般在开始时也要对旧法观点进行一番批判和谴责,然后再用“但是”等转折词来小心冀冀地诉说自己的观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一。
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倘使三个要素(部分)都有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也将是一个健全的机构”。这三个要素就是议事机构(负责立法)、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城邦国家的日常事务)和法庭(负责司法)。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14、220、228页。
宣统元年(1909年)制定颁布的《法院编制法》和宣统二年制定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均由沈家本主持,里面都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
另外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将我国司法队伍中的旧法人员,共有6000多人全部剔除出去(当时全国共有司法人员27000多人);另一个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学观、国家观改造我们的司法队伍。详见何勤华:“论新中国法和法学的起步”,《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
这一点,民国时期的宪法就已经关注到了,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民国政府并没有能够做到。如1946年宪法延续了1923年宪法第102条、1936年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第81条的规定,在第81条更明确地强调:“法官为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或禁治产之宣告,不得免职。非依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或减俸。”
温家宝:“各方面改革须逐步推进”,2012年9月1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关于审判独立和司法独立之关系的详细论证和阐述,参见何勤华:“法学观念本土化考”,《中外法学》,2013年第2期。
责 编/杨昀赟
The Chinese Communists' Constitutional Concept and Practice
He Qinhua
Abstract: The CPC is the most advanced political party in Chinese history. It not only excels at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has a broad mind and great ability in setting China on a course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Chinese leaders, including the CPC founders and those taking offic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have all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enac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constitution. This has resulted in the CPC's own constitutional concept and practice. This essay approaches the CPC's constitutional concept from its connotation and then describes and analyzes its changes.
Keywords: CPC, constitutional concepts,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constitutional studies, comparative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