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洲式“负反馈”
2013-12-29谭小章
10月30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批捕,11月4日,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胡舒立发表文章《新闻寻租不可恕》,批评陈永洲事件中暴露的权钱交易和新闻寻租现象,在引起媒体界关于“新闻自律”和“程序正义”的讨论时,人们也不禁反思:传媒业怎么了?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媒体都在关键时点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比如美国的“水门事件”或者中国的收容制度之废除。但是,如今这个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要付出青春、热血、无数汗水,甚至生命危险,但是,从个人收入来说,得到的回报却面临着巨大天花板。这个行业看起来有着极高的社会声誉,被称为“无冕之王”,被推上了神坛。但另一方面,社会资源却越来越多地在逃离它。很多年轻人,满怀理想而来。但是如今,相比那些更早转行的人,相比那些突破底线在行业里生活得非常滋润的人,理想竟然变成了负资产。
为什么媒体成了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这是个危险而有意义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在一个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风险与收益总是相对应的。要素不能充分流动,也许是当下媒体行业出现这种怪现状的根因。
三年前我在硅谷考察,跟斯坦福大学的几位教授,还有当地很多创新企业比如Google、Intel的人聊天。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极度重视风险投资的作用。比如以Google为代表的很多案例中,风险投资前期投入,上市之后市场给予极高估值,风投获利后退出,再去投资其他项目。
这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有趣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型。市场给予创新以高估值,于是,更多的社会资源愿意配置进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硅谷的创新水平。形成一个正反馈的生态系统。所以硅谷能够成为全球创新的风向标。如果用这个模型来观察如今中国的媒体,你会发现,媒体进入了一个与硅谷恰恰相反的负反馈循环:市场给予的估值越来越低,于是,进来的资本赚不到钱,甚至无法退出。更进一步,外面的资本不愿意进来,再进一步,里面的资本想逃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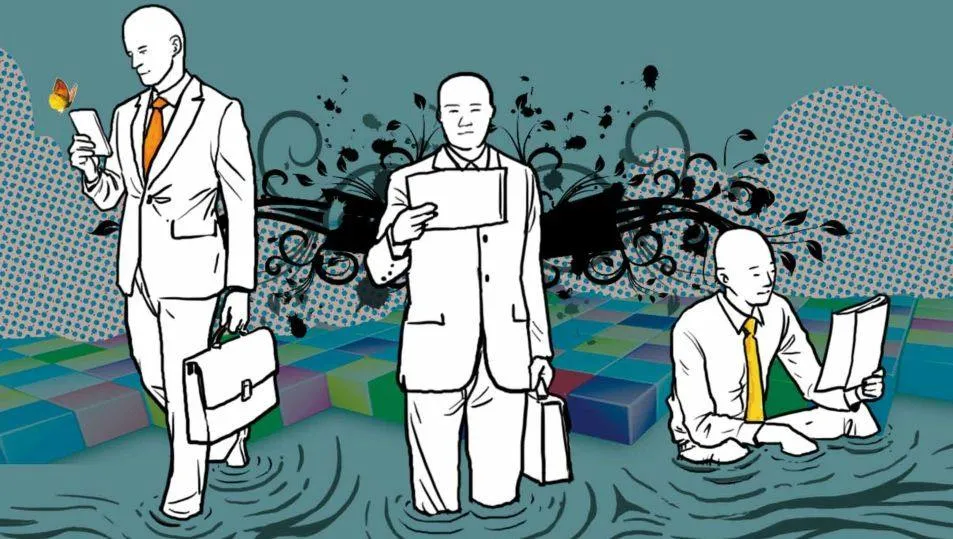
但单靠市场之手未必能让媒体行业繁荣昌盛。以纸媒为例,近年来一个突出的趋势是,优秀报道的商业变现能力越来越弱。中国好声音是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它能够为制作方带来极其丰厚的商业回报。但是,纸媒的优秀报道,能够带来的商业回报却越来越弱。因为纸媒直接面对读者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的传播是通过互联网渠道。所以,即使能够产生优秀报道,但纸媒本身的变现能力越来越弱。而这种变现能力的缺失,会进一步抑制优秀报道产生的数量。这是另一个负反馈。
矛盾由此凸显——社会是需要严肃新闻报道的,然而严肃新闻报道创造的商业价值却越来越小。于是社会资源不再配置到这个领域,后果是,真正优秀的报道越来越少。上市的传媒公司,没有说继续在内容上做大投入的,纷纷都去收购网游和手游了,因为这才是资本市场喜欢的故事。消费者也更愿意为游戏和娱乐付费,却对新闻一毛不拔。
如何在机制上做突破?胡舒立认为,应当承认公司制的效率要远高于所谓的事业制。能不能转型为公司,而且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关乎传统媒体的转型成败。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她还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不是所有的传统媒体都要从事业单位转型成公司。以报纸为例,可以是双向的:党的机关报就应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其运营机制可以考虑‘收支两条线’,也可以是非盈利机构机制,确保其完成宣传任务。党报不必有商业考量,不必考虑市场影响力和生存问题,可以搞准政府机制。而其它类型的报纸应当进入市场,以现代公司的治理模式进行管理,走市场化道路。”
但我认为仅此依然不够。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如何突破?如何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源配置进来?如何兼顾媒体的“公器”地位与商业需求?
一连串的问号,依然摆在媒体人的眼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