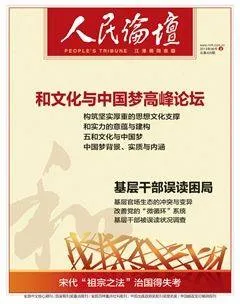未来中国文化眺望
2013-12-29庞井君

从社会价值论视角审视
绵延久远的古老中国进入十九世纪,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缓慢地演进着。1840年西方列强一阵枪炮,彻底打乱了她的阵脚,剧烈痛苦、前所未有的转型从此拉开帷幕:社会动荡、制度变革、政权更迭此起彼伏。其实,这些大潮涌动的底层,是中国的文化结构和命运发生着总体而深刻的变化。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还不能真真切切地看到未来中国文化的面目,却可以透过天边那一抹灿烂的朝霞,看到她那美丽的剪影和动人的神韵。
古雅清新
关于未来中国文化形态,一百多年无休止的争论可以归结到“古今中西”四个字上。从外在精神气质上看,我们不妨用“古雅清新”四个字来描绘她。
中国传统文化容量大、历史长、生命力强,拥有巨大的包容性、融合性和延续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一无二。几千年来,古代异族的侵入、近代西方的冲击、现代的自我变革、当代的信息革命都没有使之中断。有人说,传统就是过去在现在中,现在在未来中。未来中国文化的“古”正是源于传统文化这个特有的品性。
文化的价值主体是人。展现在未来文化中的“古”,是中华民族这个文化价值主体对传统文化选择、提纯和升华的结果。 因而,这个“古”不是复古、泥古和返古。“古”之上彰显着一个“雅”字,是古雅。雅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文化品位,一种理想追求。雅,意味着品格高洁,美丽大方,隽秀精致。未来,世人在中国文化身上看到的将是一种典雅,一种高雅,一种风雅,一种博雅。
古雅说的是继承、传统和自身;清新说的则是创造、未来和世界。清新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意气风发的想像力,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是一种凝聚着中国人生命体验、生命理想和生命价值的时代精神,是一种拥有未来、走向世界的精神气质。如果说传统文化和主体塑造给未来中国文化以“古”、以“雅”,那么时代精神和世界文化则给她以“清”、以“新”。
自由自然
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同一个人的人格,外在的精神气质是内在灵魂的展现,文化的内在灵魂是核心价值。未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自由自然。
自由价值和自然价值深深地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人类两种最根本的价值需要。自由,通俗的解释就是“由自”,她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和本质特性。马克思深刻指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本质。”自然是人类的母亲、生命的根基和永远的家园;是人类实现自我超越,探索真、善、美等崇高价值的精神源泉和不竭动力。人从自然中来,存在于自然之中,并复归于自然。学习、热爱、欣赏、理解、融入、沉浸于自然,是人最根本的价值需要。
自由是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灵魂。近代以来,以自由价值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然而在这个文化模式中,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目的性价值却被严重忽视了,认识、征服和改造自然,把自然对象化、资源化、工具化成了西方人对待自然的主导价值向度。这个价值体系蕴含的矛盾和冲突在现代工业社会日益尖锐化:社会冲突、人性异化、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接踵而至。 在这种形势下,反思和批判旧的价值体系,复归自然价值核心地位,已经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抑制了自由价值,却高扬了自然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价值,更不可能形成以自由价值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近代以来,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接受了西方自由价值理念,掀起了文化启蒙运动。启蒙的主旨与核心是自由,是飞女神(freedom)。飞女神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灵魂和母体。以“五四”为起点,自由作为核心价值渐趋融入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与这个古老民族内心深处的渴望与冲动逐渐对接。
与自由在中国的命运不同,中国人一直把自然视为核心价值。在中国文化中,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在价值论上,人和自然都融合在一起,没有西方那种明显的主客体划分;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人和自然的对立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人心中的自然是情感化、伦理化、艺术化、精神化的自然。中国人对自然的感情可用“亦师亦友亦爱亦一”八个字来概括,“一”是人和自然的融合统一,是天人合一。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放大了的人,人是浓缩了的自然,自然与人相通、相融,甚至同感同构。通过与自然和谐相处,沉浸自然而享受人生的自由与快乐,进入“天人境界”,实现“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高的精神追求。
综合起来看,在文化核心价值的演进上,西方走的是“自由—自然—自由自然”之路,中国走的是“自然—自由—自由自然”之路。如今,自由自然的价值综合已成了中西方文化发展共同的趋势。毋庸讳言,我们在两个方面都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就更需要增强文化自觉和价值自觉。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表达的是未来中国文化的空间结构和互动原则。自从《论语》提出这个思想后,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一个基本伦理原则。费孝通晚年把它明确提升为一个文化发展原则,倡导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社会价值论角度分析,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和人的集合形态,便有多少个价值主体;有多少个价值主体便有多少个具有“元“和“一”特性的价值体系。在复杂的价值互动中,每一个主体价值最大化的路径既不是泯灭自我,也不是扼杀他人,而是与他人“和而不同”。这样,每一个主体因“和”而与他人融洽共生,因“和”而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每一个主体因坚守了个性、维护了“不同”而确立了自我价值,赢得了与众不同的创造力、生命力和表现力。文化是价值的表达。文化的多元异质结构是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要保持文化的发展、繁荣、竞争和创造,就必须维护“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格局。这一点对全人类如此,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群体如此,对每一个个体仍然是如此。
“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可以预见,再过二三十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爆发200周年之际,中华民族将初步完成这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转型,初步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面对现实,虽然我们脚下的路还有诸多曲折、困厄和障碍,然而翘首遥望,我们分明看到了未来中国文化“古雅清新”的精神气质,“自由自然”的价值灵魂,“和而不同”的美丽轮廓。
责编/徐艳红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