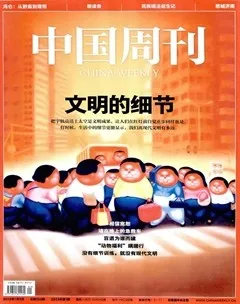最后的“斯文”
2013-12-29李佳蔚


“现代社会太讲究经济效益,太讲究效率,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祖先那会儿,不计成本精雕细刻的社会。”
东斯文里,已经“斯文不再”了。
巴洛克风格的雕花门楣,已经风化模糊,看不到原本的风采了;客堂前的落地长窗,残缺不全,前楼的门窗有的也已歪斜;居住在里面的大多数人,曾经享受过“优美而斯文”的里弄的温馨,可现在却盼着早点逃离贫民窟似的生活……
凭倚在苏州河畔快一百年的斯文里,是老上海最大的石库门住宅里弄,由东西斯文里构成,被视为上海传统生活方式的“活化石”。
西斯文里已于1997年被拆除,成为荒地一片。现在,只剩下东斯文里,仿佛暮年失去伴侣的人,孤独地蜷缩在巨大的水泥森林中,形单影只。
呼吁留住东斯文里的声音,越来越多。
有人说,“令上海人引以为傲的海派文化如果剥离了石库门里弄,恐怕要丧失掉大半的精彩”;也有研究者说,“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新盖建筑再多,也是苍白的”;即便是一心想离开的居民也感叹,“那么好的氛围一去不返了。”
留住东斯文里,到底留住的是什么?
“斯文”何来
“斯文里”这个名字,诞生方式毫无“斯文”之感。
它原本叫做忻康里。在二十世纪初时,它还是一条叫做“寺浜”的小河流(苏州河支流)两边的荒地,东北面是野草丛生的乱坟地。1914年,一个叫阿谷的英籍犹太商人买下了这块地,陆续建造起了二层砖木结构石库门,大约六年后竣工时,建成700余幢,命名为忻康里。
不久,阿谷家境衰落,将所有房产出让给通和央行,后者业主赌博,输给了斯文央行,才有了“斯文里”的名字。
斯文央行接手后,继续兴建,斯文里在1921年全部建成,并以大通路(今大田路)为界,西边前期成为“西斯文里”,东边后期的成为“东斯文里”。
《上海地方志》记载:“西斯文里318幢,东斯文里388幢,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旧式里弄。”
“当时的斯文里,确如其名,优美而斯文。”67岁的娄承浩指着一张斯文里的黑白照片说。他是上海老建筑研究专家,著有《老上海石库门》、《上海老房子》等书。
斯文里的房屋,采用了欧式联排结构,除了顶头两端之外,所有户型都是单开间。对开双门的乌木大门,上面有拉环一对,乌漆实心木做扇,条石门框,门楣处雕着的是巴洛克风格的山花。
处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斯文里,北面是苏州河,东面靠近大王庙,西侧有天然河道,南面则是交通主干道新闸路,在当时可是城市近郊环境优美的地区之一。
“斯文里,是上海历史的剪影。”娄承浩说。
1840年,上海开埠,农村的自然经济被打破,江浙农村的大量劳力涌入上海。他们的居住需求,成为一大商机。像犹太人阿谷一样的商人,先是建了木板房,遇到火灾后,便建了中西合璧的石库门。
起初,受民间对乱坟堆风水的忌讳,石库门居住的人并不多。第一次有较大规模人流涌入斯文里,与小刀会起义有关。
这场爆发于咸丰年间的武装起义,让上海周边的富人涌入城市躲避,其中一部分人就住进了斯文里。
“在租界里,他们求一份安宁。”娄承浩说当时的斯文里可以算作中产阶级聚居区。
这份“斯文”被战争彻底击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轰炸杨浦、虹口等区,避难居民纷纷逃向租界,斯文里一带人口骤增,成为全市闻名的入口高密度地区之一。集居在这里的,多是社会下层人,斯文里也成为旧上海的贫民窟。
涌入的难民让房屋租赁供不应求,原本独门独户的房子挤进了太多房客,能够反映这种居住状态的便是著名的“七十二家房客”。
1958年,为响应“大搞现代戏创作”的号召,杨华生、笑嘻嘻、张樵侬、沈一乐四位老滑稽艺术家,以解放前上海底层市民的艰苦生活为素材,写就了轰动一时的滑稽剧《七十二家房客》。从此,在全国观众眼里,“七十二家房客”就成了上海住房狭小的代名词。
此时的斯文里,已经不再优美而斯文。
斯文里房屋的设计,原本一进门是个狭小的天井,底层是客堂间,厨房紧接在客堂间之后,楼高只有两层,二楼对应客堂间的位置是一个相同面积的卧室,对厨房的则是亭子间,亭子间上有晒台,住在楼里的人家可以在这里晾晒衣物。
可就像《七十二家房客》里展现的一样,“八一三”事变后的斯文里,房屋简陋,房租低廉,最重要的是挤满了人,这种状态延续至今。
“观众看滑稽剧《七十二家房客》,很快乐,可笑声里,是居住于其中的人的无奈,甚至是悲凉。”娄承浩说。
“下只角”
命运的落差,有时只是生活里有没有一个抽水马桶的区别。
67岁的王阿姨,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嫁到斯文里来。她在虹口一个新式里弄里长大,那个地方,家里是有抽水马桶的,木框窗扇是精雕细作的,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做的,花盆里的月季似乎也开得比斯文里要好。
王阿姨的少女时代,生活的环境就像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里弄,是带有一些养尊处优的味道的。
这种养尊处优到了斯文里,戛然而止。就算到了今天,她洗澡只能跑到亲戚家里借浴室,解手只能先委屈在马桶里,第二天一早还得拎着它到弄堂口的便池排队倒掉。
其实,她和先生现在所住的这栋房子,是先生的祖父当年用金条盘下来的。那象征着旧日的好时光:整栋房子,只有他们一家人住,即便没有抽水马桶,可足够宽敞。
“八一三”事变后,斯文里人口暴增,家道衰落的他们只好把部分房间租出去,赚些小钱。因为某种原因,抗战结束后,租客都留了下来。解放后,房子产权收归国有,她先生一家尽管仍然被允许继续住下去,但租客们也反客为主,不再离开了。
王阿姨和先生住在弄堂东头二楼的一间中厢房,木质楼梯即使修过一次,可人踏上去,吱呀吱呀的叫声便会发出来。为了利用空间,夫妻俩在房间门口搭了一个简易厨房,引出电线在灶台上挂了一盏灯,还用塑料袋做了个灯罩,防止油烟把灯泡熏黑了。看上去,那个塑料袋像一张长了细密麻子的人脸。
顺着楼梯再往上走,便到了晒台。站在晒台上,东斯文里的全貌就展现在眼前:东斯文里一共13排石库门建筑,平行构成12条里弄,388幢房子里住着2600多户人家。由于空间紧张,很多房子的晒台都被改建成房间住人。这样衣服一来没地方晒,只好晒在弄堂里,加上居民堆放在门口的杂物,以及修建在房屋外围的自来水设施,本来就不宽的道路因此更加显得拥挤不堪。
王阿姨家的晒台依旧是用来晒衣服的,在东斯文里,这颇为少见。这多少让王阿姨有些自得:“这像我原来住的地方。”
她说话有些口吃,说到情绪激动处,口吃得越发厉害了,即便这样,她还是在水龙头处,边搓衣服边回忆“原来住的地方”:
“厨房后窗,老妈子经常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地扯闲篇,整个弄堂的事情,她们都知道;窗边的后门,大小姐会提着书包去读书,有时也是和相好的人约会;大门是不经常开的,一开,就有大事,要么贵客来了,要么就有红白喜事了。”
和王阿姨一家相比,楼下的老许一家,居住的则要局促很多。
老许今年70来岁了,解放后从杭州调来上海一家工厂做电工,没多久,又应国家号召支援新疆建设,在那里一呆就是十来二十年,直到1978年才回到上海。返沪当年,单位就给他在东斯文里分了房子,一个只有9.2平方米的灶间,他和老伴、女儿三个人住在里面,人均面积只有3平方米左右。
煤气未通时,像每一个弄堂里的男人一样,老许每天早晨要做的“大事”便是烧煤球炉子,然后到弄堂口的老虎灶,花一分钱打一壶开水。
烧煤球炉子,去老虎灶打水,再加上倒马桶,构成了上海里弄传统的生活方式。
“男人是绝对不能倒马桶的,晦气,只有女人去,如果赶不上倒,只能在家里发酵一天了。”说着,老许的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
最让老许一家痛苦的是,这个位于一楼的灶间房子特别阴冷潮湿,衣被发潮发霉且不说,一到冬天,户外的气温还在零上时,屋里的体感温度已经降到零下了,穿多少衣服都暖不起来。
“我们这里,是典型的‘下只角’。”老许感慨。在老上海人眼里,“下只角”是指住房简陋、环境杂乱的地区,住的都是底层老百姓,在上海日益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今天,“下只角”的时光仿佛凝固,成为上海传统生活方式的“活化石”。
这样的房子,老许一住就住了30多年。80年代后整个东斯文里都通了煤气,后来又有了空调。现在女儿已经嫁出去,屋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住着,空间比从前大了一些,但房间还是塞得满满当当,转个身都困难,更不消说其他日常活动了。
老许如果想要动动筋骨,逗逗鸟玩,只能在门外进行。
“想搬走,”傍晚时分,老许站在门外,一边给鸟喂食,一边说,“就像鸟也想住在一个大笼子里。”
和音
傍晚的东斯文里,是一天中最有生气的时候。
从新闸路的入口走进东斯文里,迎面而来是一片空地,散落着一些体育锻炼公共设施,小孩们在空地上追逐打闹,偶尔爬到体育设施上练练跑步,几个白发满头的老姐妹拉着板凳,坐在弄堂口聊聊闲话,棚子里坐着打麻将的中年男人,叫牌出牌声不断,四周塞满了围观的邻居。
老胡躺在椅子上,一手拿着茶壶,一手抚摸着像是倒扣着的铁锅一样的肚子,享受着悠闲时光。
老胡与共和国同龄,父母是当年的国民党军官。一家人原本住在南京西路华侨饭店的一套大房子里。他8岁那年,房子被没收,全家七口人分到东斯文里的三间厢房,面积只有33平方米。
“华侨饭店的名气足够大!”老胡说话粗声粗气。
华侨饭店是一幢仿意大利新古典主义的建筑,最顶部就是塔什千柱托的镏金球顶,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远远望去真是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在老上海的十大饭店里,华侨饭店名列前茅。
不过,老胡现在骄傲的是身后的家:他住在另一条弄的东头,家里有单独的厨房,单独的抽水马桶,天井被改成饭厅,容得下一大桌一起吃饭。这样一个家,在东斯文里,堪称豪华。
老胡高中一毕业就进了工厂做翻砂工,一做就做到退休。年轻时,他身体很壮,现在又发了福,体重超过200斤。前两年,老胡的肾结石经常犯,疼得满地打滚。救护车来了,医生护士根本抬不动他,主动赶来的邻居们喊着“1234”的号子,一起把他扛上去。
“穷人心连心,”老胡摸着自己的肚子,语气柔和了许多,“大家相处很融洽,哪家小孩子生病,自己出去上班,就是喊一声的事情,不分你我。”
在老胡看来,“喊”是弄堂生活独特的一种形式。
“夏天卖西瓜甜芦,秋天卖羊肉白果,修棕棚床的喊声,小孩玩飞香烟牌子的喊声,最有意思的是顾客在二楼,商贩在地面,上下对着喊,然后一只竹篮放下来,可以镇咳的糯米糖、梨膏糖续上去……”
“这些喊声,成为里弄生活的一种和音,”老胡指着巷口玩耍的小孩子说,“普通百姓,不用钱,也能得到快乐。”
让老胡怀念的还有一种安全感。在他的描述里,一个人果在弄堂口,无形之中会充当整个弄堂资产的看护者,可“那么好的氛围一去不返了”。
像东斯文里的大多数邻居一样,老胡盼着搬迁。1997年,西斯文里全部被拆除,东斯文里的居民就伸长着脖子,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够轮到自己。
实际上,和老胡一起长大的弄堂伙伴,如今留在近旁的没有几个了。“在外面买得起房子的,都搬走了。”老胡说。
东斯文里动迁的消息传开,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
王阿姨兴奋得不行:“终于可以在自己家里洗澡了!”但她也觉得有些遗憾,“市区文化氛围好,这里住久了也有感情了,到了郊区,肯定就不一样了。”
“可能要搬到农村去了,但能住大房子总归是好事。”老胡的心情复杂。他最怕的是,到时候几十年的老邻居都散了,万一自己的肾结石或者什么病痛再犯了,新邻居是不是还会“1234”数着号把他扛上担架?
谈起这些,老胡的表情看上去总是有些落寞。“可那是大房子啊!”过了一会,他又这么安慰自己。
崭新的苍白
28岁的Ryo的脸上,同样写满落寞。不过,这落寞与老胡不同,Ryo的落寞来源于一排排石库门的消失。
Ryo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男生,童年时有过短暂的里弄生活经历。从前,每天上学放学,他都会经过新闸路,东斯文里就近在眼前。
大学毕业后,Ryo做了一名设计师。他发现,上海正在发生着越来越激烈的变迁,一排又一排的石库门里弄被推倒,就地建起了一根根陌生的水泥巨塔。
“上海的陌生速度,让我们这些土著都有些找不着北。”在他看来,在上海市辖区里,这样的石库门里弄曾经星罗棋布,他们构成了上海人大半的生活空间,几代人在里面出生、长大、成家、立业,叙写着他们自己以及上海的历史。
“毫不夸张地说,令上海人引以为傲的海派文化如果剥离了石库门里弄,恐怕要丧失掉大半的精彩。”他说。
可现实是上海的石库门里弄越来越少。
今年6月的一天,Ryo像平常一样经过东斯文里,发现门口挂上了旧城改造的红色条幅。他心里一惊,回去一查资料,才知道东斯文里是目前上海现存的单体面积最大的石库门里弄。
他赶紧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呼吁留下东斯文里的消息。这条微博当天就被转发了100多次,对于只有几十个粉丝的他来说,这堪称数量众多。一家上海知名媒体也赶来采访他。
Ryo发现,民间呼吁保护东斯文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共识是:东斯文里的消亡,是本土不可再生文化资源的流失。
“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新盖建筑再多,也是苍白的。”娄承浩说。
娄承浩曾在新昌路石库门里弄生活过,他说自己是“在老房子里出生、又在老房子里长大”的人。
娄承浩对于上海石库门的命运做过调查研究。在他看来,石库门应该被“分级分类,区别对待”,而不是一味地推倒摧毁。
他去过黄陂路新天地。“新天地是将原住石库门居民整体动迁后,保留石库门里弄外型和建筑符号的商业性开发。在大批拆除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年代,能有这样的创意确属不容易。”
但在去过几次新天地后,娄承浩感觉陌生:“对我这个老上海来说没有亲切感,仿佛在松江影视拍摄基地,做假之嫌油然而生。最大的缺陷是,石库门里弄建筑群的环境消失了。”
娄承浩欣赏的是田子坊“二井巷”那样的处置方式:里弄格局不变,建筑单体不变,人文环境不变,弄堂里仍然住着许多原来居民,可以晒衣服孵太阳。游客则可以坐在咖啡馆门口喝咖啡,感受上海人的市井生活氛围。
不过,娄承浩做调查研究时,也曾被人质问:“你们居住得好,不拆,让我们一辈子受苦啊!”
“这需要政府拿钱,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在现在,这不是难事。”娄承浩说。
与91岁的东斯文里相比,78岁的步高里则要幸运许多。这处位于陕西南路287弄的中法合璧旧式里弄,已经重获新生。
从2007年6月开始,卢湾区房地局工程科利用德国先进材料,花了7个月时间,给步高里进行洗墙,既保留了原有历史材料和风貌,又对于破损红砖墙面按原状修复,使“步高红墙”的风景重现。
同时,卢湾区房地局工程科还给居民家里装上了专利马桶,方便了居民生活。
步高里外墙修缮和卫生间改造的花费,一共是700万元。其中,每户居民象征性出资100元,市文管会奖励资助了100万元,其他都由区政府承担。2008年,卢湾区还让2000只专利马桶进入石库门。
2012年11月10日,静安区负责人来到东斯文里。据说,围观的人群将他包围,“一瞬间抗议、诉求、民怨响彻大田路。”
2012年2月底,一位上海摄影师来拍东斯文里。在他看来,这里的一切似乎未变:空间依旧逼仄,电线依旧错落,万国旗依旧高高飘扬,穿着睡衣提着马桶的人依旧穿街走巷……
可东斯文里还是原先那个东斯文里吗?他问自己。
在《东斯文里的疼痛》一文中,他给出了答案:“非也,居民的心态变了,巷子里到处弥漫着一股等待拆迁的躁动,这是一种类似传染病病毒一样的因子,他们只关心属于自己的利益得失,又有谁能读懂东斯文里的疼痛呢?”
“这不是居民的错,”娄承浩承认现代科技能够造出老房子的任何构配件,“理智地说,新房子总的来说比老房子好,但是老房子依附的历史印记、生活氛围和精致的手工木雕、砖雕、石雕,是新房子所缺乏的。”
说完,他把《上海老房子》里关于斯文里的内容轻轻合上,停了几秒钟,说,“现代社会太讲究经济效益,太讲究效率,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祖先那会儿,不计成本精雕细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