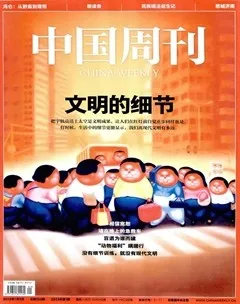来信
2013-12-29
封面评论
我在北京工作10多年了,有房有车有孩子,可是没户口。其实,就是有户口,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北京人。毕竟出生、成长的地方是在我的家乡。从情感上,我很乐意在北京当异乡人,我永远爱我家乡;但从权利上,我承担了北京市民承担的一切义务,我觉得应该获得同样的市民权利。我的同事很多情况与我一样,我们都不愿意当权利上的异乡人。
——刘佩雨/北京职员
猜不透的火车
我的表妹通过了东北财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笔考,最后一关是复试。参加复试要赶到大连,提前一天,她从老家太原出发。
从太原到石家庄很顺利,她还看了看复试的资料,车到了石家庄时,麻烦来了,前往大连的票已经卖完了。表妹想买站台票上车,售票员说送站的票要有车票才能买。
表妹一下就蒙了,明天就是复试报到,顺利赶上晚上8点半开车的K370是13号下午1点到大连,去不了这个研究生就白考了。当时已经是下午7点多,距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
表妹R052YNEb4tdor8prdlLM/w==开始找人帮忙,她站在进站口,向看上去面善的拿着车票的旅客“求救”,一个、两个、三个……但几乎没人愿意听她陈述。这年头,谁都知道火车站骗子多,就算一个小姑娘也都人人提防。
将近8点,表妹还是没借到车票,眼泪被逼了出来。
终于,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耐心听完了表妹“火烧眉毛”的急事儿,帮她买了票。表妹说,这是他的救命恩人。
8点半,深刻感受到“天无绝人之路”的表妹上了车,她惊讶地发现那车上根本没几个人,硬座车厢里,大家都睡在座位上。
表妹想不明白为什么空车不卖票,有人告诉她,如果是过路车,即使中间的车站卖了钱也不是车站拿,所以一些车站干脆就不卖桑。
表妹很单纯,她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她只是觉得有些事情不该这么样。
——牛晓娟/太原 学生
记者手记
一个比利时母亲的担心
“它甚至比我的祖国还要安全。”甜品店里香气萦绕,卡特加搂着3岁的女儿贺婷,语气坚定地说。
“它”,指的是南京。1996年,卡特加从祖国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毕业,然后来到南京大学,学习了一年的中文。她在鲁汶大学学的就是汉语,在中国待了十五六年,这让她的中文说得很溜儿。
卡特加在南京认识了丈夫贺杰克,贺杰克是德国人。两个人育有一儿一女。1997年,两人开始在南京经营甜品店。
这对夫妇是我在南京采访“普方协会”时认识的,2001年,德国人普方一家4口被四个中国年轻人杀害,“普方协会”后来致力于为贫困的少年提供助学费用,以避免这样的悲剧。在得知普方一家遇害的消息后,像其他在南京的外国人一样,卡特加和丈夫陷入震惊、愤怒和巨大的悲伤之中。
2002年4月4日,卡特加和贺杰克的甜品店开业五周年。他们计划开一个party来庆祝,两个人商量过后,确定party的主题为“更长久地纪念普方”。
后来,这个party规模不断扩大,直至成为普方协会的慈善晚宴。
实际上,贺杰克和卡特加没有加入普方协会,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参与其中。
2012年的晚宴,贺杰克和卡特加带上了三岁的小女儿和刚上一年级的儿子。贺杰克说,在德国的教育里,宽恕、慈善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观,一定会在学校的教育里有所体现,同时,家庭教育也同样重要,家长要以身作则。
卡特加略微思索了一下,字斟句酌,说,“更多的是如何看待人的问题。”
他的小儿子正在学钢琴。钢琴老师打电话给她表示了担忧:“你儿子学得太少了。”“少”指的是练习时间和关于钢琴的知识。卡特加意识到了其中的严重性,她打电话给老师,郑重地说:“钢琴是他喜欢的,能够让他快乐,如果钢琴让他痛苦,那还学什么?”
卡特加知道儿子的中国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学了多少“兴趣课程”。她扳着指头数:“画画、书法、二胡、小提琴……”一只手数完,她嘴巴张大,“太多了!”
“学校里要的是成绩,没有自由,我们要的是孩子顺着天性成长,要培养他的责任感,要他学会思考,”卡特加说。
上一年级的儿子,并不能完全理解普方一家人和慈善晚宴上的事情,卡特加只是告诉儿子:要善良,要帮助穷人。
现在,卡特加领着孩子出去,碰到乞丐,儿子总会向她要零钱。可有时儿子的疑问,让她很难解释:有的小朋友的妈妈,碰到乞讨的人,就领着孩子快速走开了,还教育孩子,“他们是骗子,离他们远点。”
卡特加并不回避对子女在中国学校接受教育的某种担心。“我们不会一直在中国生活,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她望着在玩具毯上翻滚着的小女儿说,“家长和学校教给孩子的基本价值观,会陪伴孩子的一生。最怕的是两个地方互相矛盾。”
——李佳蔚/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