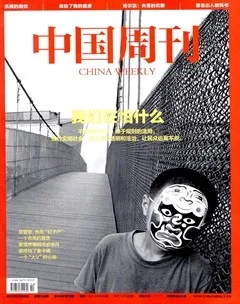美国虐童介入之路
2013-12-29焦东雨
美国虐童介入之路
合理地将孩子从不称职的父母手里“夺走”,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一百多年前,美国开始审慎地在“保护家庭”和“保护孩子”之间寻找最优之道。
1874年1月,纽约“地狱厨房”街区一栋廉价公寓楼里,十岁的玛丽·爱伦备受煎熬。
她父母双亡,称一位C太太为妈妈。即便是冬天,她也没有鞋袜可穿。除晚上到院子里上厕所,她被禁止外出,也不得与其他孩子玩耍。而晚上的床,仅是铺在窗户下的一块地毯。妈妈习惯于几乎每天都要揍她一顿,打得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一位公寓看门女子向教会工作人员艾塔·韦勒透露了玛丽的遭遇。致力于儿童救助的韦勒决心救玛丽于水火。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决心”改变了那些受到虐待的孩子们的命运。
英国殖民时代和美国独立之后,美国法律继承了英国普通法,通常“没有专门条款保护儿童这个群体,一些殖民地法律授权法院,可将遭受虐待、忽视、贫困的儿童转移给别人,做学徒或者是合约童仆。这些孩子被要求顺从主人,主人则有义务满足他们的吃穿住等基本需求。”纽约阻止虐童协会现任档案和行政主管约瑟夫·格里森说。
那个年代“法律很少适用于儿童保护,更没有专门针对儿童这个群体,制定专门的法律,提供特别的保护。”1820年至1870年间,美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爆发了内战,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和外国移民流入。其间,纽约城人口增长了七倍,人口超过百万,其中有一半出生于海外。针对儿童的剥削和虐待,屡见不鲜。除极个别情况外,人们纵容了绝大多数虐童事件。
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教授约翰·迈尔斯认为,1875年之前,出于保护目的的干预介入确实存在,但仅为零星个案。
1866年,亨利·贝高在纽约创立美国阻止虐待动物协会。出于保护动物,第一部反对残暴虐待行为的法律得以出台。人们很快意识到,既然动物都有权不被虐待,人类特别是儿童也应该享受这个权利。
“纽约的孩子们正悲惨地急需支持……”1866年《纽约晚间电讯》如此写道。1867年,纽约另一份报纸称“不止是低等动物在遭受残暴虐待……”但管教孩子仍被视为家庭事务,任何人无权干涉。
1874年,教会工作人员韦勒希望拯救可怜的玛丽,她咨询警察,警察拒绝调查;韦勒转向慈善机构,但后者没有介入家庭事务的权力。
在遭到多方拒绝后,韦勒找到了亨利·贝高。贝高既非玛丽的家人亲戚,也非目击者或警方,同样没有介入的合理身份。他的法律顾问艾尔布里奇·葛瑞使用与“人身保护权”相关的“释放令”(这一令状允许个人请求法院命令他人释放其虐待或非法拘禁的人),使得玛丽得以出庭作证。
“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妈妈打我时什么也不说。我不想回去跟妈妈一块住,因为她总是打我。”1874年4月9日,玛丽在法庭陈述。
后来,玛丽被安置到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结婚生子、组建了自己的家庭,1956年92岁时去世。玛丽·爱伦案成为儿童保护干预的经典案例,并促成了首家儿童保护组织的诞生。
救助玛丽的经历,让贝高和盖瑞意识到儿童保护机构缺位的现实,二人联合慈善家约翰·怀特,于1875年4月27日成立了世界上首家儿童保护机构——纽约阻止虐童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纽约市警方开始把虐童案件向协会通报,为此警局和协会之间还架设了电报专线。州和县检察长还授权协会代理法庭诉讼事宜。
协会发起的第一起诉讼,是一个男子在公共场合鞭笞自己的儿子,被协会官员撞了个正着。最后,该名男子被捕、定罪,被监禁30天。
成立八个月,协会收到数百起举报,起诉68起,救助了72个被虐待和忽视的孩子。
在协会的推动下,1876年,《阻止并惩罚侵害儿童行为法案》得以出台,规定父母和其他监护人要为孩子提供充分衣食和健康关照,且要保证孩子免于危险和伤害的义务。这部法律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授权法院可出于保护目的将孩子从父母处转移。法律同时也非常审慎地要求,只有认定孩子遭到严重伤害或面临死亡威胁时,才可将孩子强制转移。
当时社会多方意见都不能认同这一理念。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养育孩子是私人事务,国家不得干涉。因此,警察一般都不愿执行此类法律。更紧迫的是,没有太多机构愿意接手那些被转移或被遗弃的孩子。19世纪时,被转移的儿童多被送到孤儿院,后来出现了把儿童安置到寄养家庭的做法。两者孰优孰劣的辩论,从1850年代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慢慢地,人们认识到,孤儿院彻底剥夺了儿童的家庭生活,寄养家庭至少让儿童生活在一个家庭环境中,更接近一个正常的童年。最终,寄养家庭占了上风,孤儿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到19世纪末,协会在纽约累计调查13万起举报,救助儿童37万人,为8.4万儿童提供了临时安置。1925年,协会成立50周年,当年他们共调查了近四千起举报,涉及儿童1.1万人,其中有15%被强制转移。
转移安置这种激进的理念开始被更多人接受,并在全美和世界各地复制。1925年时,全美同类协会超过480家,世界各地则有53家。
民间机构看似遍地开花,但力量仍然有限,要求公共机构承担起保护儿童职责的呼声愈来愈强烈。
1909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召集首次白宫儿童会议。1912年,国会通过议案,成立儿童局,授权它“调查、报告任何涉及儿童福利和生命的事宜”。
1962年,亨利·肯普发表《受虐儿童综合征》,引起《新闻周刊》、《时代》等全国性媒体的关注。而此前,仅是地方报纸报道一些恶性致死事件。
那年,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修正案,首次将儿童保护纳入儿童福利范畴,并要求所有州在1975年7月1日前,建立起覆盖全州的保护服务体系。同年儿童局两次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建议立法要求医生向警方或儿童福利机构举报虐童案件。
1974年,国会通过里程碑式的《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成立国家儿童虐待和忽视中心,加强调查和举报。法律要求有义务举报虐童事件的人员逐渐扩大。虐童介入的加强,长期寄养儿童数量的激增,在1970年代末,引发了新一轮辩论。批评人士认为,近50万儿童安置在寄养家庭,远离父母亲情,更成问题。
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教授约翰·迈尔斯说,“转移儿童这种政策,自始至终、未来仍将是最有争议的话题。有时儿童保护服务处工作人员因为转移儿童而遭到批评,有时又因为把孩子留在危险的家里而遭到指责。”
1980年,国会通过《收养辅助和儿童福利法》,要求州政府力避转移儿童;必须转移的,要努力实现家庭的最终团聚。每个寄养儿童,都必须有一套终极方案,要么回归父母,要么彻底剥夺父母抚养权。
1997年,国会通过《收养和安全家庭法》,在“保全家庭”的基础上,把儿童安全置于最优先位置。当儿童被转移寄养后,法律要求必须制订严格的时间表,或者孩子回归父母,或者剥夺父母抚养权,使其成为合法收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