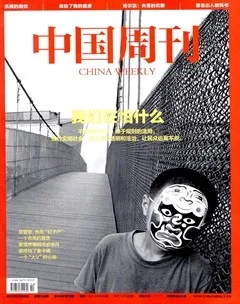激情燃烧的不安岁月
2013-12-29


“每一次都是在民营企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安全感和发展以后,又迅速被国有资本放大和淹没,随之而来一个大规模退潮现象,不安全感就会回到我们身边。”
1992年,中国明确建立市场经济后,民营企业家开始诞生。多年以后,中国成为经济总量第二大国,毫无疑问,民营企业家们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此过程中,针对民营企业家的种种不确定性,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在9月份大连达沃斯夏季论坛上,经济学家张维迎又一次带上了安全帽,黄色的,硬壳,扎眼。他说,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当下普遍没有安全感。“最大的不安全是来自我们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也曾说过一个广被传播的比喻:“财产安全就相当于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内衣,不能随便被扒掉,扒掉了以后大家不开心,而且丢大家的脸。”
回望中国市场经济这几年,在多种不确定因素下,企业家们经常被扒光。
1992年,成败在灰色地带
1992年,被公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幸运的开始。这一年,国家明确建立市场经济。国家体改委办法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两者是后来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
那一年,朱新礼创办了“汇源”;胡葆森创办了“建业”;冯仑创办了万通的前身“农高投”……
这一代商人们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精髓概括为“冒险”,也有人翻译成“投机”。这一年,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公司法律体系,这些商人们也不信法,他们宁可信胡雪岩式的官商处事方式。
市场经济里,企业是独立法人和独立利益集团,而在1992年之前的中国,政企不分成为顽疾,企业只是作为政府的一个附庸存在,是政府职能的延伸。1980年代中期,更是寻租丛生,狭缝里成长起来的商人,必须懂并且办好一件事才可能赚钱—寻租!灰色交易!所以,在确立市场经济初期,商人们仍惯性地依附于官员。
1992年,已经创业几年的牟其中已经业界大佬。1989年,他以货易货购进4架图—154飞机而闻名于中国。冯仑甚至甘当他的小弟,做了一阵子牟的办公室主任。冯仑曾对《中国周刊》记者坦言,牟其中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很江湖的大佬。而这也正是牟其中能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甚至更早之前就成功的条件。
那会儿,很懂江湖世故的牟其中,和政府做生意,搞资金运作,风光一时。最后,因为一封“十三条罪状的举报信”。2000年9月,牟其中被关进监狱,罪名是“信用证诈骗罪”。
因这个罪名而进监狱的还有90年代风光一时的摩托车大佬,原济南轻骑集团董事长张家岭,2009年被捕,罪因一直追究到90年代的资金问题。入狱前,张家岭很委屈,曾对身边人说,他们让我上规模,求我贷款,回过头来又说我贷款是诈骗。
所谓信用诈骗,是说民营企业家们欺骗银行伪造信用证据获得了贷款。当地政府要政绩的有力推动,他们个人的虚荣心膨胀,加上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导致这一代的诸多实业创业者们铤而走险。
直到现在,那时期发展起来的企业里,只有万科的董事长王石敢站出来高调宣布,“万科从不行贿”。不过,这话在其他企业家眼里,只当笑话。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对王石说的这句话就“从来不相信”。
中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一次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容易。他认为,市场经济不规范,“权力配置资源”的想象严重,导致民营企业被迫寻租,违法,最后东窗事发导致垮台。
灰色环境下,谁也晴朗不起来。直到现在,灰色地段依旧在延续甚至扩大,以至于在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都是行贿受贿的。
1998年,抓不住的孩子
1998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印发《关于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一大群企业家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改制的另一个代名词是“国退民进”。据国资委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锐减到15万户。减少了40%。这些企业要么直接倒闭,要么改变了产权关系,成为民营企业。
听起来,这对民营企业家是好事,也的确有一大帮商人通过改制购买股权把企业从集体所有制或者国家所有制状态下收入囊中。但是,不是所有企业都能顺利过渡。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之前国企或者国企控股的企业,一般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合作的。故事都是一个模子:原有的地方小企业亏损,来了一位有魄力有头脑的企业家,大刀阔斧,从此小企业变成大企业。这种英雄式的企业故事在当时比比皆是。譬如:当时的海尔和张瑞敏,当时的魏桥和张世平……
但是,上述两人是幸运的。
那个年代,在媒体的笔下被描述的最悲情的无疑是健力宝的李经纬。健力宝在李经纬手下,从一个生产米酒的小酒厂发展成销售额过50个亿的“东方魔水”。他本想借着这轮改制解决公司产权问题,愿以四五亿赎身健力宝,买下当地政府手里的全部股份。最后,未果,被当地政府和外来资本联合挤压,年过六旬,被赶出自己一手做大的企业。而且,被揭发“贪污”,判刑15年。
“赎身”失败的还有三九制药的赵新先。一个军人,带着十四个人,在一个山坡上,创立了三九制药,并一步步将其做大为一个产值将近100个亿的巨大药企。赵新先理所当然认为企业就是自己的了,用几乎逼迫的方式呐喊三九要完成产权明晰的任务。言下之意,企业要归我。2003年,5月,国资委撤销了赵新先三九公司总经理的职务,理由是:该退休了。那年,赵新先63岁。
冯仑曾把企业家比喻为政府的夜壶,让政府很愉快,随时用随时抛弃。
2003年,被调控下的不安
没有了体制限制,企业归在自己名下了,民营企业家们裤兜里的钱是不是就安全了?
答案是否定的。
2009年,《中国周刊》记者去日照采访日钢集团董事长杜双华。之前的一年,他以350亿的身家跃升至“胡润百富榜”的榜眼之位。在他治理下的日照钢铁,业已成为民营钢铁企业中不多的“千万吨级俱乐部”成员,是钢铁行业里最赚钱的企业之一。成绩面前,他理应开心,但是那段时间他很郁闷。他拒绝见记者,电话打过去,无人接听。因为,就在他的日钢如日中天时,山东省国资委要将其收购为山东钢铁集团下的一员。当时的山钢,体量庞大,却几乎没几个分厂盈利。
杜双华是撞在了枪口上。世界金融危机后,国家对资源性行业开始了新一轮整合,钢铁、煤炭行业的小企业、民营企业纷纷被收编国家正规军。民间野战军们只能乖乖送上自己亲手打下来的江山。
1980年代初,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山西煤炭领域。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近300家,其中,温州人最多。2008年,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开始,办矿企业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被关闭的绝大部分是民营煤矿。近千个温州煤老板收拾包裹回家。媒体用“覆灭”来形容这个商人群体。
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只要有机会见到政府人员,就为民营企业呼吁。那一年,在温州地区的银行储蓄每天都翻倍增长,上千亿的资本躺在银行里,达到了温州资本储蓄历史最高峰。对于一向活跃的温州资本而言,把钱放进银行,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财经作家吴晓波这样评价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这一轮“国进民退”现象,“2009年以来,国有资本利用金融危机,在重大产业中形成垄断性控制,为1978年以来最罕见的现象。”
在更早前,以“国进民退”为方向的调控覆灭了诸多实业企业家。江苏常州“铁人”戴国芳创办的铁本,撞在了枪口上。最后,钢铁项目被叫停。戴国芳本人也锒铛入狱。五年后戴国芳出狱,那块地依旧荒草丛生,只有生锈的铁块四处散落,风吹日晒。
吴晓波说,“每一次都是在民营企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安全感和发展以后,又迅速被国有资本放大和淹没,随之而来一个大规模退潮现象,不安全感就会回到我们身边。”
大V时代,该不该谈政治
老问题一直在发酵,新问题汹涌而来。
之前发家的商界大佬们,只要上微博的,几都成为网络大V。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物质生活的满足,他们开始关心和直接表达对社会乃至政治问题的看法。
随之,问题也来了。
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
柳传志在一次正和岛组织的聚会上给出的答案是:“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这个谨慎、有着丰富商界经验的“企业家教父”,也曾发表过“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的言论。
柳传志的言论迅速引发了舆论的浪潮,同是企业家的王瑛,当即决定退出和柳传志同在的正和岛组织,后来发出帖子,“……不相信中国的企业家跪着就可以活下去……”
商人是不是一定要承担国家命运的责任?商人完成社会责任的方式是什么?
这些问题,对当下中国的企业家而言,很纠结。一方面他们不关心和评说政治,会被大众指责;另一方面,跨出商界发言,无疑会给原本就不确定的命运,人为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经历过政治的动荡,政策的多变,如今年过半百的企业家们内心的这种不安感更强烈。
有媒体采访王巍,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金融博物馆馆长,给他定性“自卑”,内心有深深的不安感。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解释说,他不自卑,非要说自卑,每个他这样的企业家都自卑。他说,骨子里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民,没有经济家底,没有政治依靠,法律又不独立,没有保护,从一个知识青年跑北京打工一直发展成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内心从来没有过安全感,“你见识了什么是权力之后,才知道我们能干的太不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