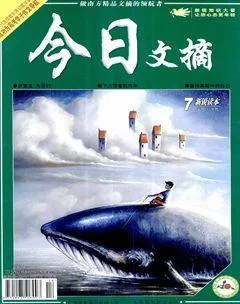65年未能寄达的家书
2013-12-29邓娟
仿佛恋人在怀,“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甜蜜蜜和软绵绵的感觉,顿时我便想入非非”,他请求“您别生气,且当是闺中戏谑吧。醒来余香犹在,窗外雨声淅沥,更添惆怅”——写信人用略带羞涩的语气谈到昨夜一场“春梦了无痕”。
这封浪漫多情的书信,来自1948年被解放军包围中的孤城长春。
信中柔情蜜意,现实却是窘迫不堪。信的落款之日,正是节节胜利的解放军攻占长春机场之时。解放军切断了城里国民党守军和外界的联系,最后在一架仓皇驾驶的飞机上截获大量信件。
这批家书先后被长春公安局和吉林省档案馆接管,在半个多世纪里成为沉睡的历史。
两年前一个偶然的场合,记者见到这封信的作者梁振奋,落笔时年方24的青年,前年已是87岁的老人,生命如同鬓发般染尽风霜。
那之前,记者从他的朋友处听到信的故事,趁他夫人离席,便半开玩笑地问:现在说起来不怕太太吃醋吗?
他微笑着摇头,但显然也不愿再就这个话题深入。
事实上,如果不是2008年吉林省解密的出版物里包含了这封信的原文,又恰好被他朋友看到,恐怕他后半生都不会主动言及。他的忘年之交告诉记者,他们相交数年,无话不谈,除了长春那段经历。
1948年长春解放,国民党守军被俘,无从得知梁振奋在那时遭遇了什么。从战俘营回到广州后,不愿连累女友的他选择了分手,此后饱受各种政治运动折磨,50多岁才成婚,毕生无子女,信中的初恋女友则嫁了他人,再无联系。
长春的记忆,成了这位前新一军侦察兵的禁区。惟有这封信,在那段他讳莫如深的岁月里,留存了惟一的甜美和明媚。
2008年是长春解放60周年,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首次披露了围城时没能寄出的国军信件,这些一手资料以个体记忆呈现了那段真实历史。
65年前的长春,凭借当时号称“坚冠全国”的工事,国民党10万留守部队与城外进攻的解放军对峙了5个月。
围困中悲观的情绪弥漫全城。国民党守军在信里频繁抱怨粮煤短缺、物价飞涨。
士兵季平写道:“市民有的吃树叶、树皮,有的吃豆渣,高粱米成为上等餐了,一斤四万余元。市内天天听到炮声,射程居然打到了省政府门口,长市变成了一个孤市。”
百姓饿殍成群,“军人虽粮食尚能维持,然而亦陷入最困苦状态”,士兵玉轩这样回复家中寄钱的要求:“恐怕你不会相信我的话,我哪里有钱寄到家里?一瓶黑人牙膏合法币千余万元,此地猪肉每斤一千五百万法币,我们月余未吃过。”
生存危机中发生了一些荒诞事。一名新七军士兵记录道:“在兵荒马乱的东北,只要有高粱米吃,结婚是特别容易,尤其学校的女学生,你可以任意选择,她们则无从选择,条件只是问你每月的收入和高粱米而已。”兵团部政训处一个快60岁的杨处长,娶了17岁的少女。
比物资匮乏更让人煎熬的是精神恐慌,季平提到“居民一天内总有千百人携老小(壮丁不准通过)离城经共区向关内走”。
而据当时的统计,3个月内国军逃亡人数超1.5万人,最多时每天300人。未逃走的,只能幻想“凑足川资回家”,烽火连三月,寄出的家书没有回音,更令人心惶惶。
那一年的孤城长春,春天来得很晚。如今隔着65年光阴,在字里行间,仍然能够感受围城中人们深重的恐惧和绝望。
即便如此,在这些沉重的记录里,也不乏如梁振奋那样甜蜜美好的情信。在窘境中,亲情爱情成为最牢固的寄托,那些不能停止的思念和期待,犹如绝境中的花朵,尤其令人心折。
1948年6月28日这一天,60军的尹辅臣在灯下给妻子芬妹写信:“相片我已收到,云峰长大了,好像很瘦,云霞好像很乖,我心真欢喜极了。”让他心疼的是,芬妹的样子苦恼而苍老,他郑重保存收到的黑发,寄语“您是我永远的发妻”。
在相近的日期,士兵培军向妻子张氏写道:“我们在这生途上,都是一朵美艳的花蕾,在极宝贵的时代,一刻也不肯把它轻易放过。但现在关山相阻,家乡千里只是望而兴叹。”
虽然“想娇妻而痛泣梦中”,这位丈夫仍宽慰爱人:“现今别离之苦正是奠定我们永久的甜蜜,我期待相聚的日子。”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信件都是单独一封,但其中一份,因为女方事先把之前往来的信件都存在男方这里,而男方预见到长春可能被攻破,又把它们打包寄出。从这些连续的文字中,可以拼出一段相对完整的故事。
这个士兵叫符祝宪,他的意中人叫刘维廉。“当你用纤指拆开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你一定会忙于看末尾的署名,陌生的名字使你费思索吗?我还没有过和你倾谈的机会,不过我却已是最仰慕你的人”,第一封信,男人单方面陷入爱情;
可女子似乎无动于衷,第二封信,心急的男人继续表白:“我胸头小鹿一刻没安静过,你是否在谅解我抑或嗔怒?”
第三封信,女子大概接受了他的示爱,因为他对她的称呼从“维廉小姐”变成了更亲密的“廉”;而第四封信里,他已经开始讨论婚礼细节了。
随着城内弹尽粮绝,城外攻势加剧,日愈绝望的国民党守军纷纷将照片、婚书、任职令等重要资料寄出。一个叫胡长庚的少尉就把300多篇日记夹在了信里。
这个年轻的少尉颇为有趣。兵临城下,21岁的他仍牵挂着4月4日是中华民国儿童节,这天的日记,他写道“今天过了我的第21个节”。
他带着童真记录琐事,“今天见到了久仰的东北歌手miss王,原来是这样一个女人,失望”“英国人说话时要轻快,要温柔,K、T、E、Z音均不发得太明显”。
他也记录国民党高官腐败:“灯红酒绿、舞影婆娑与难胞乞讨鲜明对照!”
4月15日这天,他写了一件小事:副连长因发军饷时被克扣1万元发脾气,“狂呼要当八路去,说着哭了起来”!
3年前偷偷从家里跑出来从军的胡长庚开始思考“我也希望八路来吗”?他想通了:哈,少将,我才不稀罕当呢,还是回家去吧,做妈妈的好孩子。
终于,他决定“物色我的收音机、脚踏车的买主,卖掉它们换成金子做路费”“只要能回家,就死了我也满足了”。
7月25日抽到一支问出行大吉的上上签,3天之后他去邮局寄信,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胡长庚是否能走上回家的路?符祝宪和刘维廉是否终成眷属?而培军和他的张氏,尹辅臣和他的妻儿,在那年深秋长春解放之后,有没有团聚?
尽管后来吉林省档案馆几经寻找这批信件的主人,但都未能如愿。这一个个尘封60多年的昨日故事,写下了开头,却没有人能补上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