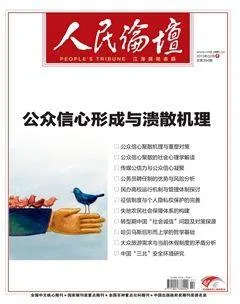全局视域下马克思的中国观略论
2013-12-29常县宾
【摘要】马克思的中国观是全面而客观的,他在认识到中国停滞、封闭和落后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人文明、高尚且富有道德心;在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近古时期日益增多的贸易往来。此外,马克思的中国观还反映了他正在形成的东方社会思想和业已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意识。
【关键词】全局 马克思 中国 中国观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中国观就是认为中国停滞、封闭、落后。笔者认为,从全局的视域来看,这些仅是马克思中国观的一方面,实际上马克思在认为中国停滞封闭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文明与高尚。此外,马克思在认识中国小农经济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近古时期大量的中外贸易往来。
封闭停止与文明高尚
在马克思的眼中,中国的确是停滞和封闭的,但也认为中国人文明、高尚且具有道德心。
马克思对中国的停滞有过诸多的表述。他说:“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①他在论述太平天国运动时说:“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②
马克思也多次抨击中国的封闭,他说,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处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③此外,马克思还沉痛地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④马克思也论述了中国封闭的原因,他说:“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⑤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观察力是敏锐而全面的,在指出中国落后的同时,他也论述了中国人的文明与高尚。马克思认为中国文明对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高度赞扬了中国火药等发明对世界的影响:“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⑥马克思也多次提及中国皇帝重视民间疾苦,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他说,1853年1月5日咸丰皇帝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⑦马克思在论述鸦片贸易时说,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会双倍于此。可是,天朝的野蛮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1853年,当今的咸丰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作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把吸食鸦片当作邪教一样来取缔。⑧
再如马克思在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时,一再指出中国是正义的一方,而英国方面则是蛮横无理的,他说:“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马克思还借用《每日新闻》社论来抨击英国政府“无所顾忌地任意把人命送上虚伪礼节和错误政策的祭坛,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丑恶和卑鄙的”。⑨马克思充分赞扬了中国人学习外来事物的能力,他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⑩最后,马克思也高度赞扬了中国人的勇敢和团结,在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说:“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经过极其冷静的预谋”,中国人采取的方式是全民参与。
自然经济与近古时期中外贸易往来发展
马克思对中国的论述中相当部分与中国经济有关,他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运转做了深刻的研究。与此同时,他对近古时期中外贸易往来也做了一定的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产物,他借用英国官员米切尔的报告来描述这种生产状态:“收获完毕以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主就收购这种土布来供应城镇居民及河上的船民”,中国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他生产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
马克思进而对中国这种自然经济的影响做了论述,首先,这种生产结构的简单性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不变的秘密,“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其次,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然经济对外来的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抵御力。他说:“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事实也确实如此,1856年,马克思根据英国驻上海领事罗伯逊的报告,认为最近十年来中国茶叶的出口增加了大约63%,丝的出口增加了216%,而工业品的进口却减少了66%。估计从世界各地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比十年前多558万英镑。1857年,马克思写道:“从1854年到1857年,向中国出口的英国工业品平均不超过125万英镑,而这是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的年份里常常达到的数字。”
马克思认为,中国长期的自然经济虽然自给自足,但中外仍存在贸易往来,1600~1830年间的近古时期尤其如此。他论述说,由于西方需要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不得不用白银来偿付,“从17世纪初起,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对欧洲和美洲的金银市场一直起着重要的影响。白银是这些东方国家的唯一交换手段,也是西属美洲大量输往欧洲的财宝。由于同东方进行贸易,就有一部分白银从欧洲大陆外流”。他认为,从17世纪起到1830年左右,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马克思进而分析说,到17世纪初,荷兰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扩大了同中国的贸易,白银的需要量大为增加,但真正大量增加则是从18世纪英国茶叶的消费迅速增长以后,因为英国为购买中国茶叶汇去的几乎全是白银。到18世纪后期,白银从欧洲向中国的外流已经达到很大的规模,乃至吸收掉很大一部分从美洲输入的白银。这个时候,白银也已经开始从美洲直接输往中国,虽然总的说来只限于墨西哥阿卡浦尔科的商船队运到菲律宾群岛去的那个数量。19世纪头30年,欧洲更加感受到亚洲、主要是中国这种吸收白银的情况,由于西班牙的殖民地爆发革命,来自美洲的白银从1800年的4000多万美元降到了1829年的不到2000万美元。另一方面,从1796年到1825年美国运往东亚的白银增加了三倍,而在1809年以后,不仅墨西哥,还有巴西、智利和秘鲁也开始直接向中国输出白银。从1811年到1822年,印度和中国从欧洲输入的白银超过这两个国家输出的黄金3000多万英镑。以中英贸易而言,对华的输出在1697年不到英国出口总额的1/52,而1822年已经达到约1/14,1830年达到1/9左右。
此外,马克思对鸦片战争前中俄陆路贸易也做了一定的研究。他说,除正常的贸易往来外,俄国还在北京派驻有特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不会有什么竞争者。这种贸易是依照178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订立的一项条约进行的,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算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约100英里的地方。这种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有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在货物定价都不高的情况下,贸易额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
综上所述,可见马克思对中国的认知是全面、真实而客观的,他对中国的论述绝大部分集中在1853~1859年间,马克思对中国的这种认知对他1859年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有重要的启迪,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体系。
马克思对中国的认知是辩证的,全面、真实而客观,但是,对于马克思的这些中国观,中外有些学者却有着不同的诠释。萨义德认为,马克思的中国观充满矛盾,表面上是历史辩证法对进步二重性的解释,但从实际上看却是马克思意识里的欧洲中心论意识与对中国的人文主义同情之间自我冲突的结果。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思政部)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第114~117页,第2~4页,第64页,第6~7页,第3页,第66页,第16~21页,第53页,第57~58页,第106页,第74页,第13页,第38页,第10~12页,第42~4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65页。
责编/边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