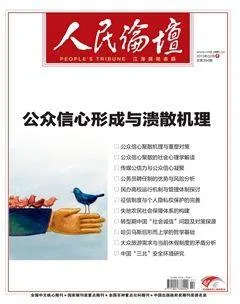信仰型杀手的人格研究
2013-12-29刘裕利

【摘要】自古以来,宗教信仰在信仰范畴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很多人的心灵家园。然而,现实中有些人却以宗教之名行屠杀之事,是为信仰型杀手,这一群体的人格极具争议性。文章以电影《七宗罪》中的罪犯John为契入点,分析其变态人格类型以及形成变态人格的因素,并结合时下我国相关犯罪现象,提出预防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宗教信仰心理 信仰型杀手 变态人格 心理抚养
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日渐富裕,可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日益空乏。在这个充满欲望但人性却无比荒芜的世界里人们不禁会追问:我们该如何面对上帝死了的人生?物欲横行的时代里何处才是人性的归程?答案是我们应当拥有精神信仰,用信仰充实我们的内心世界。
可是,有些人对宗教有着近乎狂热的迷恋,以致认为自身是上帝或神的附体,借上帝或神的名义,恣意掠杀无辜生命。在此,笔者将他们称为信仰型杀手。文章将通过对电影《七宗罪》的人物John的个案分析,探讨信仰型杀手的人格形成及特征,并结合当下我国出现的相关犯罪现象,寻求这类人格的治疗和预防措施。
宗教信仰的常态心理
宗教与宗教信仰。对于宗教的概念,学者各执一词。比较通行的观点是,宗教是指一些神秘的事物,它或者是人们深深体会到的,或是冲击人们意志的力量,使得人们不得不依附在一个团体中,宗教的核心是信仰。例如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认为,人类以其普遍因果联系的工具技术打破了狭隘的野兽实在感。他将人的这种超越直接经验实在的能力归之为“符号”,它意向指称的对象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可能的,甚至即使不可能但却是理想的。对于虔诚的宗教徒而言,这些理想或预言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比日常生存中的食宿或劳务更为真实。这种对非(直接经验对象)实在的实在感,就是信仰。①可见,在卡西尔的观念里,宗教信仰是对自然人欲以及世俗的超越。
宗教信仰的心理根源。宗教信仰的心理根源在哪?大多数古代思想家认为是“恐惧创造了诸神”,近代以来,各学者的观点渐渐有了分歧。
斯宾诺莎认为,“因为人们常常陷入极大的困境,以致无法给自己拟定任何计划,并因为他们无限地寄希望于命运女神给他们带来的捉摸不定的机运,因而大部分人常常处在希望和恐惧之间的可怜的摇摆之中,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特别愿意信仰任何东西……”②
费尔巴哈则提出,“除了依赖感和依赖意识以外,我们就不能发现其他更适当、更广泛的宗教心理根源了。”③可见,斯宾诺莎是对古代关于宗教信仰根源思想的继承,而费尔巴哈则摒弃了古代思想,主张依赖感才是滋生宗教信仰的根源。
正常宗教信仰的心理特征。宗教虽基于人类的无知、畏惧而生,不属科学,但它却以净化人的主体态度为主旨,是人类内心的美好依托。一般来说,人类个体心理本身并不产生宗教,但在生活条件的影响下,可以创造出有利于个体从周围环境中接受宗教信仰的某些心理状态(如心理压抑、悲痛、孤独感、不满意自己等等)。
首先,宗教信仰的心理不具有遗传性。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现象,必须来源于人与社会的接触。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父母信教,小孩传承信教衣钵的事例,这是言传身教的结果,非遗传基因的问题。
其次,个人生活中的危机可能促使人们皈依宗教。比如,离婚使某一女性绝望至极,甚至万念俱灰,于是她选择了遁入空门,在信仰中,她体验到了仁爱、宽容等幸福感。
再次,需要能促使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追求。需要不仅使我们得到某种经验,而且一旦需要得到满足,导致满足的行为将会被人铭刻在心或得以强化。周而复始,信仰便得以形成。例如,某农夫为了自己的庄稼而祷告求雨,要是雨果真来了,他就更有可能为了雨水和他所需要的其他什么而进行祈祷。
最后,情绪可以促成宗教信仰。情绪本身是宗教的一个重要部分,并有助于个人信仰的整体化。例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偶然得知,在某一宗教团体活动中,大家可以欢畅地体验到上述种种积极的情绪,由于人们需要这些积极的情绪体验,为此,选择了信仰。
信仰型杀手背后的变态人格
John变态杀人的事件回顾。John是一个对天主教有着“无暇”信仰的人,但他却做出了无比残忍的杀人举动。他以上帝传道士的名义,根据但丁《神曲》中的七宗罪,在人间找寻出犯相应罪行的代表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惩罚:
强迫饕餮者进食大量的意大利面,最后使其肠爆裂而死;将贪婪者的血放干,并割下他身上的一磅肉;让淫欲者死在性高潮中;精心策划让懒惰者饱受凌虐一整年;让傲慢者死于骄傲中;妒忌者(John本人),因为垂涎警察Mills的妻子Tracy,但被拒绝,于是就杀了Tracy及其肚子里的孩子;暴怒者,警察Mills,当得知自己的老婆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被John所杀时,他的愤怒已经无法控制,因为“愤怒”,他选择开枪射杀了John,致使John这个变态的信仰型杀手,最终也以身殉道。
信仰型杀手的心理异化—变态人格。电影《七宗罪》的角色John,一个对天主教有着无暇信仰的人,却作出无比残忍的杀人举动。他以上帝传道士的名义,根据但丁《神曲》中的七宗罪,在人间找到犯有相应罪行的代表并对他们进行惩罚。
John沦为杀手,是因为对宗教教义的痴迷抑或是其自身的原因?对此问题,一度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且争议不已。
有人认为,这是John“伟大”的信仰使然,借此抨击宗教的鄙陋及腐朽,认为宗教信仰应当摒弃;也有人认为,John杀人纯粹是为了排遣内心的孤寂,试图得到社会的关注,与信仰无关;笔者认为,宗教信仰只是John借以杀人的幌子,其深层次的原因是John的变态人格。
关于变态人格之界定。变态人格,也称人格障碍,指在社会和人际环境中广泛存在的,个体对环境和自身的感知、联系以及看法的持久的模式,它顽固、不适应环境,并导致功能损伤或主观上的痛苦。根据DSM-IV-TR的诊断标准,结合John的个人情况,笔者分析,John应属于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分裂型人格障碍是一种以观念、外貌和行为奇特以及人际关系有明显缺陷,且情感冷淡为主要特点的人格障碍。具体特征见表1。
根据《七宗罪》的剧情描述可断定,John不是精神病患者。一是John的整个犯案过程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尤其是对懒惰者实施的长达一年的折磨,可见他不但意识清晰,具有一定的医学专业素养,且非常有耐心。二是反侦查能力很强,比如,为了不留指纹把手指表皮割掉,假扮记者以了解警方的侦查进展等。三是熟知法律,在五桩命案暴露后,他选择自首,同时聘请律师以保护自己的权益等。以上种种表明,他不但意识清晰,还是一个高智商的犯罪分子,不是精神病人。随着剧情发展,我们可以看到:
表1 分裂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DSM-IV-TR)
其一,John是一个极其孤僻的人。他常年处于独居状态,没有任何工作记录,没有信用交易记录,却过着富裕的生活。这是一个基本不与他人交往的个体,足够的金钱滋养着他在自己的宗教世界里偏执地沉迷。
其二,他的宗教世界观是异常的。如前文所述,天主教教义警示我们不可杀人,更不可以上帝的名义杀人,但John却自称是上帝的使者,用杀人的方式实施布道。
其三,John是一个偏执的人。从John的作案手段看,他应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受过高等教育,衣食无忧,但却不了解生活实际的人很容易偏执,这种偏执主要表现为对自己的观念和行为高度自信,且认为其他人都粗鄙不堪、平庸透顶。
其四,John应是一个存在交流障碍的人。他写了2000多本日记,在日记中,除却记录他犯罪的整个过程外,处处表达了对他人的平庸、无聊的痛恨和厌恶。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只有在十分闲暇时或者在不愿和别人交流时,才会诉诸日记。可见,他很可能是一个和他人交流存在障碍的人。
其五,John行为反常,外表也比较怪异。在John出现在警局自首的场面中,他满脸猥锁,满身沾血,手指皮已被割去。另外,由前文的犯罪过程的叙述可知,John的整个犯罪行为都比较变态、残忍,这亦是他人格障碍的一种表现。
John人格生成的根源。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先天因素和后天教化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个体的早期经历(如具有暴力倾向的父母)可导致个体特定脑区的神经变化(如影响视丘下部和脑垂体的功能)。为此,每个人的人格形成因素都是多维的,有生物学因素、学习因素、心理动力学因素、文化因素等。人格障碍的形成,也像正常人格一样,有多种成因。在此,笔者以John的变态人格特征来分析其生成的根源。
首先,生物学领域的根源。历史上,分裂型人格障碍一度用来描述那些倾向于发生精神分裂症的人群。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分裂型人格障碍是精神分裂症遗传型的表现型。④而关于家族、双生子以及收养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有亲属患精神分裂症而自己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群中,分裂型人格障碍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另外,有研究表明,如果妇女在怀孕期间患流行性感冒,那么她的孩子患分裂型人格障碍的几率有所增加。⑤综上,遗传因素对分裂型人格障碍的形成可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认知评估表明,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记忆以及学习能力有轻到中度的下降,这表明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的大脑左半球可能受到一些损伤。⑥还有研究者通过对一群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使用核磁共振成像,结果表明,这些人群中普遍存在着大脑的异常。⑦
可见,生物学因素对分裂型人格障碍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具体到John,由于电影对John的家庭背景没有详细的介绍,所以,关于生物学因素的影响,我们无法作出结论。但John表现出的孤僻以及偏执的个性,这里涵盖着遗传基因的影响是我们无法撇清的事实。个性是一个区别于他人的,在不同环境中显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影响人的外显和内隐性行为模式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它是人的本性与环境作用的结果。而本性是人出生就具有的秉性,是外界难以改变的心理感知特性及行为趋向,这是遗传的结果。
其次,家庭教育因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认为,抚养人对被抚养者具有生命的决定权,物质的提供权,照顾的程度权,个性的决定权。她认为,小孩的胃口是喂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而无耻是百般迁就溺出来的……即使孩子出走、自杀、犯罪,看似孩子的选择,却都是父母行为的反应或结果。其实,刚刚出生的婴儿,就像一张白纸,虽然天性具有一定的不可变性,可是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却决定着这个小孩将在这白纸上所画的图案:是快乐的?悲伤的?忧郁的?暴力的?还是和平的?
从剧情中,我们无法得知John的父母对他的抚养、教育过程。但是,我们知道:一是John的父母是天主教教徒,他们让John从小出入教堂、接受洗礼、上教会学校,这使John深陷于天主教的氛围,与世隔绝;二是John长期处于独居状态,他的成长极度缺少关爱;最后,John无任何工作记录,亦无任何信用记录,却过着优越的生活,这应是他父母在经济上对他的过度溺爱。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John只能是一个偏执而孤僻的交流障碍者,他沉迷于无暇的信仰,无法忍受现实世界中的丑恶现状,他忘却了信仰的本真,罔顾了真实的教义,无视现实中的法律,最终沦为变态杀人者。
最后,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是产生变态杀手的根源。John生活在美国工业化转型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但心却越来越远,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和金钱的关系。在这个冷漠的社会里,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欲望奔跑,并且这些欲望已被合法化。只要你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做这些事,不对他人构成侵犯,就不会犯罪。比如影片中,吃的像肥猪一样的胖子、被John捆绑在床上的被房东誉为“最好的房客”的人等,这些人只要不犯错,警察永远也不会找麻烦。所有这些都是对当时的虚无主义的社会现状的深刻描述。
可想而知,John是一个痴迷而又充满妄念的宗教信徒,怎堪容忍如此阴暗的社会?于是,他妄想自己是上帝派往人间的使者,用自己心中的正义之剑,以宗教之名,行杀戮之事。这是John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悲剧。
对信仰型杀手的心理矫治及综合预防
John虽是电影中的角色,但艺术来源于生活。当下的中国,有一部分人已经被物欲浸染,沦为了虚无主义者,他们无谓宗教信仰。可是,还有一部分人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对此我们要充分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可是,有些人因为自身的无知以及偏执,以致使他们沦为像John那样的人格变态者,上演着一幕幕血刃同类的悲剧。我们究竟该怎样对待这一群体,才可以遏制如此恶性的悲剧上演?变态人格的生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一旦成形,便很难改变。他们类似于罗梭笔下的“天生犯罪人”,对于他们而言,刑罚已基本不再具有威慑力,道德的说服力更显苍白,犯罪是他们的必然选择。为此,要遏制悲剧的上演,就必须塑造健康的人格,保持健康的心理。
心理抚养是父母早期家庭教育的重中之重。大多数父母认为,小孩在三岁前,属于无自主意识期间,抚养人只需要管小孩吃喝拉撒睡,可以恣意地在小孩面前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上演一幕幕夫妻战争片。事实上,父母的言行举止,好似可以回放的影像,一张张地纳入了小孩那洁净的眼眸,嵌入那稚嫩的心灵。因此,抚养人除了给予小孩物质所需外,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对小孩的心理抚养。
婴儿刚出生,本能地会去吮吸母亲的乳头,这是存续生命的必要手段,同时这也是为了从母亲身上获取安全感。通过重复这一行为,逐渐地建立起对母亲的依赖感,这时母亲已然是小孩的“心理上的依赖对象”。接着,小孩开始了对自己及外物的探知,开始吮手指、翻身、爬行、撕咬他物、学步、呀呀学语……在这过程中,如果他的周围充斥着谩骂声、上演着暴力情节,如果抚养人给予他的是批评甚至是大声呵斥,如果给予的是冷漠甚至是将之遗弃,那么,他的眼里将布满恐惧,从而将形成烦躁、敏感、神经质等性格障碍。或许他们的智力发展完全正常,但他们的社会性发展,如与他人的交往、关心他人等方面却容易表现异常。
有研究表明:许多杀人恶魔冷酷无情的心态往往源于他们在幼年时就没有“心理上的依恋对象”,或是在他10岁前后曾失去“心理依恋对象”。为此,为人父母,应该积极地致力于跟幼儿建立起“心理上的依赖关系”,及时地给予他们拥抱、爱抚及激励。当然,父母同时也需要适时地对他们说“不!”以培养他们适当的挫折感,锻炼其心理柔韧性,成就健康人格,远离变态,远离犯罪。
社交技能训练法,成就健康人格。人是社会人,为此,我们需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而人际沟通就是桥梁。所谓社交技能训练法,就是通过心理治疗专业人士的引导与沟通,让人格障碍患者掌握相关的社交技能,学会与人沟通,在沟通过程中,使他们能够得到关爱、享受关爱,并学会给予关爱,最终回归社会的一套人格障碍心理治疗方案。
当然,除了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外,周围集体的干预与影响显得同样重要。对于人格障碍患者,特别是有社交障碍的患者,不应让其处在相对封闭的时空中,而是应该让其融入社会群体。我们应该更有耐心,并适时对他们表示鼓励、赞扬以及关爱,以让他们重拾自信,感受关爱,慢慢地把扎根于内心的压抑、偏执以及孤僻等不良心理摒弃,逐渐融入健康的人群。
树立正确的信仰,铸就健康心理。当下,人们需要信仰,但信仰需要理性。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的宗教信仰,正确且全面地去理解宗教的教义,不能陷入原教旨主义,更不能以宗教之名屠杀我们的伙伴。当然,我们亦可以选择信仰正确的、符合绝大多数人类利益的普世价值。我们可以信仰社会道德,用道德律己。而更重要的是,在法治国家,我们更应当信仰法律,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理念,当我们在内心及外在行为上成为守法者时,我们已经远离了变态。
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当代社会物欲横流,财富似乎已成为区分人群三六九等的重要标志。为此人们竞相为追逐财富而不折手段,暴富者开始过起奢靡的生活,“富二代”、“高帅富”、“白富美”等成为了当代青年人恋爱甚至是择偶的标准。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每天辛勤劳作,可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挑灯夜战,可是,他们所得到的财富却是少得可怜,甚至不足以维持生计。在这样的背景下,仇富心理恣意横涨,变态人格者越来越多,灭门案、杀童案、恐怖主义犯罪等等早已屡见不鲜……
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减少变态人格群体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首先要缩小贫富的差距。我们既要尊重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更要尊重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要致力于缩小这两类人的收入差异。只有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缩小了,整个国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富民强。与此同时,人们要注重精神财富的增值。国家要保障既有的精神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多的新型精神文化产业链,以丰富发展人们内心所需。届时,人们的内心将不再空虚,妄念将无懈可击,孤僻将远离人群,偏执将被抛弃,抑郁、躁狂亦逃之夭夭,变态人格将不再具有扎根社会的温床。
(作者单位:广东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本文系广东嘉应学院人文社科类一般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
注释
①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②洪汉鼎:《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2页。
③[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26页。
④⑤[美]David H. Barlow,V. Mark Durand:《异常心理学》,杨霞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483页。
⑥⑦[美]兰迪·拉森,戴维·巴斯著:《人格心理学—人性的科学探索》,郭永玉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第565页。
责编/韩露(实习)